神经衰弱的病友们都知道,我们都偶尔做过连续剧一样的梦,醒来想想剧情,闭上眼睛睡着依然走回刚才的梦里。困扰我的梦境是部古装戏。凄风苦雨的嘉峪关外,我被一支紫金白羽箭穿胸而过,我低头看到鲜血瞬间染红了战袍,却没有丝毫的疼痛。一个男人抱着我的头,眼神里的绝望忽然让我的心痛了一下,他象是在大声问我什么,然而我却听不见,便努力想对他笑笑,想让他别那么悲伤。
梦里我清楚得知道我叫做陈莫,是漠北陈家的最后一根独苗,而抱着我的那个男人叫做阿景,他是齐皇的亲侄,却也是齐皇处心积虑要置于死地的人,我们都是弃子,都是必须华丽的死去之后被国葬的命运。一个不属于正史的匪夷所思朝代,开元十七年,一个清晰的纪年,北胡集结十万大军分两路犯边,边西青州、秦州危急。开元十七年三月初八,我爹爹阵亡,陈家军损失殆尽。年仅十七岁的我孤军被困嘉峪关外,苦战三天等来的援军却只有阿景和他带来的二十几人。包围圈越来越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命运就这样不可避免走到了最后。然而我还有个奢望,希望上天让阿景活下去,虽然年少的我也不想死,但是不敢再与上天讨价还价祈求更多。
阿景后来怎样了?我很想这个梦境继续下去,然而漫天漫地的风沙呜咽已然不见,只有眼前细纹罗纱的床幔。
我很想回去梦里,我想再见见阿景。然而睡眠却是我最无法控制的事情,直到清晨似乎已经来临,才朦胧睡去。
这次的梦境似乎是嘉峪关之战的前史,梦里的我还是个活泼可爱的少年。应该不算少年,只是一个从小扮作少年长大的女孩。因我是陈家最后一个孩子,生来注定要接掌陈家军,要被锻造成能抗下边西大业的顶梁柱。然而我让爹爹失望了,到了十七岁上,我依然文武都是半吊子,整天招猫逗狗的到博了一个边西第一纨绔的名头,当然这名头的好处就是谁也没怀疑过我竟不是男儿。这年我迎来了一个玩伴,他就是阿景。
阿景的父亲六王爷当年在与当今皇上争储中败北,去了江南番地,没几年就去世了。而阿景这个侄子,因酷似其父,也是今上眼里的刺。爹爹曾说过,今上身体越来越弱,他不放心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太子禀弱,一件是景王聪敏,这两件加起来就是一件,他要在自己驾崩前除掉阿景,保住他子孙的江山不落在他六哥后人的手里。
阿景也知道他的处境,他沉默寡言,锋芒内敛,来到军中以后,不与任何人接近。而我们相识走近,却源于一次意外。我因从小男装,便十分好奇女子的服饰,每每见到漂亮女子,便免不得多看几眼,于是色名远播。灯节那天,城守府秦家的一个女孩出来观灯,我便好奇了她那浅兰色软纱纹束腰长裙,上面绣起的蝴蝶栩栩如生煞是好看,我追着看去,竟不自觉上手拽了那裙摆细看。然而那女孩回头见我,却花容失色,险些就要跌倒,我便好心的伸手拦腰扶住她。。。那女孩就哭跑开了,竟寻了路就近跳进了一弯湖水里。我惊慌失措跳下湖去救,不想她扑腾着宁死不愿让我救她。我知道我的名声很烂,没想到烂到她宁死不肯让我靠近,可叹烈女啊烈女。可是姐姐,我不是故意的。就在将要出人命的时刻,阿景从游船上跳了下来,救起了那姑娘。
那夜的月亮很好,游船上的灯火映照在湖面上,我泡在湖水里看着阿景把那姑娘送上岸,然后俯瞰着我。后来阿景说,他听闻我是不折不扣的小色狼,然而那夜我的眼神无辜又恐慌,他莫名有些怜惜。十七年了,还没人用过怜惜这个词给我,于是我拍拍阿景的肩豪情万丈的对他说,兄弟,我死也会挡你在前面的。后来我做到了。
天亮了,要迟到了。我匆忙的穿衣洗漱,赶到影城还是晚了。我讪讪的从人群里悄悄向导演组移动,尽量让自己悄无声息,却电光火石般被一副容颜吸引住,阿景!那个站在导演身边的男人不就是梦里的阿景吗?我忍不住掐了下自己腿上的肉,想看看是否自己仍然还在那个连续的梦里。然而很痛,我惊呼,惹来目光,我囧了,却没有低头,因为阿景也在回头看我,我想我在用眼神询问他是不是阿景,然而他毫无所感,漠然的回过头去。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李姐挤过来,自以为很小声的对我喊,摄影组新来的那个男的你看到了吗?我觉特适合你!
姐,你能小点声吗?虽然我知道你们做录音的耳朵受得摧残比较严重,可你这样的音量说八卦你觉得合适吗?
李姐于是从善如流的更加靠近我,那个男的,多帅啊,北影的研究生,我跟你说这样的新鲜菜可不多,后期那帮小妞都盯着呢。
我继续大口吃着盒饭,心里埋怨着制片组的人越来越吝啬,盒饭的菜色越来越差,量还不够。
李姐忽然推了下我的胳膊,就那个,叫齐景的。
我的筷子差点掉在地上,迅速抬头,可怜我的小心脏万马奔腾般轰隆一片,黄沙漫天,纠结成痛啊,你还叫齐景!老天啊,别这样耍我好不好?
我说,李姐,看你本事了,这棵是我的菜!你快去给我抢来!
李姐郑重的点头,以她堪比职业媒婆的效率第三天就促成了我跟齐景的第一次准相亲式的晚餐。
我激动啊,从化妆组借来全套化妆品武装自己。其实这包装全然没有用,我那烈日炎炎下不修篇幅的形象估计已经多次闯进他的视角,再修饰也还是个女汉子,成不了女神。然而我却萌生个想法,我想打扮成梦里陈莫的样子去见他。
这几天梦里依旧的继续着那段剧情,依然是倒叙的模式。作为陈莫的我已经和阿景混得厮熟,也因为被爹爹教训了多次。爹爹深知阿景的命运没有未来,他不想我被牵连。然而年少的我,怎么会在乎未来这么个遥远的东西呢?
那时战争还远,然而朝堂却不太平,因太子再次病发,今上也跟着病势加重,他只有太子一个儿子,而这太子似乎患得是心绞痛一类的病,总是一副要大限了的样子。更乱的是三朝元老郑阁老冒死建议改立储君,这就是要今上把皇位让给别人的儿子啊,今上于是病得更重了。郑阁老提的人就是先六王爷的儿子景王,我面前这个叫阿景的少年。
这对阿景不是件好事,也可以说是灾难,也可能是七王爷或者九王爷为了快点除掉阿景而买通了郑阁老这么做的。阿景没有后台,他父亲六王爷的母族田家当年显赫一时,后来全族覆灭。阿景是风雨飘摇里的一棵没有依靠的小树。
那天酒喝到微醉,阿景忽然说,你看我的指纹,十个都是传说中的簸箕,我的命运注定是苦的。而我却不以为然,我兴奋的伸出手给他献宝,你看我的十个手指都是斗啊,我们天生是互补的,你跟着我混没错的!
那天梦里醒来,我匆忙的打开电脑查有关指纹和手相的书,却看到令我失望的解释。手纹生就十个斗的女子,与生就十个簸箕的男子注定会纠缠的缘分,世世相遇,却只有一世能得善终。
饭店在我读过书的那所大学旁边,是一间十足的情侣餐厅,菜肴精致,装修非常有情调,尤其是灯光,非常适合朦胧美。
然而我却嫌灯光太暗了,为了提升形象没戴眼镜出门的我完全看不清楚齐景的表情。我不知道怎么把话题拉近,总不能冒冒失失就开始讲述我那个奇怪的梦,这样被他嘲笑还是其次,只怕以后整个剧组都会流传出我为了钓个帅哥已经走编故事路线了,这个虚名我担不起。
下
我没能装扮成梦里陈莫的样子,反而在自己修眉的时候手抖华丽丽的割破了一道小伤口。出门的时候权衡再三,还是贴了一个创可贴在眉上。李姐见到我,立时囧了,上前就要拽下创可贴,责怪我不争气,总是关键时候出状况。我心里不忿,说毕竟小命要紧,伤口感染可不得了。最终李姐妥协变出一把小剪刀把创可贴裁成了一个小方块贴在了我的伤口上。她边裁边说,眉上落了疤,这可不是小事,这叫破相!然而很快伤口还是肿了起来,于是我眉毛上贴着一块创可贴眼睛肿了一只表情怪异的坐在了齐景对面。(艺术来源于生活啊,今天早晨的受伤经历咱给妙用了)
心不在焉的点了菜,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一定是没有做过跟我一样的那个梦,否则不会认不出我这张跟梦里陈莫八成像的脸!于是我失望了,自顾自的叹口气。
听说你睡眠不好,去看看中医吧。大望路那边有个叫周小金的大夫看得很好。
是啊,睡眠不好就时常做梦,有的梦像连续剧,完全可以出本书。
我还是琢磨着那个梦,然而终究知道讲出来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成功拽住了自己,在心里给自己戴了朵赞许的小红花。
他笑了,大约觉得我是职业病。他嘴角上扬的弧度很亲切,跟梦里阿景一样的笑容。只是梦里的阿景似乎很少笑。
我想交个朋友也不错吧,于是释然了。菜香飘过来,勾起我念书时的回忆,那时多么喜欢这家小资情调的餐厅啊。有一天要带上自己心仪的男人来这里吃饭,是我们宿舍六个丫头唯一没有分歧的梦想。我不仅微抬头看我对面的齐景,这是我心仪的男人吗?我对他的好奇源于也止于他跟梦里阿景的相像吧?
饭后喝茶的时候我终于恢复本性做了一件符合我格调的无厘头的事,我给他看了手相。这男人和阿景一样,他十个手指都是簸箕。然而我没有告诉这手纹里的玄机。毕竟我与梦里的陈莫不同,我以旁观者的角度判断那个陈莫是有些幼稚乘以二。
没几天,剧组就传开了,导演组的梁小树学会给男人看手相了!于是我愤怒了,这个叫齐景的太不讲究,几天来一直没联系过我这个可以理解,毕竟树姐我也不是什么花容月貌没想让你一见钟情,可你也不能把树姐我形容成一个花痴啊!
午休的时候我找到齐景,斜眼瞪着他,酝酿着从哪一条开始谴责他。齐景正在修摄像机,抬头看到我,很自然的说正要打电话问我明天可有时间,他有一个大学同学结婚,想约我一起去。我的脑子高速飞转了几百秒,去蹭饭吗?于是我把来找他最初的目的全然忘记了,郑重的思考了这个蹭饭的问题,这要穿哪件衣服去才合适呢?
梦里的陈莫和阿景如胶似漆的每天混在一起。我在梦里就变得迟钝,对,我必须得说只有在梦里才迟钝,现实我必须是个聪慧的人,没有这及时的纠正我便无法继续写下去。
前世里你一定对我很好,于是今生我不管怎样对你好,都还嫌不够。那晚的梦境就截止在作为陈莫的我如此花痴的一番表白。似乎阿景表情怪异的看着我,眼神有感动却更多一丝掩饰不住的哀恸,他说,我但愿前世曾对你很好很好。梦里的我完全被他忧郁的眼神吸引,不知道这句话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而醒来后我就无暇再去分析梦境,我开始和齐景频繁的约会,吃饭看电影逛庙会,不远不近的距离走着,似乎只比朋友多一点,我丝毫没意识到这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我的眼睛视角有限无暇顾及齐景以外的人了。李姐气恼的拍我的头,你等我给你再介绍一个更好的,齐景他不合适。然而这次我没信李姐,我和齐景是有前世的,她不懂,我也不想对她讲,这是秘密,多幸福的秘密。
我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会和齐景就这样快乐的走下去,和世上所有幸福的人一样,书上不是说了,这世上幸福的人都一样,悲伤才与众不同。于是我开始彻底清扫我的小公寓,买了好看的围裙戴着跪在地上擦地板,一边哼着走调的歌。然后我坐在地板上想,也许我们以后会生个像小丸子一样的女孩,每天看她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件囧事,或者生一个像阿景一样帅气的男孩,我会对他说你是男孩子你要照顾妈妈,妈妈是女生,乖,去厨房把碗洗了。于是我被我自己逗笑了。李姐吃了几次我做得豆豉豆腐,都只斜睨着我说,齐景跟你不合适,他心太高,这事是姐没调查清楚,我想挽回行吗?你别让姐丢手艺行吗?我却没给她挽回的机会。
在邻居阿姨也鉴定了我做的豆豉豆腐和鳗鱼寿司能拿得出手后,我决定第二天就请齐景来家里吃饭。我去超市大采购,看到包装可爱的巧克力,想要买一盒回来,却又嫌巧克力的颜色太单调,没有七彩的星星糖那么好看,于是我带回了一盒五颜六色的星星糖,郑重的摆在茶几上,怎么看怎么满意。
那晚我早早的睡着了。然而梦却很不太平。梦里的我和阿景的悲剧命运终于来临。战争让秦州这个西北第一大城变成了死域,秦州失守了,北胡军屠了城。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然被困在嘉峪关外。我的眼泪滚落在脚下的黄尘里瞬间消失不见,我想起了那年灯节被我“调戏”而跳河的秦小姐,她还好吗?她的命运会怎样?这个城留给我的无数童年少年的记忆在我眼前生动回放,似乎在跟我做最后一次告别,我的心痛到不能呼吸。
爹爹阵亡时,让偏将李将军带我出城,那时我们还有几百人。几天来我们依仗对嘉峪关外地形的熟悉击退了几次追兵,然而终究且战且退,只剩下了十几人。
那夜暗黑的天幕没有一丝星光,空气飘荡着是大雨来临前的土星味道。小九忽然抱住我说,小姐,你换了这套衣服走吧,老爷说了,要您一定活下去!
小九是我身边唯一知道我女儿身的侍女,她八岁就扮作小厮模样跟着我,亲如我的姐妹。然而我却不能听她所劝脱下这身战袍换上女装躲藏,我是陈家军的少将军,只能战死,岂可偷生?
然而我却点了点头,想让小九换了女装爬过山隘混进偶尔经过的流民里,或者还有一线生机。小九本以为我答应了,待得知只有她一人要走的时候,忽然哭着跌坐在我面前,小九生是小姐的人,死是小姐的死人,小姐怎么可以舍弃小九?
这场战争已让我对随时降临的死亡司空见惯,那么就一起生一起死吧,不要再哭了。于是小九连忙擦干了眼泪,悄无声息的坐在了我的身旁。黑暗里我的眼泪却滚滚落下来,如果真的要死了,我还想见见阿景。爹临终遣我出城的时候,因匆忙不曾与阿景别过,终这一生,再不得见了吗?
第二天红日东升的时候,是阿景带着他仅存的二十几个亲卫赶来,我激动的迎过去,晕红的阳光照应在阿景的脸上,我以为是上天听到了我的祈求,带阿景来见我最后一面。然而阿景的表情如此沉重,让我想禁不住想要安慰他什么。可我还什么也来不及说,北胡的军队铺天盖地包围过来,数面明紫的大旗上绣着明黄色的鄢字,是北胡最勇武的公主郑鄢的队伍。北胡这个民族,历来男女一样尚武,女子可以做官可以带兵打仗甚至可以当女王。传言这个郑鄢,很可能就是下一任北胡王。
郑鄢高高坐在马上,穿着银色的盔甲,脸上带着半幅颜色的面具,她眼神冰冷的看着我。我想我在她眼里是狼狈而渺小的,然而我却只能挺直了背脊与她对视,我是陈家军的少将军,死也不能坠了父亲的威名。
我终于知道那只紫金白羽箭来自哪里。它带着破空的声音从侧面飞向我身旁的阿景,我看到那拉弓射箭的人是郑鄢的副将贺图,没有时间去想,转身挡在了阿景面前。那箭锋利的穿胸而过,伤口不痛,只是心有点凉凉的,是死亡前的征兆吗?
我以为我就这样为阿景死去,是多么幸福而值得的方式,于是我微笑着闭上了眼,耳边只剩下风声。如果我永远看不到之后的事情,那么我至死都是幸福的。然而梦境忽然剥离了我,我悬空看到我死后的画面。阿景悲伤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和我的血混在一起,他轻轻擦干净我的脸,就放下了我。
郑鄢从马上跳下来,阿景走向她。两人熟稔的用北胡语说着什么,我竟然能完全懂得这陌生的语言。
阿景神色已经恢复了以往的冷漠和平静,他只说,你要除掉我?
郑鄢公主很爽利的回答,误会,他以为没有你,就可以娶我。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攻下秦州,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回国我们就成亲,你就是北胡的驸马。然后她果断的回头命令把刚才放箭的贺图立即处斩了。
郑鄢和阿景两人站在晕红的日光里,那么绝美的一对,完全出离了周围悲怆的画面。我的小九正扑在我的身上恸哭,她转身大骂阿景,你这条毒蛇,你私通胡人,你害死小姐!
阿景转身看着小九,似乎在对她郑重的解释,或者是在对自己解释。我并没有要她死,我只是为了我的大业,没有北胡的帮助,我永远无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齐国的江山,本就该属于我的。
我的魂魄飘荡在半空,我很想问阿景一句,你没有要我死,可是你给了我活路了吗?
我想起阿景曾说,我但愿前生曾对你很好很好。他说的是前生。
清晨我哭着醒来,无法言喻的悲伤混合着胸口窒息的痛,一如穿胸的箭伤。我摸过手机打电话给齐景,哽咽着说,阿景,来我家看看我吧。
然而齐景沉默了。我在他的沉默里忽然感觉他变成了梦境里的阿景,我的手心开始冒出冷汗,阿景,你怎么了,你说话啊。
齐景冷静的说,小树,我一直当你是很好的朋友,能让我感觉快乐的朋友。
我放下了手机,原来我只是朋友。我想起李姐的暗示,齐景和苏培培走得很近,苏培培的父亲在央视任要职,她一向眼高于顶,却只和齐景不远不近的暧昧着。是啊,齐景一直这样不远不近的游走在这个世界,一如前世的阿景,生来有自我保护意识,随时懂得全身而退。
齐景不知道曾经有一个纠缠前世走进我的梦境,我想他无缘知道,他也不知道那个关于手纹的箴言,于是我想上天还是更疼爱我的,让我比他知道的多。我穿着睡衣走去客厅,打来窗帘,让清晨的阳光照进房间里,有什么了不起,至少今生的梁小树还活着,有什么了不起!然而我回头时,看到茶几上那盒五颜六色的星星糖,我愣愣的看着那糖,边擦着眼泪边对自己说,我才不是为你哭,我只想起谁说过,有些糖,注定是不会甜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2-18 23:09:22编辑过]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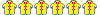


 :越混越钱多
:越混越钱多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4/2/18 23:0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4/2/18 23:08: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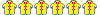


 :越混越钱多
:越混越钱多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4/2/18 23:1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4/2/18 23:10: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婉约小令
:婉约小令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4/2/19 7:0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4/2/19 7:05: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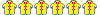


 :越混越钱多
:越混越钱多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4/2/19 23:0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4/2/19 23:08: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小小新娘
:小小新娘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4/2/20 7:0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4/2/20 7:05: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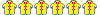


 :越混越钱多
:越混越钱多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4/3/13 18:2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4/3/13 18:24: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8/11/23 0:53:0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23 0:53:0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8/11/24 0:10: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24 0:10:2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8/11/24 0:13:0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24 0:13:0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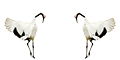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8/11/24 2:37: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24 2:37:1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