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
刚过去的中秋节,那天一大早,他发来一条信息:小黄同志节日快乐!
我回了一个表情,然后问他,有几个秒回你的人。他说:一个。
和他认识算起来有十年了,如我半个人生导师,带入歧途那种。
互不相干的日子照常继续着,国庆假期的第二天 ,他又冷不丁发来一句:老爷子应该没几日了。
他父亲生病的事我知道个大概,但恶化如此之快,未曾料到。他说已经挂不进水,接回家来住了。说话间我没有感觉出多少悲伤或者唉声叹气,除了隔着屏幕的隐隐疲惫,就是他一贯的冷淡了。
床边端水端药,收拾大小便的都是他,这段日子他应该是辛苦又煎熬的。只他一人在旁,母亲也是才刚他从医院接回来,家里头根本没有可替换的人。大半夜的他守在病榻边上,怕他父亲被痰堵了呼吸,所以自己不能睡,便与我断断续续地叙说着。
他想着父亲这么去了也是个解脱,他像是在数日子、等时候。虽然我们无话不谈,但思量了下还是用了个算是中性的措辞,我说,你比较“冷静”。
他父亲已是很难安稳入睡,想要些安眠药。但他怕老父一把都给吃下,真就去了,所以始终没去配。我说要在医院,有些极度疼痛的晚期癌症,医生是会开吗啡杜冷丁之类的,你就权当临了他能好受些吧。又给他看了自个一直在吃的安眠药,没见过什么副作用,让他明儿就去医院开处方。
这一夜后,我们又不再联系。也是担心扰了他照顾父亲,或正睡着觉。直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才给他留言:怎么样了。他没回复,到晚上零点后收到他四个字:老父走了。我说那你要辛苦些日子了,等回头再慢慢说与我。他“嗯”了一声后,一切变得死一般寂静,我对着电脑呆呆地坐了很久很久……
随后那几天,我独自一个人时总会想象,现在他在做什么仪式,现在是不是已经从殡仪馆回家了,现在他是不是在烧纸箔,是不是眼睛红红,也在哭在流泪……又或许他是在默然中度过,他是个最不会做作的人,如今的他心里大抵是空荡荡,一片荒芜的,做不出来任何悲伤的形式。是的,他应该还是冷淡的,按部就班地送走老父,安静地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和自己。
而现在的我,一边跑步一边也没能遏止住胡思乱想的念头。跑到一点力气没了,最后连走步都迈不开时,重重地舒了口气,放弃思维放弃了想象他的一切。任由喷涌的热水,将一堆缠绕的思绪连带一身的汗都彻底冲洗尽了。倦极地坐了会儿,背起包走出健身房。
一出大门,冷瑟的夜风劈头盖脸地打来。我拉高衣领,把包扔进车篮,缩着身体压着自己的影子缓缓骑回家。
路上遇见一对晚归的老人,拽着衣袖过十字路口,两人的样子被夜色衬得很沧桑,叫人移不开视线。红灯似乎极漫长,我就看着这对老人一步一步,迟钝而略显艰难地挪过眼前。
我突然想,自己的父亲母亲到了这把年纪,又会是怎样的光景。那时我还在么,会陪着他们垂垂老去,像他那样在病榻边守着老父的呼吸,淡然而孤独的面对这无能为力的生活,坚持着活下去,走下去么。
绿灯亮了好一阵我才知觉,被夜风吹得凉透的脸上,泪水却已不知觉的蔓延。为了避开行人,避开路灯,我狠命踩了几下自行车,把自己疾速送入夜幕当中,深深的,望不到底的暮色中……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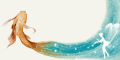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8/11/10 20:09: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10 20:09:1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月隐西楼
:月隐西楼
 :小满。
:小满。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8/11/11 11:05:0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11 11:05:0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8/11/12 10:45:4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12 10:45:4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8/11/12 10:50:5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12 10:50:5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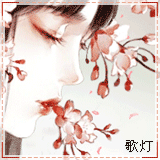




 :歌尽灯火阑珊处。
:歌尽灯火阑珊处。
 :江湖夜雨十年灯
:江湖夜雨十年灯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18/11/12 11:02: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12 11:02:0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月隐西楼
:月隐西楼
 :小满。
:小满。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8/11/30 13:04:4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30 13:04:4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月隐西楼
:月隐西楼
 :小满。
:小满。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8/11/30 13:34:4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1/30 13:34:4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武陵人
:武陵人
 :亸袖袖
:亸袖袖
 :袖白雪
:袖白雪
 :金屋子
:金屋子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8/12/3 16:13:1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8/12/3 16:13:11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