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海边,每天听惯了的是风吹浪打。若然风吹浪打寻常事,顺势而长傲苍天。
--题记
天气朗晴的夏日,带着气垫船、救生衣或者一套轻便的钓鱼装备,前往海边,是这个城市居民最寻常的休闲方式。彼时,携子负老,毕力同心,搭一顶帐蓬,撑几把遮阳伞,也有省了气力就近旁处租用来的,然后打开满满一箱的木炭,支起烤炉,烤架,摆上各色的食物就案,甭管天气多热,海风吹得多大,怡然而自得。
顶大个儿的西瓜开了瓢,汁水顺着手掌流淌,孩童眼窝窝地瞧着,贪嘴地咀嚼,待到把这西瓜挖空,遂将西瓜皮扣在头顶,俨然一顶天然浑成的贝雷帽,拿着叉铲用力挖掘,骑士城堡,带一湾清浅的池塘,梦想中的罗马帝国在脚下铺开。垂钓的老者,一竿子远近,丈量韶华荏苒汤汤岁月的否泰,于日薄西山世态婆娑的苍凉中安稳心境。好水者,扑腾起了浪花,时隐时没于渐远的水域,又有嗜水者,潜下扎几个猛子,稇载而归,肥硕的海参、鲍鱼,不过寻常。几个汉子较劲下了赌注,再一趟的潜,谁的货更稀罕数量更多。又或者,并不喜这样那样的热闹,一个人静静地躲在荫凉蔽处看海,看天边的云,看一方风景独好,也有海阔天远的潮在胸中涌动。
我爱行海,我爱看海,而我更爱的是海中若许无名的小岛。在英国女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作品中,岛是悲凉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秽往生世界的鲜花,岛是重生,是期盼,是孤独相望的连接。
这座城市,有名字的岛屿大约有百座余,棒棰岛、獐子岛、凤鸣岛、骆驼岛、广鹿岛、……但因人迹繁杂,商业往来频频,已渐渐失去了天籁天音天成的宠幸,它们更像与城市附生附链的子息,拥有城市的五脏,却缺乏了野生野态的原生气息,而我,喜欢的是另一种岛。
从我的窗棂一眼能望见的海域并不见岛,倘若肯驾快艇行驶2海哩左右,可见一个无名小岛。小岛并不很大,方圆一公里不足,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驱而往驶,常日倦不知归途。
密密的绿植是小岛的特色,因并无人打理,疏间浓密颇不自在,或有蘑菇野花野草点缀其间,也生长得并不匀势,大慨是惯看了齐整之美,倒觉得这样的随意疏放自有一番韵味。某喻这小岛为奇异的恋人之花,插在一望无垠的大海花瓶之中。我亦叹服,想到了芬兰的别卡宁。
暗礁与隐藏的棱砺是小岛的另一特色,要熟悉水路的驾船员,才能将小舸安稳地停在小岛的一处,而于小岛深处居坡凝望,这些暗礁更像是鲨鱼的牙齿,与海浪搏击,呼吸天宇之凝华。它们是小岛某种意义的守护者。
春日当景,和风薰炉,绿植的气息扑面飞扬,这里是天然的氧吧。夏日浓暖,轻风徐来,暗礁上布满各色贝类殖生,这是小岛上最有收获感的季节,纵不以渔业为生的游者,也能采集到海波罗,生蚝牡蛎,小螃蟹横着爬到手上,猝不及防地轻甩,又小心地把它引到瓶中……秋日,岛上金黄的叶片为小岛铺上厚层的地毯。而至冬,我是没有去过的,不知它也是否也会穿上一身冰霜的盛装。
在岛上看到的海,我总觉得是和别处不同的,太阳似乎格外钟情的把颜色分解成若干谱系,层次照在小岛近处的海水。我看过最红的海,最蓝的海,最橙的海,甚尔有碧绿的海,都只在这小岛周边。落日的海的色彩尤为变幻不定,水面上异彩纷呈,令人为之炫目。波澜起伏处,各色的海水像一尾尾游弋的大鱼,掀天逐浪。
风和暴雨在小岛上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肆虐猖獗,哪怕是酷热的夏,也有莫名的风从不知的海岸处呼啸抵达,最大的风掀起的海浪可达五米树高的梢头。这时的小岛便失去了往日优雅的娴静,凌乱婆娑,叶片飞舞,枝杆摇曳,或带起的还有小石头,在土地上打出一个个小窝来。这样的天气,小船大抵是不敢动的,但我的一个朋友,却每每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驾船至小岛中途,携一泳圈穿着救生衣游泳到小岛。这是勇敢者的游戏,当痛击与风浪袭卷全身,搏击的勇猛,战胜的喜悦,直穿头顶,让人有莫名的快感。而带着这样的快感,再回到人与人纷争的世界,大抵可化而为之,闲庭信步了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的人,这座城市的人有着粗砺的性格,广博的胸怀,住在海边,每天听惯了的是风吹浪打。若然风吹浪打寻常事,顺势而长傲苍天。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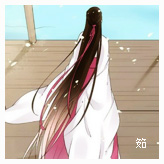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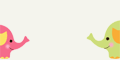

 :涵空日月
:涵空日月
 :陶白阁
:陶白阁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0/4/19 18:53:25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0/4/19 18:53:25 [显示全部帖子]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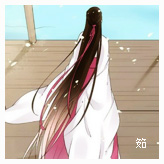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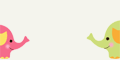

 :涵空日月
:涵空日月
 :陶白阁
:陶白阁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0/4/19 18:55:18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0/4/19 18:55:18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