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迟迟
一只蜗牛在奔跑
一只蜗牛在春天奔跑
春天在写一首碧绿的诗
一只蜗牛在湖面上奔跑
风吹湖面波光粼粼
一只蜗牛在玫瑰的尖刺上奔跑
它跨过鸟语与花香
它想像一匹骏马一样
在广袤的原野里奔跑
一只蜗牛可以和春天谈判
让春天写一首碧绿的诗
一只蜗牛也可以像一匹骏马一样
跨过日落与日出
不要因为笨和慢
不要因为小和轻
坚持奔跑到终点的蜗牛
一样会得到世界最热烈的掌声
—— 楚心心《一只蜗牛在奔跑》
“周家婶子,快去看看你家二妮,这会子正和老陈家的小子撕掳呢!”德宝家媳妇端着个乌漆麻黑的小锅,仰脖子吸溜了一大口面汤,蝎蝎螫螫地喊。
周婶子虽然看不惯德宝家媳妇的死乍乎劲,却不能不顾自家孙女。这孩子与别家孩子不同,听村医说得了多动什么病。她爹娘都在广东打工,大儿子带去那边上学了,留下二妮给老婆子带。二妮是真好动,点火烧房子的事没少干,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老大不小了还时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老陈家那臭小子比二妮小三岁呢,还能欺负得了她,十分讨嫌。周婶子越想越爆躁,顺手操起一根火棍子,拖着跛腿一路追了出去。
到了三月,天再凉,也还是春天,山脚下的雪融化得差不多,牧草迫不及待地冒出头来,一眼望去,如一匹青翠的地毯辅向天边。村长手搭凉棚朝远处望去,明黄的阳光下,几只燕子欢快地低飞着,一群挂着鼻涕的小屁孩追着燕子疯跑,他叹了一口气,村里的小学唯一的校长兼老师病了,开学都几周了,再没人接手,村里这些孩子野皮实了,可不就废了。
唉!村长叹了一嗓子,愁眉苦脸地望着周家婶子两手黑泥地拎着二妮从地里一路骂回来。乡里说这几日有老师下来,他都在村口等几天了,也没见个人影儿。
他忍不住给乡里挂了个电话,电话里说老师今天就该到了。
老村长高兴地一拍大腿,将烟袋锅使劲在鞋底上磕了磕,招呼着德宝,跑去村口迎接。
竟是个年轻瘦小的女娃子,姓白,师范刚毕业,双眼细长,白白净净的。德宝将老师简单的行李提进学校旁边的宿舍。村民见着这么一位标致的女娃子,纷纷来看热闹,站的站蹲的蹲,男的抽着劣质狠辣的旱烟,女的手里也不空着,做着一些针线活,很快将这间小屋挤得满满当当。眼见全村的老小都围着白老师,二妮自是不甘寂寞,又是泥又是尿的,硬是挤靠在老师身边傻笑。周婶子到底面皮薄,拉起二妮一巴掌打下去,却没打在妮子身上,被白老师闪身接了,那巴掌便硬硬实实打在了她的背上。虽然穿着厚实的棉服,也是一声闷响。
“大娘,孩子没犯错你打她干什么?”白老师年纪虽轻,却很稳重。
“这孩子身上脏,蹭你一身泥。”周婶子讪笑着摩搓手。
白老师抚了抚二妮的脸颊,那上面结着鼻涕眼泪和一些泥垢混合物,到底是孩子,长年没认真清洗,虽然天气日暖,但满脸都是皲裂的痕迹。
全村人都像看稀奇物一样看着白老师,德宝媳妇竟然拿了一大块刚熏制好的香猪肉干来;周婶子也跑回家,端了一碗酥油糌粑,却被村长拦下了。南方的女娃身子弱,吃这个难消化。说得周婶子满脸羞愧,像做错事一般,一只长着白色翳障的眼睛下意识闭了闭。白老师见了,赶紧将那团油乌乌的糌粑接下来,老人家这才将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舒展开来,撩起围裙悄悄地擦了擦眼。
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他们结婚生子后就把孩子留给老人,为了省钱,很少回家,有的孩子甚至几年都没见过父母一面。
说起来,二妮爸妈还算是比较有能耐的,把大儿子接到外面读书。大多人家的孩子就没那么好。
学校座落在一片空旷的山坡上,校舍半新,桌椅倒是齐全,只教具比较简陋。全村三十来户人家,矮小颓败的房屋错落着分布在坡底下。坡顶却修了一座洁白的大尖塔,比校舍还高,上面飘着经幡,荒烟曼草下,飘着淡淡的青草香。
白老师接管学校后,将孩子重新分了一下班,有三个年级。说是三个年级,其实才十三个孩子。孩子的年龄差别大,最小的六岁不到,最大的十六岁了。她身兼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老师于一身,很是辛苦。
为了摸清孩子们的基础,她出了三张难易程度不同的试卷给孩子们做,通过摸底将基础比较好的孩子分出来,让这些孩子在掌握自己课业后去教低年级的孩子,这样不仅巩固了高年级孩子的学习,也解决了自己的不能分身的困难,一举两得。
开学后,孩子们都被关在教室里,二妮失去玩伴,变得十分寂寞。她每天都跑到小学校的操场去玩,等待孩子们课间的十分钟。这天,白老师发现孩子们下课后都朝坡顶的白塔跑,她不明所以,朝那看了一眼,骇然发现塔上有个孩子摇摇晃晃地趴在上面。
是二妮,这个看似瘦小弱智的孩子不知用什么方法爬上白塔,正不上不下地乱爬,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田鼠。她赶紧让一个孩子去叫村长,自己疯了似的跑向白塔。原本,二妮双手双脚趴在塔顶,但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围观,不由兴奋起来,竟自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嘴里哇啦哇啦喊着不成语调的声音。孩子们不知道危险随时降临,竟跟着嘻笑,拍着手直乐。塔身长年日晒雨淋,很是湿滑,眼看二妮一脚滑倒,身子一横,头朝下栽下来。白老师来不及细想,一个猛冲,伸出双手接住,两人抱在一起,滚在匆忙赶来的村长脚下。
所幸白塔不高,二妮被白老师接住,毫发未损,老师的脚踝却骨折了。
离村里最近的乡卫生所三十公里,都是山路,不通车,除了步行,只有人力车可以用。但村里的男人都是年老体弱的,显然,拉着人力二轮走三十里的山路不现实。白老师坚持不让带出山,没办法,村长只能用祖传的老办法,采来草药捣烂了敷在伤处,再用两块板子固定,疼得白老师脸色煞白,牙关紧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周婶子心疼得直擦那只长着白色翳障的眼睛,村长又叹了一嗓子。这条路,啥时候能通到外头。
第二天是礼拜六,白老师柱着刺槐枝子做的拐棍一跳一跳拐到周婶家看二妮。
屋子里十分灰暗,有一股子尿潲混合着年迈女人特有的气息。白老师适应了好久,才勉强不至于被这气息逼走。
“大娘,让二妮上学吧。”白老师摸了摸二妮枯黄的头发,小妮子正专心地研究她伤腿的夹板。多动症的孩子越早介入矫正越好,她已经打电话咨询过北京的老师了,还托老师买了几本相关的书籍,她没有把握能够帮助到二妮,因为上学时学的并不是特教。
白老师给浑身尿潲味的二妮好好洗了个澡,找了一件相对干净的衣服换上。当她牵着二妮的小手离开的时候,周家婶子手里执着一串佛珠,踉跄着追出来,朝着白塔缓缓跪在地上,嘴里喃喃念着什么。
自此,二妮成了白老师的小尾巴,她走到哪,二妮跟到哪,有时候白老师去家访,她也跟在后面等在门口。
只不过大半个学期过去了,二妮还像往常一样,不会开口说一句整话。
全县中小学生要举行《国旗下的朗诵》活动,往年,这个村小学从来没有条件或不想参加任何活动,能完完整整上好课就很好了。再说,出山也不容易。但白老师决定参加这个比赛。全校不同年龄组包括二妮在内有十四个孩子了,十四个孩子的朗诵,可以的。
这么说,不会说话的二妮她也不想放弃,她选了一首著名诗人楚心心写的小诗《一只蜗牛在奔跑》。
五月,县里传来消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朗诵比赛改成线上比赛,参加比赛的学校需将孩子的朗诵过程录制成小视频送赛。白老师听了反而长舒了一口气,这种方式的比赛解决了孩子们出山困难的问题。
六一儿童节这天,白老师起了个大早,孩子们也早早来到学校化妆。白老师拿出自己简易的化妆品给孩子们描眉点唇。爱美是女孩们的天性。她们第一次看到自己被化成美丽的样子,既紧张又兴奋,高兴得像一群小燕子。
朗诵的视频上传到评委老师的面前。十三名孩子戴着红领巾坐在山坡上的国旗下齐声朗读,二妮打扮成一只可爱的小蜗牛在镜头前天真无邪地笑着,挪动着。阳光忽明忽暗,打在这张有着明显智力缺陷特征的小脸上,打在村民们身上,他们围坐在山脚下,整齐而清脆的童声绕过五星红旗,穿越山林,四野阒寂,群山侧耳倾听;惊飞的燕子俯冲下山,将诗句衔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花海上空,山风低吟,春日迟迟。
比赛得了一等奖。
视频被传到各大网站,最高点击量达到上千万,被一家企业看到,出资修了一条可以开车通向外面的宽阔公路,还把二妮送到专业的特教学校学习。
有了这条公路,百年来从未热闹过的古老村庄突然忙碌起来。大片的植被及原始的风光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了,他们将竹编笸箩、五彩织锦、水磨石刻等等特色产品卖给游客,还在路边搭起小食摊,等到游客又累又饿时,正好可以坐在简易摊点前喝一碗冒着煞白热气的羊肉米线,可以鲜掉眉毛。富裕起来的村民衣着不再褴褛,而是浓彩重绿起来,孩子们被送到县城去读书了。
冬天的时候,孩子们都走了,白老师和二妮两人升了一次国旗,明天,她也要被送到山外的特教学校去学习了。
一师一生并排站在国旗前,远处,雪峰蜿蜒接连,冰舌逶迤而下,终年覆盖积雪的的冰川,呈现盛大而纯粹的白,在近乎透明的蓝色苍穹下,五星红旗卷着山风,猎猎作响,肃穆庄严。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冠冠
:冠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3/15 20:30:0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0:0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1:4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1:4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2:3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2:34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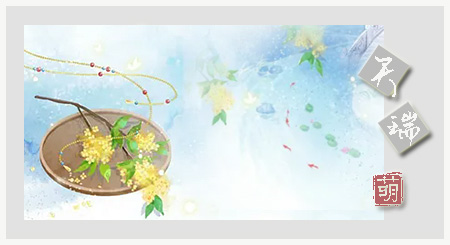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4:1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4:1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4: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4:1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4:2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4:2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5: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5:4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6:2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6:2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6:2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6:2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杜松子
:杜松子
 :酒神@古藤杯
:酒神@古藤杯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7:1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7:1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7:3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7:3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7:5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7:5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8:3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8:3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战斗民族特供
:战斗民族特供
 :酒神@保温杯
:酒神@保温杯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8: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8:4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3/15 20:39: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15 20:39:16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