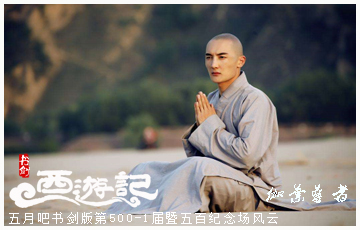登上科隆大教堂
科隆曾是古罗马要塞,拜H先生所赐,在二战中被炮火夷为平地,古罗马遗迹也多半荡然无存。
科隆大教堂之所以能够在瓦砾堆中奇迹般劫后余生,乃是因为被盟军飞行员选中作为投弹的参考座标。
而今的科隆“老城”,房屋建筑年龄都不超过七十岁。倒是大教堂前的古罗马拱型门残迹,已经傲然伫立了二千年。
少年呆立在台阶下,两座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尖塔的雄姿,豪气地撑满眼眶,猝不及防的视觉冲击让他“哇——”的一声呐喊之后,嘴巴久久未能合拢。
始建于中世纪的科隆大教堂,象一座突兀的山峰,披挂数百年沧桑,于老城闹市中拔地而起,生猛地闯入人们眼帘。石笋般的尖塔和石壁上繁复精美的浮雕,都饱蘸经磨历劫的风霜,色泽深沉厚重。
整座建筑带有沉重的压迫感,强大的气场似有夺魂摄魄之魅。
这情形似曾相识。
回想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与科隆大教堂的初见,震惊度不亚于少年。
当时有幸遇到一位敬业的好导游,老生常谈的游览项目也被他别出心裁在细节上玩出彩儿来。
当他煞费苦心选好停车位置,把车停在两座尖塔正对面,再让我们一行人从车里鱼贯而出时,所有人都被逼入视野的一百五十七米高的双塔深深震撼,众人对着教堂齐行四十五度仰视注目礼。此时,语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其他角度初见教堂,冲击力固然也很强烈,但怎及这劈面而来、狭路相逢的力道。
那个如邻家男孩般的导游,带着极度的满足,笑眯眯地享受这一刻,游客们的各种夸张表情与惊骇叫喊,是对他良苦用心的最好回报。
少年显然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个一路懒洋洋、只为海德堡而来的家伙,像是服了兴奋剂,开始围着教堂转圈拍照。各种角度,大轮廓、小细节,不厌其烦。转了足有三圈之后,又兴致勃勃进入教堂里面。
教堂里的氛围是祥和宁静的,默默静坐的教徒和三三两两的游客,各得其所。
少年放慢脚步,蹑手蹑脚地拍那些彩绘玻璃和精致的雕刻,尽量不打扰那些静默的人们。
因为在教堂里流连太久,错过了登塔时间。于是我们走到教堂后面,到那座挂满了各式锁头的霍恩佐伦大桥去拍教堂全景。
不过,因为朝向和光线的关系,从大桥拍教堂最好是安排在旭日初升的早上和白天,我们傍晚去拍,就只能是拍剪影了。
第二天一早,匆忙吃完早餐,少年便拉着我直奔教堂而去,又是里里外外好一番补拍。
教堂前广场上用围挡围出一条路来,正在进行城市马拉松比赛。选手们陆续到达终点,围观者渐渐人声鼎沸,但少年无心观看。
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买了票陪他一鼓作气登上了五百零九级旋转台阶的尖塔。
少年兴致勃勃拍照、瞭望,自己去跟塔顶服务台坐着的老帅哥换了硬币,投一欧半,然后到机器上自助手摇压出有大教堂图案的纪念牌,忙个不亦乐乎。
下塔的时候,少年显然感觉到疲倦了,说:“我知道为什么下午五点就不让登塔了,是为了给在塔顶工作的那个老爷爷留出时间,让他慢慢爬下去。他每天都要爬上来再爬下去,可真够累的。”
……
居然得出这样的判断,果然还是个孩子,哈哈。
直到我们离开科隆,坐在去往海德堡的火车上,少年还意尤未尽地边看介绍大教堂的册子边说:“科隆大教堂我还没看够呢。”
看着他依然雀跃的神情,我不由欣慰地想,所谓艺术是相通的,此言诚不我欺也。我家少年这一代动漫青少年,不是宗教信徒,也不具备欧洲历史文化背景,但他们并不缺乏对人类建筑艺术的本能感受力和对美的鉴赏力。我暗自庆幸因为受那个导游的启示,没有“剧透”,只选“切入点”,让他对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有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不过,当我说起当年导游如何享受我们一票人的极度震惊时,那个半大男孩漫不经心的不屑嘴脸又回来了,他违心而又嘴硬地评价说:“哼,导游的恶趣味。”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众人皆醒我独醉
:众人皆醒我独醉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3/24 21:39:3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3/24 21:39:33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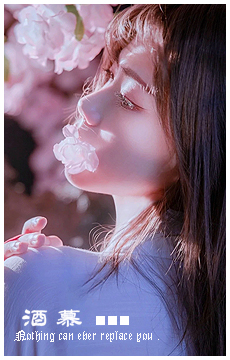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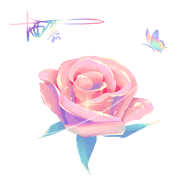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6 届
:风云0-6 届
 Post By:2023/3/24 21:50:3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3/24 21:50:3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我花开后
:我花开后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3 届
:风云0-3 届
 Post By:2023/3/24 22:02:5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3/24 22:02:5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23/3/25 15:19:0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3/25 15:19:0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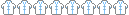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5 届
:风云0-5 届
 Post By:2023/3/25 19:12: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3/25 19:12:21 [只看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