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复行行
——在故事里,走进落日
是日尚早。独自一人去阳产土楼。
这是我所走过的最蜿蜒的盘山路之一。
深山里的村庄,土墙灰瓦,石板小路生满绿苔,有与世隔绝之感。
却又怎可能隔绝呢?
进村便有当地村民一路殷勤相问:要导游吗?皆是老人家,鬓发花白,背弓,让人实在难以说出拒绝的话。
遂与一位老伯同行。一路絮絮说着村中故事,也说他七十多年的人生履历。
十八岁当会计,六年后做出纳,管钱管账又管人。八十年代做族长,并村之后不做了,也闲不住,成了一名“导游”,带南来北往的人逛土楼,聊天。漫长一生,也不过几句话就说完了。待想细问,竟也无可相询。
人生匆促不过一段盘山路的时间,弯折曲绕,回首几人记得来路?
走到村里曾经的小学校,我停下来久望,他便跟我讲起:三年前学校就停办了,村里娃娃都要去深渡镇里上学,周一去,周五回。见我感叹,又说:村子里人越来越少了,近的,去深渡镇;远的,去杭州,去绍兴,年轻人都走了。以前村里三百户人家,一千八百多人口,现在只有一百多户了吧……
我看着他饱经风霜的脸,想:当这些老人在风吹雨打中离开世界,这里保存了三百多年的、二百多年的、一百多年的土楼群,会不会逐渐也湮灭在岁月的风沙里?那些被人们当作故事的故事,如同浮在风沙里的一颗尘埃,随着离开世界、离开土楼的人们,终有一天也会尘埃落地。
翌日,没有特别安排的地方,乘船至新安江山水画廊。
水面清且阔,风在耳边,喧嚣落尽。我穿的少,却还是在甲板吹了全程的江风。
画廊无甚别致。天下画作无外鬼斧神工、中规中矩之形容。我只透过画作,看我目光所不及之世界。
在樟潭渡,有一棵极高大的,据说已有千年的樟树。
围观的人很多,都在惊叹它的繁盛,我只惊心于它的伤口。即使活了千年,它还是带着这么一道伤,永远不能消失和愈合的伤。
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样惨烈的伤痛都没有击溃它,它用自己的方式与其共存,才有了这样的千年屹立,不倒不死,热烈嚣张。
最后一站,鱼梁坝。
我喜欢这里,我永远喜欢看人类对抗自然的伟力,喜欢时光和长河同时滔滔流淌的感觉。
我不能用具象的词语形容目之所及。
黄昏云朵正美,我心亦沐浴美之光。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弦音在彼
:弦音在彼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4-0 届
:风云514-0 届








 Post By:2023/12/4 21:20: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12/4 21:20:1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占卜师
:占卜师
 :薛副将YG
:薛副将YG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4-7 届
:风云514-7 届
 Post By:2023/12/4 21:22:0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12/4 21:22:0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4-3 届
:风云514-3 届












 Post By:2023/12/4 21:22:4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12/4 21:22:4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刘成YG
:刘成YG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4-8 届
:风云514-8 届
 Post By:2023/12/4 21:43:1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12/4 21:43:1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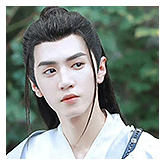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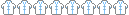
 :谢韫YG
:谢韫YG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4-5 届
:风云514-5 届
 Post By:2023/12/4 22:10:1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12/4 22:10:1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一世安宁
:一世安宁
 :谢危YG
:谢危YG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4-2 届
:风云514-2 届
 Post By:2023/12/5 11:39:0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12/5 11:39:05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