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
三十年前的湖好像比现在宽阔。小小的我站在桥上,远处湖岸杨柳看不清一丝一绺。微风像女孩子的手,牵着柳树绿色的裙摆,荡出湖面上的波纹。在波光粼粼处,花色的泳帽时隐时现。偌大的湖面找不到海鸥的踪迹。我只好从桥上滑下,用这种方式填补一整个下午的失望。
不知怎样形容杨柳。总之,春天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就像是湖面上偶尔出现的鸥鸟,不会以我预想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春天。
海鸥是一幅壁画,准确说,是用拇指盖大小的瓷砖拼贴成的马赛克壁画。从记事起,这幅壁画就镶嵌在少年宫的墙壁上。周六午后,我坐在父亲自行车上,习惯性背过脸,不愿直面湖面反射出的阳光。在车轮规律性的旋转下,周期性陷入煎熬。
我实不情愿参加围棋培训,这并不是一项有趣的游戏。可能幼小的心灵装不下那么多繁杂的规则,亦或者小小的棋盘局限了漫无边际的想象。我讨厌回合制围剿拼杀,一整个下午都需要注意力集中在方寸之间。不能率性地将所有棋子快速铺满整个棋盘,码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老师发觉到了我的煎熬。那是用棋子铺排成的黑色军舰,舰舷上两只白色海鸥振翅高飞。带着老师的教诲,父亲领着我离开少年宫。出门前,我最后一次站在壁画前,我要和它告别。此时的壁画俨然一张巨大的棋盘,每一粒瓷砖都像是棋子嵌入墙中。我奔出门外,绝不学那壁画上的海鸥。
学习高尔基的海燕时,我早已了解并不是所有的鸥鸟都叫海鸥。那时常去市中心,期间多次经过少年宫,与当年差不多温度的风拂过脸庞,我长大了,湖边的杨柳依旧荡漾着小时候的裙摆。我揿着车铃,背过脸去,不愿直面这座校外机构带给我的煎熬,甚至暗自开心,嘲笑起来往的孩子们。这时候,我肯定长大了,并不会觉得湖面如儿时般宽阔,更不会在桥上停留,把桥面光滑处当做滑梯。
许多年后,当我驾车穿过钢铁丛林,远处的垂柳在一栋栋高大建筑的掩映下,失去了原有的比例。
少年宫的壁画依旧保持着上个世纪的模样。轻轻抚摸壁画上雨水冲刷后的斑驳,海鸥失去了原有的光亮。两只老鸟陪伴着那艘还没有退役的军舰,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包括我。等待的过程充满局促和不安,我紧张地看着孩子蹦蹦跳跳从少年宫教学楼中走出,手中拎着一张画。她笑了。
我牵过孩子的手,带她去桥边,去滑滑梯,做我儿时的游戏。孩子摆了摆手,她说,她要坐在桥上继续没有完成的画,画海鸥。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人间烟火煮清欢
:人间烟火煮清欢
 :破碎星空
:破碎星空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6-4 届
:风云516-4 届










 Post By:2023/12/26 21:28:1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12/26 21:28:13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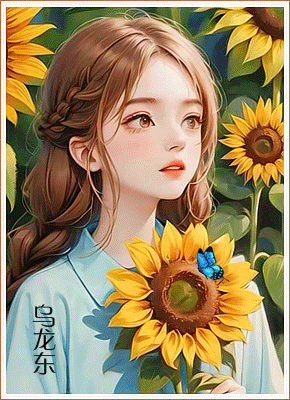 缘起,我在人群中看到你;
缘起,我在人群中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