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笙
像雾似的雨,像雨似的雾。
飘飘洒洒,从夜里一直落到天明,且没有要停的样子。
老虞头关上窗户,视线在昏暗的屋子里游移了会,西面墙上挂着本老黄历,他走过去,习惯性地撕去一张。哦,三月初七,他看到日期上有红笔画了个圈,轻轻念叨了一句,似乎想起什么,去衣柜里翻出个铁皮盒。盒子锈迹斑斑的,该是有些年头了,盒里有张皱巴巴的旧报纸,一张泛了黄却依旧平整的奖状,还有一沓封了口贴了邮票的信。他抽出一封小心翼翼揣进口袋,想了想,又去五斗柜里捧出个精巧的小木盒,把里面的东西攥在手里,随后披件雨衣出了门。
这条巷子弯弯绕绕一直通往后街,这个点还早,又下着雨,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老虞头孤零零的脚步声在小巷里清澈又模糊的回响着,与他踽踽而行的背影很是般配。
老虞头住在这里有些年头了,曾经围着他讨棒棒糖吃的小屁孩们,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小屁孩,原本挺拔的脊背慢慢弯成了一张弓,一些自以为的铭心刻骨也渐渐淡出记忆,只残存一些似是而非的轮廓和碎片。
很多年过去了,小城外的世界日新月异,小城变化却不大,水乡古镇的标签,注定了它必须保留些古旧的成色。河道上的乌篷船,穿蓑衣戴斗笠的船工,就连河边洗菜的小媳妇,都是蓝印花布衣配着绣花鞋。这满目的旧色,哪怕只是人为做旧,都让小城平添几分慵懒祥和的味道。
后街的拐角处有一只邮筒,新上的绿漆,和周边那些做旧的老物件摆在一起,颇显突兀。老虞头也一样,眼睛里总时不时闪过一些炽热和迷茫,那是一种罕见的眼神,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仿佛隔着很多深邃又迷乱的东西。
路过阿毛烧饼铺时,小夫妻俩正在卸门板准备开门做生意,那种夫唱妇随的安稳和惬意让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啊,普通人的日子就该这么乐呵呵的过。想到过日子,老虞头又陷进一个懊恼又痛苦的黑洞: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的媳妇,孩子他娘,怎么就忍心抛下他们爷俩,离家出走那么多年,渺无音讯。
◆◇ 余生
远远望见邮筒时,老虞头咧嘴笑了,似乎那不是邮筒,而是一个天天念叨着的人。每年的三月初七他都会来这里,用近乎虔诚的神情朝邮筒里投一封信。刮风下雨,头疼脑热,从未间断。这只邮筒仿佛成了他的蓄电池,生命之树从茂盛到凋落,枯叶落在青石板的缝隙里,又长出些嫩绿的青苔......
“那人”近在咫尺了,老虞头稍稍加快步子,还未收拢的笑意却在几秒后僵在唇边:几尺开外,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正蹲在地上玩玻璃弹珠。男孩的身后,有辆小摩托正拉风地驶来。车主一手打电话,另一只手扶着后座上绑着的一堆小山似的货物。
仿佛有股寒流迅速爬上他的脊背,并顺着血液流遍全身。
“儿子......”他大叫一声,本能地扑上去,一把将孩子推开。他的雨衣被摩托车的车把挂住了,因为车速太快,摔倒后又被拖移了近十来米,后脑勺重重地撞在邮筒上。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刻,他的意识仿佛元神归位般清晰起来,他下意识地握紧手,还好,瓶子还在,完好无损。他想起那个手握玻璃瓶,在风里轻盈舞蹈的女孩,她说,喜欢牵着他的手在风中漫步,听风歌唱,她说那是一种把幸福和浪漫装进小瓶子里的感觉。为此她还买了一只漂亮的水晶瓶,特意让店家刻了四个小篆:虞笙,余生。
老虞头蹙了蹙眉,用手揉了揉被撞的后脑勺。他猛然想起,二十年前的今天,妻子楚笙死于一场车祸,除了给他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虞晓笙,还有一张市府颁发的见义勇为证书。
半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进后街,医生把他抬上车时,发现他脖子上挂了张小卡片:家父虞平,55岁,血型AB型,阿兹海默症患者。家住青溪老街78号,联系电话139XXXXXXXXXXX。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518哨蜜
:518哨蜜
 :宴爽SY
:宴爽SY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8-0 届
:风云518-0 届


 Post By:2024/1/18 21:34:0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1/18 21:34:0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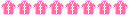

 :神之一首☆妖皇
:神之一首☆妖皇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662-1 届
:风云662-1 届








 Post By:2024/1/18 22:24:3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1/18 22:24:3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8-2 届
:风云518-2 届



 Post By:2024/1/19 14:36:3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1/19 14:36:3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