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浮白》
人生的归途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是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还是风烟俱尽,天山共色?
于我来说,是元好问的“醒来明月,醉后清风。”
一
苍生须夷,百代成山,而浮生如梦如附何体呢?
席慕蓉说,火车飞驰而过时,闭上眼,就错过了这一路旖旎之诗。而只有睁开眼,看着窗外这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才能看到的嵯峨或奇骏,这本身就是一种诗意。诗人在这份诗意里,是诗歌的另一种表达:悲悯,沉思和摆烂。
每一个的时光都是手上的老茧,破碎成山河森林,蝼蚁苍山。过往的时光里,忘记了金戈铁马的激昂,开始等待、奋斗、观望和离开。那些我们为之奋斗的少不更事或糊涂年华,慢慢地开始在春天的第一片梨花上绽放,最后沉淀。最后我们都活成了这山河里的河流,红尘里的过客,只能看着山山海海,如一页轻舟,过万重山,到流放的地方,仕林而下,青染白霜。
长大后,心中的梨花已然凋谢枯萎,最后依然是满目沧海,枯木雪后。最终的驿站,不是官谍文书的喧嚣,却是渭城的烟雨,一城一马,一笛一街,终是马放南山,将归府邸。回首时,新花老树,又都不是当初走马终南时的意气风发。倥偬与从容之间,有趣的灵魂和苍老的容颜,也化着一杯浊酒,举杯千山无一人,喝干之后,就是天涯,留下的或许更多是一声长叹。
红红翠翠的闹市里,找不到惊鸿一瞥的飞燕穿过王谢堂前,一身长衫之下,隐约可以看到当年书生寒窗苦读的影子。瀚海沉沦,烛尽灯灭,一尺案牍开不了千里江山,最后枕着夜雨,偶听窗外,才发现此生已经被压榨得惴惴不安,于是疲惫和茫然,如芭蕉之秋雨,滴漏到天明。于是,白发苍髯,知影二三,在偏安一隅里患得患失。
这当是一面苍白的栖迟,如若要满山毰毸,或心有暄妍,则当如《新青年》创刊词中的曜灵:如初春和朝日,如百卉之萌动。
如此,当才有徐熥在《与瀚公宿绿玉斋》中言:
对坐空山天籁寂,满林花雨月明中。
二
浮生之芳草,灼天时之爇,但还需日夜濯灌。
竹斋眠听雨,梦里长青苔。那是枕山栖谷的阒道风范,琨玉秋霜的背后,其实是耽独寂寥和汪洋恣肆,如果坚持要为自己的人生刻画出一抹葳蕤的境地,那么就算最好的桃花绽放,也能感觉到动如脱兔静如秋叶的安逸之美。
《诗经·小雅·伐木》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深谷里的鸟儿飞到枝头,用动听的声音呼唤同伴。鸟儿尚能飞出深谷,期待同类的弦歌不辍,而不是懒卧山川,任凭菀枯,如若此,则何能跳出藩篱,绪风云杪。
或许已经想不起曾经奋笔疾书的纶巾雄发,或者忘记了少年时课堂上的怀瑾握瑜风禾尽起。于是,梧桐夜雨成为靡言,山林桃花成为归隐,当年的梦想丢到梦呓里,随那万古蛮荒的大地,一起雨膏烟腻。
勤参念,才能红尘不染;芳草之森郁,自花泥入土,天英落地,才能身如介子,藏得须弥。
不然,则弦歌途断,心老天山,一世泯然。
三
《周易》蒙卦云:山水蒙,艮为山,坎为泉。
潺潺山泉奔流出山,必将形成江海,正如蒙稚渐启,又山下有险,因为有险停止不前,所以蒙昧不明,事物之初始,必然蒙昧。
治其之道,在于跳出蒙昧,遂成大统。
春风梨花一处香,娇柔暄妍之态,则为大地之澄和、之纯清、之滋生供养,方有春色瑄瑄如华盖,惊动山河。人皆如此,愚钝之顽,豆蔻之娇,须有春华秋实的秉性,方能写秋不见秋,踏春见山色。
之初,始于蒙泰,当“还应毫末长,始见拂丹霄。”如若无积厚之凹,站立山头,让那红霞染了天际,此生虽丽,却如楼台半壁,悬空无立。
人之于天地,蝼蚁苍山,应该善意地对待万事万物,哪怕只是一片绿叶,大地也记得曾经的郁郁葱葱。灵魂的最深处,在红与黑的交合中,往往藏着通往天堂的路。
天地需要一个理由,来培育原生态的生命,不管你痴念与否。
当春天闻到青草的芳味,蓬勃的意气就滚滚如流,蓊郁苍生,那是红尘之外,对生命的一种赋予的丹雘。
这便是:把乾坤收入,篷窗深里。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8-0 届
:风云518-0 届
 Post By:2024/1/20 21:33:1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1/20 21:33:1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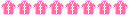

 :神之一首☆妖皇
:神之一首☆妖皇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662-1 届
:风云662-1 届








 Post By:2024/1/20 21:35:5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1/20 21:35:5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8-2 届
:风云518-2 届






 Post By:2024/1/20 23:02:2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1/20 23:02:22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