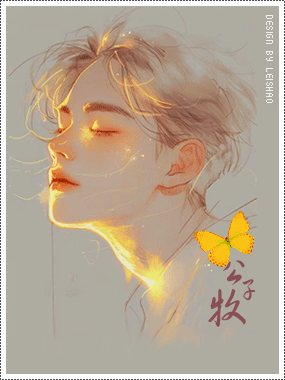多年前,我有一本迟子建的小说集《向着白夜旅行》,草草看后,并不觉得多么喜欢,但觉得这个作者很有趣。
不是所有女作者且很年轻的女作者都能有趣的,让她们空灵、优美、沉郁,甚至阴暗都更容易些。也因此她们制造出的文字若不无病呻吟,自戕自怜,就是愤世嫉俗,针针带血。
迟子建却是有趣的——并且这种有趣完全有别于男人的贫嘴或是滑头,也有别于那种正式意义上的“诙谐”,或者“幽默”,就只是简单的有趣,本质上非常天真,然而又必须非常敏感的人才能信手营造出这般况味。
后来读过她的小说《花瓣饭》,这篇小说的名字和迟子建的文风珠联璧合,两相辉映。花瓣与饭,最艳丽的与最朴素的,最浪漫的与最平实的,精神世界里最绚烂的焰火与现实生活中最安稳的土壤,它巧妙融合。不,在她心里,它们从来都是相依相存的,所以才能浑然天成,滴水不漏。
这篇小说里一样也有着摧残,有伤害,有恐惧,有灰暗,她只若无其事,轻描淡写,使一切又回归了美与爱。
美与爱,在她笔下是多么温暖的两束强光,什么样的阴暗还能存在?
最近又买来她新编本的散文集《我的世界下雪了》,年少时曾经很匆促地看过,如今再看,依然是纯粹的脚踏实地的美,邻里、动物、家什、往事、永远的乡愁北极村,美的华彩纷呈,浩瀚无边。像自黝黑的土地上蓬勃生长了红的高粱、白的棉花、黄的稻谷,生活的本质依旧朴素,却在她的文字里迤逦成一幅华丽精美长轴。
无可否认,她的文字依然有趣,但我忽然明白,这有趣绝非刻意营造,而是随心而来。我想,这个集子里的每一篇散文,也都可以是一首儿童诗,那种失传已久的儿童诗。
但有一篇像一束破空利箭,带了最深痛的悲哀直袭而来——《灯祭》。
“我愿意请他回来,而永远不希望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朝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字字都在滴血。
读这篇文章,我的眼睛湿润了。“国难”遥远,“家愁”太近,我因深爱自己的父亲而体恤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儿,并因这个女儿对父亲的深爱而直面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恐惧——如果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也会有着和她写下这段话时一样的心情……
她写《灯祭》的时候是28岁,这篇文章也曾收录在另一篇散文集《伤怀之美》里,但读《伤怀之美》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那么年轻,哪里懂得岁月的一路奔波,哪里知道悲欢与离合?如今是稍稍懂得了,并十分知道珍惜。
在她的另一篇散文《棺材与竹板》里,又看到有这样的句子:直到我中年经历了婚姻的变故之后……我并不能很好地明白,但“中年”这个词和“变故”一样,让我悚然而惊——她出名那么早,十几年的阅读与“神交”让我固执地将她的年龄停留在最初读她的那个时候,停留在和我相仿的时段,并一直固执地将她的心理年龄停留在孩提,但她自己说,“直到我中年经历了……”原来我跟着她踩下的脚印一路走着,已经看她从青年走到中年,如今发现,她和我年龄、经历的鸿沟越来越深。
后来,我看到钱红丽的随笔《你在读什么》,遂明白了“婚姻的变故”——中年的迟子建又经历了丧夫之痛。
《木匠与画匠》里她还写了新房的装修,喜气洋洋,小妇人味道十足。而松香未散,那人已经不在,心火烧火燎地替她疼起来。自内心,早已一厢情愿地觉得和她,不仅仅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她,似乎就在自己身边,一个既有趣又极浪漫的孩子。
这本书里有她的照片,每张照片上她都在笑。有一张是东北辽阔纯净的雪地,她穿了大红的羽绒服(黑白照片,但我相信她的衣服是红色的),笑容无比明亮。我久久地凝望她的笑容。
——省略掉一切人生中必然会出现的沉重、寥落和苦难,这样明亮的笑容。
最明亮的文字与笑容,抵御生命里的黑暗。
见过北方寒冷冬天,屋檐下长串长串悬垂的冰凌吗?极晶莹到凛冽,极华丽到夺目,极剔透到孤寒,但,从不让人觉得冷,只让人想起童年,想起家,想起游戏、笑声、温暖,想起春天。
她的文字给我温暖,我希望她的心灵里一直住着春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4-1-29 14:32:45编辑过]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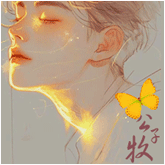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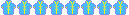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1/29 14:31:31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1/29 14:31:31 [显示全部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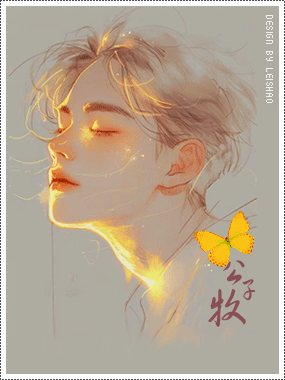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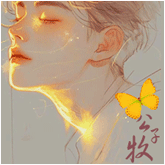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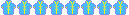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1/29 15:25:13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1/29 15:25:13 [显示全部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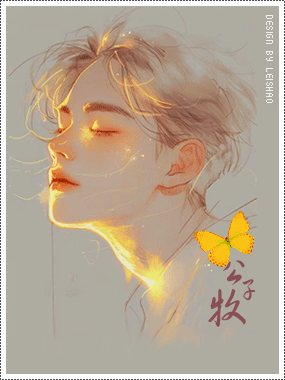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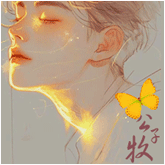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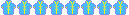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2/2 23:43:4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2/2 23:43:46 [显示全部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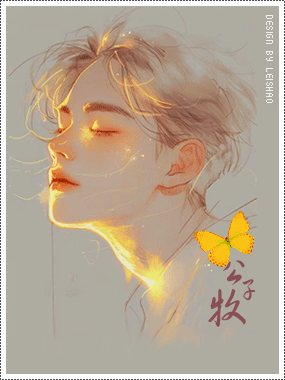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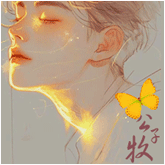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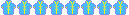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2/2 23:44:21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2/2 23:44:21 [显示全部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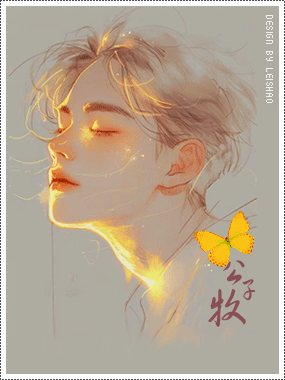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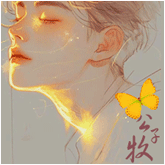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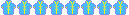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2/2 23:46:17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2/2 23:46:17 [显示全部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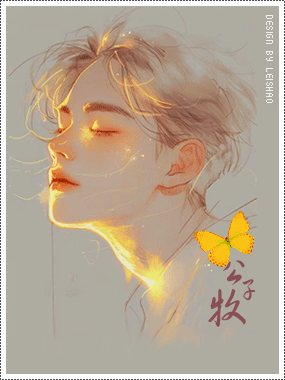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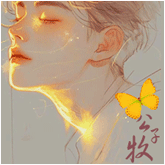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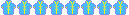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2/26 16:38:38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2/26 16:38:38 [显示全部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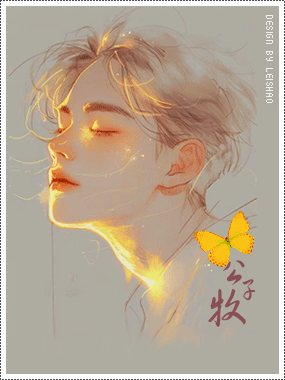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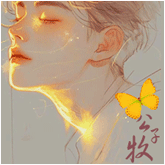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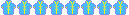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2/26 16:40:43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2/26 16:40:43 [显示全部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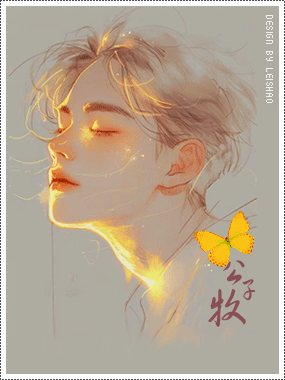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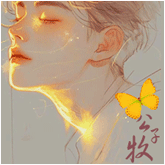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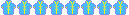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2/29 19:02:1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2/29 19:02:16 [显示全部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