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是树木留在岁月里的记忆,也是生命的烙印,一圈圈记录了树木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历程。
树木与人类相伴相生,每一棵树皆有其独特的韵味。它们以不同的姿态站成不同的风景,支撑起每一道风景的则是生命的力量。
写到树,谈起树,我的记忆中少不了房后那一排杨树。
六岁那年父母带着我和弟弟从老宅分出来,搬到了新盖的房子。正好房后是一条大街,大街中有一条人工渠,所以这条街特别宽。有几家邻居就在房后种了一排杨树,刚种的小树苗只有小孩胳膊粗。
我家东院的邻居两口子是教师,男主人姓田,对于树苗精心呵护着。那时候的孩子们特别皮,小树苗总是被折断枝杈,甚至被折断主干。于是,田老师便用木棍圈成围栏将树苗保护起来。别的邻居也纷纷效仿,但是小树苗依旧少不得受伤,尤其在刚长出绿叶,枝条可以拧成哨子的季节。
就这样小树苗伴随着整条街的皮孩子长大,不记得从哪年开始,皮孩子们再也够不到杨树的枝条。几年的时光,树干已经很粗,夏天树冠遮起大片的树荫。邻居们扎堆在树下乘凉。皮孩子们也找到了新的乐趣,在树干上刻字。
一条街十几家,每家两个孩子,年龄也是相差无几。免不了磕磕碰碰,男孩子们打架更是家常便饭。女孩子相对心思稍微多了点,今天不和这个玩,明天不和那个玩。男孩子打完架,又少不了家长的一顿泡揍。“仇”就这样结下了,墙上,树上则会留下骂“仇家”的字迹。常年累月树干上留下无数伤疤,却不影响树木长成材。
随着皮孩子们长大,杨树也长得特别粗了。女孩子陆续出嫁,男孩子陆续娶媳妇。与之的连锁反应便来了。二十年的房子已经跟不上时代,娶媳妇是不行了。各家开始翻盖自家的房子,房后的树木正好派上用场了。
粗壮的主干当房梁,够粗的枝干当椽子,用不上的树枝则只能当柴火。卸树是个技术活,将树木主干从最底端锯开,锯的时候不能完全锯断,否则无法控制树木跌倒的方向。需要剩一部分,来支撑整个树木不倒,提前将绳子拴在树干上端,锯到需要的部分后几人合力再将树拉倒。
树卸倒之后,树桩是不会挖出来的,因为挖树桩太费时费力了。这时候就能看到树桩平面一圈圈纹路,也就是树的年轮。没有去数过树木的年轮,只记得那些树桩从土下又长出嫩枝条,嫩枝条将一个树桩围在中间,杂乱无形地生长。
我想,如果只留一根枝条,它会长成一棵新树。如果全部枝条都留着,它们或许会长出十几棵歪脖子树。但是邻居们不给它们机会,只要长出来会一棵不剩都铲掉,直到树桩腐烂,根部枯萎再也长不出枝条。
邻居们前后翻盖了房子,新媳妇也陆续娶进们。时光荏苒,当年的皮孩子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这条街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父母辈,我们这辈,和现在的孩子辈。将来,孩子的孩子还会有孩子,那些树木的故事只留在两代人的记忆里。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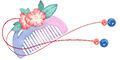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5/30 13:22:1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5/30 13:22:1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青衫烟雨
:青衫烟雨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5/31 23:56: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5/31 23:56:45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