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克坐在副驾上,用一只小枪指着我的胸口示意我上车。他那张略微浮肿,但却又显得冷硬的脸,成了此后多年我关于那天的回忆里最多的画面。
我用海星集团的冷链车载着老克,躲过了警方的关卡和盘查,然后被老克带到了一个海滨小城,在那里挨过了大半年,最后跟着他走进了老板们的会馆,那是我唯一的一次面见老板,老克带着我,就如同带着一个被情夫抛弃的女子,义无反顾的走进窑子里一般,把自己卖给了他们。
老板把脸藏在阴影里,只有嘴上的雪茄,闪着红点,他的眼睛藏在暗处,上下打量着我,像是狼在舔舐我有些苍白的脸。你确定他能行么?他问老克。
肯定行,别看着文弱,心够狠。老克说。
老克的话总是那么的一针见血,这个粗鲁,不修边幅,看似对一切都毫不在意的人,却并不缺乏直达本质的直白和深刻。
有些事,你想得深了,就会连一口饭都咽不下去。他还说。
在心灵的深处,适可而止,大约是我们这一类人平安活着的最好方式,这一点,老克一直做得很好。杀人或者被杀,生与死,他早就看得无比的透彻,所以才说出有些事想深了,饭都咽不下去那样的话。
你真她妈是杀手界的柏拉图,我嘲讽他,他嘿嘿傻笑着,却又冷幽幽蹦出一句:哲学是他妈什么玩意,哲学是咽不下的那口气,是越来越浓重的尸斑。
在之后的很多个日子,我曾不止一次的自问,如果不是遇见他,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这也仅限于假设与想像,这条路,永远回不了头,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无论是否遇见他,还是是否杀死他,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当时的我和后来的我,总会想要试一试,认命,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在他背后,我轻轻扣动了扳机,他像一头死猪一般,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我对着他的脑袋连开两枪,随后快速遁入黑暗之中。
我在暗夜中睡眠的罅隙里,无比清醒,无比清楚:所有发生的一切,无论是隐隐的憎恨,还是杀死他,以为推倒了推倒牢笼的墙,都只不过是在挣扎里沉沦,在懊悔与憎恨中持续着懊悔与憎恨。
不会有什么改变,无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这是一种很难言说的悲伤与隐痛,怎么可能如花开一般的美好,怎么可能如同小哑巴送给我的小红衣,在每个露珠的润泽中努力地张开欢欣的眼。
人和人的命,从来就不相同。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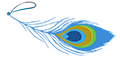
 :公主发财
:公主发财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0 届
:风云528-0 届








 Post By:2024/6/11 21:21:0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1 21:21:01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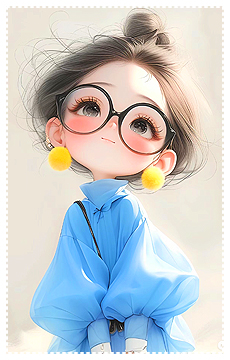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7 届
:风云528-7 届
 Post By:2024/6/11 22:42: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1 22:42:4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7 届
:风云528-7 届






 Post By:2024/6/11 22:48:3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1 22:48:3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玄族郡主
:玄族郡主
 :曜仪SM
:曜仪SM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1 届
:风云528-1 届
 Post By:2024/6/11 23:02:4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1 23:02:4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2 届
:风云528-2 届
 Post By:2024/6/12 8:10:0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2 8:10:0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4 届
:风云528-4 届




 Post By:2024/6/12 18:34:4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2 18:34:4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4 届
:风云528-4 届




 Post By:2024/6/12 18:35:1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2 18:35:1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4 届
:风云528-4 届




 Post By:2024/6/12 18:35:3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2 18:35:3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