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布袋子里,横七竖八堆放的,是一件件青铜器,有盆状的、有壶状的,居然还有铜马铜人,足足有三四十件。
由于岁月的侵蚀,它们周身上下铜绿斑驳,泛着黯淡清幽的苔藓的颜色,乍一被扯开遮挡,裸露在阳光和空气里,它们显得局促、阴森,甚至面目狰狞。
原以为打捞到宝贝,实则是一堆破铜烂铁,人们哭笑不得,议论纷纷,陆续散去。
周大老爷命人把这些破烂收拾起来,扔到后山,免得污染了河水。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覃远志说话了:“老爷,扔不得!”
那时还没有收废品卖破烂的行当,对于一些没用的铜铁物什,大多是一扔了之,无人问津。
周大老爷看了看覃远志,嘿嘿笑了,“怎么,拿回去,给媳妇置办家用?”
话一说出口,他就拍了拍嘴,干咳了两声,他知道覃远志并非懂得玩笑之人,连忙挥挥手,“用吧用吧,呃,你都拿走。”
“老爷,您不觉得,这些青铜器皿大有来头吗?”覃远志并不介意周老爷的话,他一脸严肃地把目光重新投向这些青铜器,继而拾起一件壶状器皿,轻轻抚摸,甚至是擦拭,它身上的斑驳痕迹。
那是一件长形的壶身椭圆的器皿,壶身部分有铭文,锈迹斑斑,看不出是什么年代的字。鋬上铸有兽首,也看不出是什么动物,不过像是个并不太凶猛的小兽。整个器皿的上部是敞开的,口上有流,将开放部分形成一道完美的弧度,像是一种酒器。
这件酒器虽然色泽黯淡、阴郁,但在覃远志看来,那并不是它原本的颜色。铜,本不该是“青”色,更不该是这种“青绿”色,而应该是熟铜的颜色——鲜亮的金黄 色。在细沙柔软的河滩边,在秋天的太阳懒洋洋的照射下,那是一种质感非常强的通透的金黄。古人原本就把铜称之为“金”,铜器上的铭文就被通称为“金文”。就是因为它们在岁月中沉淀的久了,才会变成 人们眼里的青绿色。
覃远志擦拭着那些斑驳,他心里忽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自语着,这不是它们的本色,这是岁月的颜色。岁月是有颜色的,那是苔藓的颜色。它们之所以带着这些斑驳的青绿,是岁月强加给它们的。
它们不知在这世上漂泊了多久,也不知在这水里沉溺了多久,它们和岁月,融为了一体。
覃远志的心里涌荡着一股说不出的情绪,他深信这些青铜器大有来头,它们身上一定深藏着年代久远的秘密。它们就像深埋于地下的种子,一旦给了它们破土重生的希望,它们就必会势不可挡,把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抽茧剥丝一般抖落。
覃远志要去探寻它们,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痴迷地捧着这件青铜器,他仿佛呼吸到了,那久远年代的味道,就连它们身上斑驳的痕迹都透着湿润的泥土的气息。
哦不,那是酒的气息,芬芳浓郁,在时间中长存,越久越香,他甚至听到觥筹交错、鼓乐相协的声音,隐隐传来。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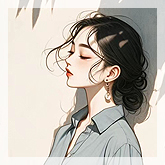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0 届
:风云530-0 届







 Post By:2024/7/11 21:08: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21:08:0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5 届
:风云530-5 届
 Post By:2024/7/11 21:09:0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21:09:0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马仙洪BX
:马仙洪BX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7 届
:风云530-7 届







 Post By:2024/7/11 21:10:3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21:10:3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7 届
:风云530-7 届







 Post By:2024/7/11 21:12:3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21:12:3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7 届
:风云530-7 届







 Post By:2024/7/11 21:12: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21:12:4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2 届
:风云530-2 届
 Post By:2024/7/11 21:21:1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21:21:1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陈朵BX
:陈朵BX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7 届
:风云530-7 届
 Post By:2024/7/11 22:12:2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22:12:2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0-5 届
:风云530-5 届
 Post By:2024/7/12 1:06: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2 1:06:1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