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老为敬>
今年开春后,因为老宅要重建的事,舅舅来找他大姐商量,也就是我的妈妈。等敲定了紧要的几桩,喝了口茶,又照例放下几张购物中心的储值卡,舅舅便赶回去了。
他前脚刚出门,老妈就拿了我的包,翻出钱夹子,把卡塞了进去。
“给你包里放了几张储值卡,回头记得少买垃圾食品,尤其薯片!”
我从书房探出头来,看了看包,看了看妈,“嗯……”一声,又坐回电脑前,略带愧疚又心安理得地做了苏明成。
其实我跟苏明成算不得一路货,但有一点倒是一样的,就是妈妈特别宠溺我,我也非常疼妈妈。
去年中秋那会儿,妈妈超市买东西回家,直到过了有大半天时间,我问她要自助餐抵扣券她才发现,手包落在超市的推车上。老妈急的立刻汗都滋出来了,多少卡和证件。还有今天放进去的一个红封袋,里面整好五千新钞,是打算派用场的。
我一秒没犹豫,拉上老妈飞快赶到超市。所幸结果有惊无险,管理推车的安保捡到手包后放在了服务台,我们核对完身份,签好字便拿了回来。然后我跑去找捡到我妈手包的好人保安,我一定要谢谢人家的,不止是钱和证件失而复得,最重要的是我妈的心情。如果包没找回来,她说不定会难过自责好一阵,肯定晚上都睡不好了。与我而言妈妈的开不开心,身体好不好,绝不是多少钱可以衡量作价的。那个好人把我妈妈从万分焦虑的边缘拉回来,更给予了那份世上还是好人多的温暖感,才是我最最看重的。
可惜我们来的晚了,已经换岗下班了。我先让妈妈回家给书呆子老爸做晚饭,自个去找超市的领导,要到了那个好人的地址。在超市里买了两盒月饼,我立马就上门去郑重地感谢了那位安保大爷。
打那以后,我跟妈妈说,我们要买东西只在这里了,员工和领导都那么好,也是全市最大的,旁的不去了。
今次舅舅给的卡又是这家的,我第二天就愉快地去给他们添砖加瓦了……逛了一两个小时,堆成小山的一推车,当然大半都是上网游戏时吃的零食。
“唰唰唰”,刷完卡,大包小包满载而归。出来走在霓虹耀眼的**广场,面对来来回回翻涌的人潮,我这个死宅,似乎略微有些不适。在我想迅速逃离时,看见音乐喷泉边,矮矮的石墩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大概并不担心被飞溅的水珠淋湿,一动不动地坐着,保持着微仰的姿势。她像个雕塑一样安静的存在于这迷幻的人海中,除了脚下的铁盒子,证明她应该是个乞丐。
这个铁盒与她仰着的头,如同卑微与骄傲的奇异结合体。她眼里没有哀怨或是控诉,有些迷茫地望着远处,远处唯有闪烁的灯光,和高楼大厦之间隐约的一小块模糊的夜色。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有没有家或者孩子。稀疏的未曾全白的头发,看起来稍稍有些凌乱,但暗红色的衣服却显得干净笔挺。而满是褶皱的手放在膝盖上,夹着一根烟,烟头被风吹着,忽明忽暗。那画面竟让我想起了老年的杜拉斯,嗯,是有那么一点儿像。也许这个奇怪的乞丐也有一个不能忘怀的情人,谁知道呢。
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杜拉斯”,便快速离开喧闹的广场,我要回到我的书房,专属于我的世外桃源。
回到家,不出意外收到老妈的一顿教育,劈头盖脸的“不能吃”,“不健康”,“太不让我省心了”等等等等的老和尚念经。老妈的经还没来得及连绵不绝,就已经被我关在了书房门外。
核桃仁、牛肉棒、酸奶、薯片……我像摆放祭祀物品一样,认真地为它们在书桌上找到了最好,最趁手的位置。然后打开电脑,我这个对夜晚重度依赖的人,开始两眼放绿光。
启动,自动登录,一排闪跳的提示消息,再一个个点掉。那个十年的人生导师,头像依旧暗着,如今我们很久才会联系一次。得了无爱症的他,是否也在某个广场或公路边叼着烟,凝望远方,思考人生。周围的兵荒马乱似乎从来不会对他有所影响,可惜,这么久了,还是没学到他的这点本事。唉,进段不易,排位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大概只会是个佛系法师。
不管何种修炼,总是要先储备能量的。我撕开盖子,深呼吸一下薯片的经典原味,死宅的美好夜生活开始了……
等我几局游戏打下来,微博、知乎豆瓣加论坛全遛一遍,又已半夜。但无论多晚,临睡前习惯点开自己的群看一眼。
今天除了一个晒自拍桃花照片的,没什么有趣内容,这帮伪文青跟他们沉迷于游戏的群主一样,日渐堕落。想想以前,一个个都是伏案疾书,按期写作业,互怼互助的大好文艺青年。现在全玩跨界了,有投身八卦界的,美食界的,摄影界的,股票界期货界的,咳咳,全门类。前儿个跟歌灯说起,自己有一帮伪文青死党时,心下还有点点小欣喜。可再看看这群逗比青年,也是无语凝噎。
就像今天发片这位,作为群主的我批评她色调角度存在各种问题,好好的桃花拍成了棉花田。她居然都不搭理我,自顾自刷屏。呜呼,贵群主悲哀,熟归熟,总要给我点面子的啊。
说起来,与她相识十年都不止了,大概是08年的时候,某天半夜,某个群里。根本不认识的她突然喊我唱和,那时的我初生牛犊,who怕who。结果一来二去玩到了两三点,居然还玩得有点猩猩相惜了。这十余年,她这个正规军和我这支野路子,断断续续的竟然没有分道扬镳。到现在群里时不时发些繁体作品的也就她了,虽然会立即出现一排队形整齐的白眼。她照旧时不时做做搬运工,转一些联想,可贵群主只擅长变态题,她一道道的典故不能秒下时,总恨不得踢她出去面壁,面子这东西,我也不要了。
她还是群里最著名的淡定君,不管我们怎么怼怎么白眼,从来不妨碍她独自蒂花之秀,永远是一副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时候,和我同仇敌忾的是认识比较晚的老穆。他算是名校毕业,又进了国内排得上的大企业,游走在才子与痞子之间的毒舌君。再说他肚子里墨水确实也有点,有个做大学问的老师,国学典故什么的,他跟淡定君倒是能比划比划。不过一般情况没几个回合,他就会开启蜜汁毒舌,纯掰扯学问那功夫,他宁可去看美女。好像也出现过二般情况,老穆极其严肃地跟我们说,他要写小说了,而且已经写了好几章。只是过了好几个月他都没有再显摆,我们也就知道结果了。“太监”了并不影响他的高大上形象,他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在球场的飒爽英姿。有时脖子上还挂着奖牌,一脸的得意,看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你的发际线又高了。
就算老穆的颜值已经不抗打了,在群里他还是有个铁粉,一个我们这帮人里,硕果仅存的目前还在文学的芳草地辛勤耕耘的妹子。她多年前曾跟我一起在别人的山头默默干活,那时还没看出她是一枚极仗义的女汉子。直到我一个暴脾气,拉起大队人马自立门户,她是最先几个二话不说跟我走,撸袖子一起干的。那时的我们多么热血,多么天真,费尽所有的心血,只为撑起自认为的完美的文学世界。所谓的梦想,所谓的同道,最后被我尽数辜负。当营运商问我时,我连一份数据都不想保存,那些心血连同光阴一并,没能留下一点痕迹。她和当时的那么多伙伴,从未有过埋怨,反而到今日还会偶尔怀念当年的美好。后来我一场大病,归来再无征衣飘飘,她们却依然待我如初,一个再无斗志的我,真的不配和她们携手同行。
还有我那个就像上辈子欠了我万贯家财的师傅,他是个稽查队长,天知道有多忙。但只要我如悟空般喊一声:师傅!他就会神兵天降。接到的不管是绝句小令,或是又长又臭的碎碎念,他都会认真看完,指出错误给出建议。有次我脑壳进水,说师傅,我要好好写作了。他花了几个小时听我立提纲,还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然后,我就没然后了……
师傅在我们这帮人里属于神秘人物,平常根本看不到他,除了过年和我生日,会突然出来给我发个大红包。同样玩快闪的,还有我徒弟,会用两个马甲在群里抢红包。却往往拼起来只几毛钱,这波青铜操作明显不像我教的,不过真的也没教过他什么。哈工大的他,我这个工科学渣其实也不敢称师,再说现在的他已经脱离文青界,还正式脱单了。今年突然发了一组超美婚纱照,他的新娘,竟然看起来落落大方,极贤惠的模样。老怀甚慰,老怀甚慰。
说到贤惠,群里有个经常晒营养早餐的,更恐怖的是她365天,天天早上坚持发新闻和养生食物推荐。对于恒心严重缺失,又拒吃早餐的群主,怀疑这人不是同住地球村。也不知道她几时混进来的,又几时蜕变成了群里的神级补刀手。在敌对双方即将尘埃落定时,她总会适时地出来,以表情、动图或是极精炼语句,神评论其中一方。然后战局就锁定胜负了,她就事了拂衣去了……
但不管这些人怎么牛,都牛不过群里的红领军万能男,他是移动的百科全书。我们对他的评价是:除了不能亲自怀孕生娃,就没有不会的。他会打毛线,对,真的会。一般谁有什么疑难困惑,都是直接@他,而且保证他会给出科普式的,你满意的答案。但他做过一件很出乎我意料的事,那是好多年前,他去一个极冷清的论坛,给我注册了一个极其妩媚的ID,让我陪他玩。他起的那个名字到现在我还无法接受,如同一个字正腔圆的四辩玩起了抖音伪娘,万能君果然无所不能。
而我,什么也不能了。除了看看他们,翻翻旧时光,什么也不想做。自从他们会面红耳赤的互怼互踢后,我去掉了管理,只留自己一个群主。就像一个孤独而自由的守夜人,每晚零点钟声以后,打开那个叫回忆的世界。
他们说一个人习惯回忆就象征着老了,若可以选择,倒是愿意直接就老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时间问题,若能跳过寒暑回轮的煎熬,亦是人间快事。如此,除了寿数可以证明医学的昌明,又抹去了中间的幸与不幸。或许还可以学着三毛所说的:我们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可惜,三毛渡人却未能渡己,终究是连回忆连躯壳都通通舍去,才算是真正的解脱。
不记得谁说的,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我现在大概是在彻底诠释生命的无意义,以放过自己的名义,真实完成,青春是拿来挥霍的,不用还。
想起好久之前,我在网上发起过对一位残疾诗友的资助,身边的死党都三五百的捐上了自己的心意。我一个朋友帮他在自己的刊物发表诗词,多少发点稿费,还有淡定君把诗词大赛得的奖金也给了他。可后来朋友说,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就帮他找了可以发帖给钱的论坛,虽然钱很少,又找了朋友的论坛挂版给报一年宽带费。但最后他都不做了,慢慢地,我发现他活的其实还不如我糟糕。自己在几次倾囊之后,根本生活费都不够。那时又遇到诸多变故,比起他唱唱歌写写诗的小日子还远不如。后来便没再寄了,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再看如今的我,和一个残疾人又有何区别。花着妈妈塞给我的钱,刷着舅舅留下的卡,只在夜半时分,游走在自责与假装自责之间。唯有点开那个回忆的世界,翻检着往日的点点滴滴,嘴角或许还会微微上扬。那些一直在的,和已经远离的,有的结了婚,生了孩子,有的还在人海某一角飘着。看着他们最后的发言,日期或许停留在一年前了。还有的,永远不会再说话了。如此年轻的敖敖走了,加上自己大病,曾经感觉这世界很绝望。那些人,那些时光,悄无声息地走了,都不跟我打声招呼。
于是,我开始常常默念里美的话:有时间绝望,还不如去吃美食然后睡个觉。所以,我要将桌子上的核桃仁、牛肉棒、酸奶、薯片,一样不留的全部装进肚子里,不管有没有营养。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以无益之事,遣此无意之生。努力吃完写完,明天就有动力多跑三公里了。跑完就又可以继续美食,可以继续刷卡了。
也许在熙熙攘攘的**广场,在那个迷幻的人海中,音乐喷泉边,可以再看一看老去的杜拉斯。也可能,她不在了,换成了泉边的卡夫卡。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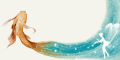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9/4/11 0:08: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1 0:08:1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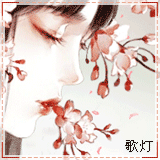




 :歌尽灯火阑珊处。
:歌尽灯火阑珊处。
 :江湖夜雨十年灯
:江湖夜雨十年灯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19/4/11 10:47:5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1 10:47:5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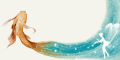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9/4/11 13:1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1 13:12: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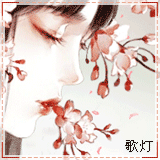




 :歌尽灯火阑珊处。
:歌尽灯火阑珊处。
 :江湖夜雨十年灯
:江湖夜雨十年灯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19/4/11 13:46:4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1 13:46:4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 勇 者 胜
: 勇 者 胜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9/4/12 22:37:3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2 22:37:3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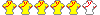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9/4/14 13:21:4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4 13:21:4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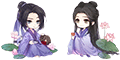

 :在渭
:在渭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9/4/14 18:24:3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4 18:24:3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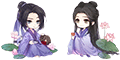

 :在渭
:在渭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9/4/14 18:25:2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14 18:25:2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月隐西楼
:月隐西楼
 :小满。
:小满。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19/4/24 10:45:0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24 10:45:0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19/4/30 22:38:3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9/4/30 22:38:34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