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春天突然就来了。
像是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在某天清晨突然来访,你尚且穿着厚而温暖的毛绒睡衣,揉着惺忪的睡颜打开门,早春阳光和新鲜空气一下子就涌进来,而在你面前的是一张多么亲切且温和的脸啊——你张了张嘴,想说欢迎回家或者好久不见,话还没说出口,她就毫无预兆踮起脚,凑上前,轻轻地、甜甜地吻在你的唇上,带着些花香的味道,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心中有什么东西融化了,仿佛长久淤积在胸口的冰雪化开了,变成温和清凉的雪水。
别来无恙。她微笑着说。我们都平安无事,各自度过了一个冬天——我们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年。
别来无恙。你终于反应过来。于是你请她走进你的家门,让她来到你的世界,或许你还会拥抱她,拥抱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其实也不一定是她敲开你的家门,也许你们会在马路上遇见,当你在路边焦急地等待红绿灯,眼前车流不息,却忽地感觉到有花瓣落在你的头顶的时候;也许会在某家餐厅里,服务员端上季节限定的饮品,这时你看到了她的名字,就想起她的面容,下一秒,也许她就会像童话里的妖精一样突然出现在你对面的座位上,对你微笑。
我向来是个对时间不那么敏感的人。念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我都会记不清这一天是几号或者周几。我对气温也是如此,很难察觉到气温的渐变。更不用说季节了,好像一切都是突如其来地——夏天变成秋天,冬天变成春天。
所以我只能这样来写春天。
关于春天,我没有多少可以说的回忆。
小时候爷爷会给我买纸鸢,带着我在体育场的沥青跑道上奔跑。我们那儿的纸鸢大多都是做成燕子、鹰或者别的鸟类形状的,我看着它们渐渐升上天空,越变越小。学校会组织春游:低年级的孩子们会就近爬山野餐,说是野餐,其实就是同学们各自带一些零食当成午饭吃;高年级就会去野炊,一个班里的孩子们分好组,组内分配各自携带的材料和道具,有带锅的,也有带食材的,第二天大队伍全副武装地出发,来到指定地点后就开始做饭,大多都是简单易做的炒年糕之类。
还有就是高中里的樱花。在我的高中,教学楼围成的天井里种了不少的樱花树,一到春天就是粉色的一片。我喜欢看日本动漫,日本人写的故事,其中但凡有些青春伤痕的味道,大多都会出现樱花这个意象,于是看着校园里的樱花,我也会觉得很浪漫。大概是触景生情,有时候我会幻想自己是某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故事才写到开头,该遇见的人还没有遇见,该发生的故事还没有发生。现在回忆起来,总觉得那时的时间过得很缓慢,缓慢而安静,像是午后的阳光浅浅地铺在走廊上,空气并不炎热,清爽的风在过道里穿梭。
大学里也有樱花,而且品种更多,图书馆下面一片都是樱花。但我那时忙于与所谓“庸碌的生活与庸碌的未来”作斗争,却鲜少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了。
如今我已经步入社会,每天步行上班,路两边种满了银杏树,秋天的时候黄澄澄的很是好看,但在其他三季就有些乏善可陈了——或许还有一些我没有察觉到的路边的小花——但对我而言,总的来说,如今春天到来的标志只能是公司里热空调的关闭或者电脑右下角的日期,这样朴素的东西了。
我对春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结。我以为,赋予这个季节特殊意义的,是过去的人和事,但并不是非要在春天遇见或者发生,只是恰好——恰好在这个季节,这个时间。而春天,她更像是一位信使,每年在固定的时间把来自过往的信件送到。
又是很久没有写东西。在朋友的催促下,鼓起勇气动笔,写的也都是浅薄的回忆,既缺乏技巧,又欠缺深度,文字也没有什么打磨的痕迹,像村口老婆婆的碎嘴,乏善可陈,听多了、看多了让人生厌。加上字符和偏离主题的内容,姑且是凑足了一千五百字,算是完成任务。
但又一想,我还是想写的。写作这个事,写的时候痛并快乐着,过了一两年再读,心里就满是怀念和感叹。或是写了随笔,给三五亲朋看,观察他们的反应,也是挺有趣的。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3/21 18:04:0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21 18:04:0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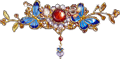

 :迟迟钟鼓初长夜。
:迟迟钟鼓初长夜。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6-0 届
:风云516-0 届






















 Post By:2022/3/23 20:11:4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23 20:11:4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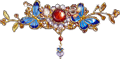

 :迟迟钟鼓初长夜。
:迟迟钟鼓初长夜。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6-0 届
:风云516-0 届






















 Post By:2022/3/23 20:13:4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23 20:13:4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3/24 10:41:5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24 10:41:5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释迦
:释迦
 :别影
:别影
 :云间月
:云间月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3 届
:风云0-3 届















 Post By:2022/3/24 11:23:5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3/24 11:23:5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