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渺
【一】山雨
淅淅沥沥的秋雨打在窗外梧桐叶上,细沉声响此起彼伏。伏案的秦苍为这动静惊扰,骤然睁开眼,才发现天光微亮,黑夜竟已悄寂逝去。
山间寒凉袭来,他只穿着单薄青衣,不禁深吸一口气。发麻的胳膊微微一动,不慎碰到近旁簿册,“哗”的一声,堆叠如山的账本顿时歪斜倾倒,凌乱坍了一地。
他静默了片刻,才俯身去捡。
门被“吱呀”打开,风雨斜侵,卷翻这满地书页。
“少帮主。”来人魁梧粗壮,就这样站在门侧,似乎对眼前景象见惯不惯,“昨晚您在泰和堂说的事,是真的?”
秦苍低着头,继续收拾着书册,慢慢道:“昨晚我说了许多话,不知道你问的是哪句?”
那人铁青着脸,用力将门关上:“不准镇江漕帮罢运,让各堂人手全都回到码头!”
秦苍手持泛黄的卷册,直起腰来平静地看着他:“常长老,我那番话,并不是下令,而是在真心诚意替弟兄们考虑。他们若觉得我讲得有理,自然不呼而应,若觉得没理,我就算将家法杖架在他们颈边,也是无用的。”
“你还说是为弟兄们考虑?!”常世雄难忍心头火,在门口来回踱,声音不由拔高,“原本我们只要将粮运到淮安或徐州,现在呢?一道诏令下来,原本该我们做的事被官军承担了,每年却又要我们长途跋涉运二十万石白粮去京城。这往返一趟差不多小半年,弟兄们又苦又累,要是再遇到风浪就船毁人亡。你说说看,这长运法再不改,是不是要了我们漕帮的命?!”
秦苍将手中卷册轻轻搁在书桌上,望着满桌账簿:“你说的这些,我何曾不明白?但我们镇江码头的情形你也清楚,年初运粮去淮安遇上大风雪,连翻十三条大船,不光血本无归,还赔钱赔粮,我父亲一气之下吐血病故……好不容易熬过那几个月,眼下才有些好转,你怎么能鼓动弟兄们扔下漕船回家去?”
“那不然呢?就由着当官的撺掇皇上改了漕运法子?咱们就该合计着撂挑子,那什么白粮也不运了,他们官军不是能行吗?都叫他们运去!”
“然后呢?全镇江府的漕帮子弟们就这样全待在家中,上百条漕船盖着草垫停在码头?一天可以,两天可以,接下去他们靠什么养家糊口?”
“只要熬得住,镇江府会把话传到京城,我就不信朝廷不怕!”
秦苍的眼中浮现悒色:“常长老,朝堂之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区区镇江停运,吓不到他们……”
常世雄没等他说罢,便冷笑道:“少帮主,我不爱听文绉绉的话!你是读过书的人,可那些写书的夫子,谁懂江湖事?漕帮人靠天靠江不靠烂纸堆里的大道理,你这样胆小怕事,只会害死镇江府的子弟!”
秦苍还想说什么,常世雄却已经愤然转身,一开门,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斜密雨帘倾洒而进,霎时间淋湿门内砖石,染上黯淡灰黑。
秦苍默默站立片刻,过去将门虚掩了,又坐回书桌前。注清水,细研墨,墨香淡淡晕洒,他却出神望着前方,直至又一阵轻微的开门声将他思绪唤回。
他并没回头,只是以眼角余光瞥视一下,继续研着墨。
来者唰唰两声甩着油纸伞,飞溅白珠碎沫。
秦苍淡淡道:“说过多少次,进屋前将雨伞放外边。”
“矫情!”玄黑衣衫的年轻人叱了一句,随手将伞搁在门旁,拍打着筒靴上的水滴,“常世雄气冲冲出去了,又是来跟你找茬的?”
“不是。”
风铃绕到书桌前,打量他一番:“那是为什么?”
他低着眉,将手中笔搁置一边:“我上次与你说过的,昨夜对漕帮其他长老和堂主讲了,他听说后自然要来骂醒我这个书呆子。”
“其他人呢?怎么说?”
“黄堂主应该是听进去了,但其他人还是意见纷杂。”秦苍神情宁静,已然预料之中的样子,“从来就没有一呼百应的时候,我知道的。”
风铃怔了怔,看那满桌书册,以及一旁信笺:“那你打算怎么办?”
秦苍摇摇头,没有回答。风铃再度看了看素雅的信笺,忍不住问:“这是要给谁写信?”
“一个远亲。”秦苍将信笺挪到一侧,“一大清早还下着雨,你怎么来了?”
风铃顿滞一下,转而嗤笑起来:“你以为我连夜从太湖到你这里?昨晚就到了,还不是想来看看你这少帮主,最近身体可好,能不能服众……”话说到一半,他看看秦苍的脸色,又忙倚在桌前问,“有空吗?今晚一起去西津渡?”
秦苍睨了他一眼:“特地赶来又是为了垂钓?你对鱼就那么痴迷?”
“不然整天窝在这阴沉沉的屋子里?”风铃随意翻翻簿册,“出去散散心不好吗?上次跟你一起去夜钓,好像还是两个月前……”
“好了好了,你先让我写完这封信。”秦苍有些吃不消他的絮叨,挥了挥手,“出去转转,或者到厢房休息会儿。”
风铃故意叹了一声,到门边拿起伞,出去了。
秦苍只回过头看看,随即凝神思索,过了许久,才谨慎落笔。流丽笔划才刚刚收止,窗外又有人轻敲,他有些不悦:“是谁?”
“少帮主,有人送来一封信。”
他推开窗,接过那薄薄信封。簌簌展开信笺,幽香晕染浮沉,而那信笺底部,恰印着迎风娇羞一朵红莲。
【二】花未眠
清晓的雨连连绵绵下了半天,到午后才止歇。
秦苍处理了一天帮中事务,直至黄昏时分,才脚步沉重地回到堂屋。刚坐下想要休息,却听有人抱怨:“你这成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体能好得了吗?”
他微微一怔,循声望去。靠墙卧榻上,风铃正枕着双臂悠闲躺着,地上还散落了书册。
“能不能别这样随便?”秦苍怫然,“好歹也是镜湖门的二当家。”
风铃嘁了一声,一下子坐起来道:“怎么?当家就要像你那样一本正经?有用吗?底下人听话吗?”
秦苍愤愤然盯他一眼,拉开椅子坐下不说话。屋内未点灯,他的身影更显灰暗阴郁。
风铃轻咳一声,拍拍衣衫起身笑道:“这就气着了?走啊,别在这憋闷了。”
他不耐烦道:“去哪里?”
“钓鱼啊!看你这记性!”风铃抱着双臂一脸得意,“走吧,西津渡那边很久没去……”
“……我还有事。”秦苍愣怔了一下,打断了风铃的话语,看他的笑意凝滞住了,又道,“看明天吧,有空再与你去。”
风铃尴尬地笑了笑:“你这人真是变了,找你出去散心都推三阻四,有那么多事务要忙?”
“我……”秦苍话才开口,门外传来唤声:“少帮主,马车准备好了。”
“好。”秦苍走到门口,回头道,“今夜别赶回太湖了,还是住西厢房,我吩咐人去收拾。”
风铃无所谓地道:“别操心了,有事就去忙吧。”
秦苍点点头,快步而去。
*
夜色初降,西津渡口花灯缀彩,嬉笑声扬。马车缓缓行于江岸,秦苍疲惫倚坐,耳畔浮沉的仍是帮众喧哗声。
清晨,常世雄从他那里出去后,便召集了手下的弟兄,到泰和堂与其他长老堂主争辩。都是漕帮几十年的老伙计了,却个个怒目以对,面红耳赤。他赶到那儿时,常世雄已和黄长老动起手来,其余人叫嚷吵闹,将原本清静的泰和堂前搅得一团乱。
“黄志齐,你他娘的就是个软耳根,自己没脑子不会想!只会听别人鼓动?!”常世雄的眼角挂了彩,鲜红血迹蜿蜒而下,更显可怖。
“少帮主讲得有道理,咱们光这样瞎闹没用,还是要另想法子……”
“他懂个屁!从小病病歪歪行不得船,扯不动帆,只会缩在屋里念书的窝囊废!要不是老帮主只有他一个儿子,这漕帮会轮到他来管?你听他的,就等着漕帮被毁吧!”常世雄吼得嗓子都快哑了。
“少帮主……”有人叫了一声,挥起的拳头、扬起的棍棒生生停在半空。
他一个人站在空旷台阶下,雨点滴滴答答打在纸伞上,连缀成线而落,溅起无数涟漪。
潮湿寒凉的空气凝滞沉郁,秦苍注视着这群孔武有力的汉子,慢慢走向台阶。
“老帮主的灵位就在里面!你……”常世雄还在大声嚷嚷,秦苍却只平视前方往堂内走。人们低声议论着,不情不愿往后避让,留出中间窄窄一条道。
他轻轻收起油纸伞,认真地放在了门外。
“矫情。”不知是哪个帮众,躲在人群间带着冷意嘲讽。
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整衣襟,拂长衫,三步一跪,直至香台。铁钩银划的匾额下,乌木托架间正放着盘龙棍,虬首仰昂,怒睛圆睁,在其两侧则是历代帮主灵位,黑底金漆,犹如一张张肃穆脸容,无声排列。
重重叩首,前额触及冰硬地面。这滋味,令他想到了那日头戴白巾眼含热泪,在此接过盘龙棍时候的情形。
青衫孤凛,磊落而起。
“镇江府众长老、堂主、帮众听令!今日起尽数回到码头,若再有人鼓动罢运,立行杖刑逐出帮去!”他攥紧沉沉盘龙棍,霍然回身,“我秦苍在此立誓,不让朝堂改变漕运法令,愿以死谢罪!”
劈啪作响的雨点重重打在堂前砖石地,寒意越发渗骨了。
……
“笃笃笃”,马车窗外响起轻敲声。
他开了半扇,蒙蒙夜色下,是犹含稚气的脸容。“秦少爷,我家小姐等你好久了!”
堤岸弯弯,浓树覆影,远方灯火烁动,烟波濛濛间,有画船静泊。
*
红莲灯在晚风中影影绰绰,映出旋转光晕。
远处戏腔袅娜,若断若续飘飞于江水间。他心绪缭乱,思忖片刻后,撩开了细密的竹帘。
灯火下,南晴婉正望着几案上的茶具出神,碧色连珠纹短衫衬着湖蓝织金马面裙,人似珠玉,静润生光。只是一抬眸,看到了弯腰进来的他,她眼里便漾出温柔的笑。
“外面不冷吗?你只穿这一件长衫。”她持着紫砂壶,为他轻斟一杯温热的茶。
“还好。”他坐在她对面,望了一眼,“你这回又是找了什么借口来的镇江?”
“看望外婆呀,谁叫你总不来南京。”南晴婉语音轻柔,娇叹之后又染上忧虑,“怎么了,脸色不太好的样子……是不是漕帮事务繁忙?”
“有点。”秦苍接过那杯茶,手心才温暖起来,“你爹从京城回来了吗?”
“还没呢,不然我怎么能那么大胆子过来?我最好他过完年才回呢!反正他喜欢跟那些官员打交道。”
“那你……”他还想问,外面蓦然传来一声响,岸上人群欢悦。南晴婉好奇地撩起竹帘张望,回头唤道:“快来啊,秦苍……”
她语调婉转,如水润氤氲。秦苍凑到窗畔,渺渺夜色间,空中烟火盛放,粉紫亮金丝丝绽出艳魅的花,纷纷扬扬坠入江雾深处。
他有一瞬的出神,记忆深处的某夜恍惚浮现,却又一晃而逝。
“美吗?”南晴婉凝望着他的清隽侧脸,轻柔问。
“美。”秦苍眼中映出那最后一抹亮色,低声回。
她静静笑了,倚靠在他肩侧。
【三】西津渡
夜深时分,云台山秋雨又至,风一阵雨一阵,萧萧飒飒缭乱了石径。
秦苍撑着油纸伞推门回院,满院漆黑无声,唯有雨滴敲打翠竹,泼珠溅玉。
他本来是走向正屋的,行了数步,忽而望向西厢房。门窗紧闭,悄寂沉静。他走过去,叩响屋门。
“风铃,那么早就睡了?”
没有任何回音。正待再问,仆人从院门外道:“少帮主,风小哥早就走了啊。”
“走了?”秦苍一怔,“什么时候?”
“您出门后,他就走了。”
他愣了一会儿,默不作声地推开门,屋内果然冷寂空荡,连包裹都没有。他坐在窗下,想点燃油灯,终究还是收回手,独留在了黑暗中。
*
自那之后,他越来越忙碌。常世雄碍于帮规约束,不敢再当面与他叫板,只是当朝廷运粮命令又来时便称病不从,连带着其他堂主也推诿不愿接受任务。秦苍连夜找了黄长老商议,才凑齐运粮的队伍。
烟波渺渺,一艘又一艘漕船迎风升起巨大的帆,往北驶去。帮众家小聚在岸边送行,哭哭啼啼,怨声载道。
这一去,不知何时还,不知能否安?
秦苍望着这一切,转身而去。
雨罢风又起,一天天地冷了下去。临近年关,他为给出船的帮众家中筹备钱粮,不停奔波游说,好几次忙至天明。洗得泛了白的蓝夹袄下摆勾破也无心去补,南晴婉从应天府偷跑出来的时候,见到他这副样子,不由心疼。
“你身边的人都不管事?好端端的少爷成了什么模样?”她倚靠在他怀里,抚着那衣衫,“我叫翠钿去买针线来,这就给你缝补好。”
“不用了。”他看看南晴婉,又解释,“若是被人发现了,不太好……”
她的眸中隐现失望,过了片刻才道:“我爹大概过完年就要回来。你……”
“什么?”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
“我们真要一直这样偷偷摸摸下去吗?”南晴婉低着眼帘,“我爹早就在为我寻找夫家了。你,什么时候去见他?”
秦苍努力地笑了笑:“我会去的。只是,你也知晓的,我这江湖人的身份必定不能入他老人家法眼。”
“那就不打算去挑明了?”她含着怨怼,侧回头直视于他,“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还不明白?那些附庸风雅的所谓才子,还有油嘴滑舌的商贾子弟,我看着就心烦,怎么可能嫁与他们?!”
“我知道。”秦苍抬起手,轻轻掠过她发丝,“我会来找你的,晴婉。”
马车辚辚,带走了满腹心绪的南晴婉。他牵着马,站在长街畔,望家家户户灯火摇曳。过了片刻,从怀中取出了一封信。
才刚展开,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声,有人带着笑意道:“好久不见,秦苍。”
他回头。
四蹄踏雪的骏马轩昂而来,马背上的年轻人黑衫利落,抬手扬起遮风帷纱,朝他展出醇澈的笑。
秦苍内心不安,却同样报之以微笑:“怎么来了?这么冷的天,我可不想再去钓鱼。”
“矫情!”风铃习惯性笑骂一声,从腰间取下葫芦,抛了过来,“尝尝,我们东太湖的冬至酒。”
秦苍接过酒葫芦,翻身上马,问道:“去我那里坐坐,还是另寻地方?”
“不去云台山了。”风铃想了想,“西津渡,走吗?”
秦苍微微一怔,还未及回应,风铃已策马驰骋而去。
他叹了一声,扬鞭追随。疾影飒沓,如电如风。
*
西津渡口已无渡船,阴沉沉云层厚压,灰暗江面波涛翻涌,似是酝酿一场大风浪。
“风那么大,来这里做什么?”秦苍皱着眉,勒住缰绳停在渡口。
“望出去水面开阔,不会觉得憋闷。”风铃拍了拍马的脖颈,转回头,“你最近还好吗?”
“就这样。”秦苍顿了顿,“上次,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自己走了?”
“你忙,我一个人待在云台山也没意思,就回东太湖快活去了。”风铃笑了笑,望向烟波浩渺的水面,“漕帮那群老东西怎么样了?还和你对着干?”
他摇摇头:“不敢当面顶撞了,但总是推诿敷衍。不过……”他顿了顿,长出一口气,“风铃,我有办法的。”
“你找人帮忙了,还是?”
秦苍淡淡一笑:“这不是江湖上的事,你不晓得也好,总之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他们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只看到眼前是过不长久的,吵嚷也无济于事。”
风铃欲言又止,过了片刻才道:“你要是遇到麻烦,就只管说。我本事没多少,能帮的,一定会帮。”
“好。”秦苍如释重负地打开酒葫芦,饮了一大口,转回身道,“走吧,找个地方避避风,将这酒好好喝上。”
*
西津渡畔画楼东,灯火幢幢影迷离。
东太湖的冬至酒入口甘醇,酒性却烈。秦苍饮尽一杯又一杯,原本冰凉的手与脸发了烫,他还是与少年时一样,沾酒便热。
醉意涌来时,许多片段便自然浮现。譬如记忆里的那场大风浪,掀翻了漕运航船,十四岁的他拼死抱住桅杆,几乎就要覆灭于冰冷江中。
嘶喊声,呼救声,飓风卷起波浪劈头打下,让他的世界一片混沌。
但他咬着牙,硬撑到底,不肯松手。他不想死。
被父亲逼迫着第一次单独押运,一路上备受异样眼光,恭敬的背后是窃窃私议。他们说他常年躲在屋里看天书,他们说他见不得阳光,他们甚至说他大概不是男人……
只因为,他不像他们一样,袒着胸膛扯声吼。气力小是错,爱干净是错,不骂娘也是错。
他的世界,始终灰暗如这滔天江浪。
唯有那一声“接着”,那段急抛而来的绳索,那个驾着小舰穿浪而来的少年,在灰暗水天间劈开一道光,随后,将他从沉陷绝望中拽曳出来。
那晚岸边,黑衣少年提出一壶酒,不管不顾就给他灌了下去。浑身冰透的他,被辣得连连咳嗽,却也第一次感到了那股从心底蓬勃滋长的热与火。
——多谢你。怎么称呼?
——风铃。他哈哈笑着骂,这破名字,女孩子似的!你呢?
——我……秦苍。
——秦苍?好名字啊!多英雄气概,一听就能成大事,担重任!
……
许是长久没见的缘故,秦苍醉后一反常态地躺在窗下卧榻,眼神恍惚地说了很多。风铃却也与往日不同,顾自饮着酒,笑着听他絮叨。偶尔提醒一句:“你上次去东太湖找我,还是去年夏天。”
“不是过年时候吗?我还看到人家放焰火!”他低声地嘀咕,闭了眼侧睡。
“搞错了还不承认!你是大忙人,忙得都没空找我钓鱼。对了我问你……”风铃无聊地摆弄手中酒杯,挑着眉梢问,“你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人?”
“什么人?”
“西津渡口,你常常等在那里。”风铃顿了顿,拖长声音瞥着他道,“可不是我盯梢,手下耳目不少,往来消息也多。听说,是从应天府来的……”
“别乱打听!”秦苍忽而烦躁起来,虽还是闭着眼,手却重重敲在竹榻上,“你怎么管这闲事?”
风铃微微一怔,不屑地笑道:“我还懒得管这些,不过是操心你的终身大事罢了……你这少堂主,什么时候请我喝一杯喜酒?”
秦苍疲惫地一哂,抬起手遮住眼,并没搭理他。
“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为什么要瞒住我?”风铃眼含愠色,起身想要拽他,手才触及他的肩膀,才发现,他已经睡着了。
凛冽风声在窗外呼卷而过,撼动木格窗棂咔咔作响。风铃惘然站立片刻,想要坐回桌旁,却看到了卧榻侧地上的一封信。
他愣了愣,看看合着眼的秦苍,悄无声息地将信捡起。
【四】初雪
天光微亮时,秦苍迷迷糊糊睁开眼,借着朦胧的光,望见风铃伏在桌上睡着了。他揉了揉酸痛的肩背,起身轻轻走到门边,还未开门,却听身后传来风铃略显低沉的声音:“不说一声就要走?”
“吓我一跳。”秦苍回过头,见他没什么精神的样子,讶然道,“怎么没睡好?走,去云台山再好好休整一下。”
风铃却坐在那里,望着他道:“秦苍,我们都是江湖人。”
秦苍茫然:“怎么了?”
“江湖事,就该用江湖的手段来处置。”风铃解嘲似的笑了笑,眼里却有说不清的无奈,“谁不听你的,那就用帮规,用家法杖收拾。再不然,只要你说一声,我用拳头将他们打服打怕,镜湖门的弟兄们,也能为你撑场面。赢者为王败者寇,我们这条道上的,历来如此。”
秦苍注视着他,缓缓道:“然后呢?打服了,他们就真能心甘情愿效力?漕帮的生计,靠的是成千的兄弟相助,而不是用一双铁拳去将人打到俯首帖耳。”
“那你想依靠什么?卑躬屈膝去找京城的官员?我们在那些人眼里,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只会喊打喊杀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风铃攥紧手中早已空空荡荡的酒杯,指节突起,语含愤然,“你不是一向很骄傲?为什么要去巴结他们?!我说过,你若是有难处,我不会袖手不管!但你现在,瞒着我的事,还少吗?”
秦苍深深呼吸几下,哑声道:“你知道了什么?”
风铃愤愤盯他一眼不回声。秦苍忽而一省,瞥到他袖下压着的信封,疾步上前道:“风铃,你偷了信件?!”
风铃一抬目,眼中覆着冰霜。“……你说什么?”
秦苍厉声追问:“我放在身上的信,你偷拿去了?!”
风铃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他,静了片刻,忽然忍不住好笑道:“你对我说,偷?十五岁认识你,互相换过衣衫穿的交情……你现在,用这样的语气呵斥我?少堂主!”
“我现在管着镇江码头,我有自己的事!你以为还是小时候,彼此之间什么都可以拿走?!”秦苍的手在微微发颤,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你全看完了?”
风铃又笑,笑里满是讥讽,他站起身,将那封信甩到桌边。“我读书少,看不懂你们那些文绉绉的词句!秦苍,你该放心了?”
“你……”秦苍还待说话,风铃已开门而去,脚步无一丝停顿。
西津渡口马鸣萧萧,一袭黑衫的风铃就此离去。然而卧榻边,他送来的酒葫芦还半开着口。
*
除夕前,南晴婉托人捎信来,满是哀愁地说,因父亲提前回到了家中,她不能再偷偷来镇江,问他如何是好。
秦苍对着那封信,犹豫了许久,提笔又搁下,始终不知如何应答。
整个春节,他都在忙碌。北上的船队那边传来消息,今年山东境内严寒迫人,船队为风雪所阻,停在岸边已多日。运粮的弟兄们受冻挨饿,有不少感染风寒,连连高热,弥漫返家颓念。
他焦虑地整夜无法入睡,又不愿召集长老堂主商议。当初是他极力要求帮众北上,如今出了问题,更多的人只会指责嘲讽,能真正出力者寥寥。熬到天亮,他终于写完几封信,急忙派人快马加鞭送往济宁府与兖州府,希望那边的同道能予以相助。
然不到半日工夫,众长老堂主纷纷得到了消息,络绎不绝前来询问。旁敲侧击者有之,当面发怒者有之,表面关切实则作壁上观者更有之。就连一向支持他的黄长老也紧锁双眉,问道:“少堂主,你先前说会让朝廷改长运法,那话还算数?”
“我不会说大话,黄长老,有些事牵扯深远,我不能公开讲。长运法也是数位官员上奏后,万岁经过仔细考量才定下的法子,不可能短短时间内就重新推翻。”秦苍独坐在泰和堂匾额下,身形消瘦,“上个月扬州那边也闹事,结果怎样?还不是被官府出兵,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不能再莽撞。”
黄长老深深叹息,向他拱了拱手,转身离去。
济宁府的大雪还未消融,秦苍就接到了从京城来的信。
信中提到了两件事,其一是与改长运为兑运有关,他看到那短短几句的时候,手不禁微微颤抖。然后很快,当他看到另一件与之相关的事后,心又一下子沉坠下去。
那天晚上,他反常地让人买了酒,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喝了一杯又一杯。想要大醉,醉到不省人事,或沉坠或飘渺,便可活在虚无世界。有太多话积蓄在心,无处可说,无人可说,亦让他日益习惯于坐在灰暗书架前。他总觉着,有沉沉冰石压覆在心,在身,令他无法抬头,无法直视,却偏偏还要挺直了脊梁,敛起了神容,做那个手握盘龙杖的当家人。
烂醉一场,直至天光。
初七清早,街角鞭炮犹响,他坐上马车,离开了镇江。
*
秦苍登上栖霞山时,风中飘起了微雪,簌簌小小,轻凉无声。
他在望江亭中坐了许久,手已冰冷,才望到那白底兰花的纸伞一角。
“秦苍!”南晴婉的脸冻得发白,眼里却依旧漾着兴奋的笑意,她跌跌撞撞从山路而来,奔向这僻静之地。
“小心点。”他起身迎上,轻扶住了她的手。
她急促道:“我爹说要出去见朋友,结果磨磨蹭蹭好久都不走,我都急死了……你来多久了?冷吗?”
“还好,早知今天会下雪,就不约你出来。”他为她拂去碧衣上的雪,牵着她的袖来到亭中,“你爹出去见什么朋友了?会不会很快就回家?”
“不会啊!”南晴婉冻得瑟瑟发抖,心却滚热,“他这次回南京后忙得很呢,经常很晚才回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了,你这次,怎么会来应天府?”
他怔了怔,一笑道:“收到你的信很久都没有回,你又说,不能来镇江,可不是得我过来?”
南晴婉看着他的眼睛,抿了抿唇,小声道:“那是,很难得。”
“……你怪我?”他垂下眼帘。
“没有!”她紧紧裹着斗篷,“我知道你忙帮里的事,只是,只是希望你有机会的话,能过来……”
他定定地看着她,许久不说话,忽而拉过那狐绒斗篷。南晴婉不安地往前跌出一步,已被他轻轻抱住。
浅息初缠,肌肤轻触。
她的身与心俱在颤抖,风雪拂过脸颊,也传来他的低语:“晴婉,你能帮我个忙吗?”
南晴婉一震,屏住呼吸。
“什么?”她不安地抬起眼眸,想要望进他的心,只是他的眼眸深处仿佛雾霭流离。他再次将她抱紧,死死的,好似不愿放手,闭上眼深深呼吸。
轻雪缭乱翩飞,掠过重重山岭、层层松枝,纠缠着,跌下断崖去了。
【五】流年
他终究还是离开了栖霞山。来到马车旁时,四野空寂无人。
南晴婉早已走了。
只是那撑着竹骨兰草伞,身着碧青织金裙的影姿,似乎还存留于落满细雪的山间小径。
原路返回时,他隔窗望着寂静山野,不知她会在心里如何想,或许只会像方才那样,坐在一角默默流泪。
他也不知道那个从京城来的按察使,是不是已经到了南京。
南京、镇江、京城,南、秦、苏、许……像是无形的网,逐渐密织缠紧,让人难以脱身。
离开南京后,他犹豫再三,转往东太湖。
阴霾沉沉的天空下,东太湖烟波渺渺,一望无际。他独自驾着小舟,去了漫山岛。踏上那久违而熟悉的地界,他在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开口。然而在岛上走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有寻到那个人的身影。
他问,风铃呢?
他们摇头,说,不知道,很久没有回来。然后反问,没去镇江找你?
他只剩惘然。
坐在湖水拍岸的岩石边,看白羽水鸟低徊,恍惚意识到,真的已经很久没能像以前一样,躺在落满月光的岸边,望群星璀璨,甚至不去管搁在石缝里的鱼竿。
因为风铃总会骂骂咧咧,再为他看好时机,唰的一声就将鱼儿提上。
然后他们就在湖边架起篝火,烤鱼。
出身于漕帮的他依旧会被风铃笑话,说他居然不爱吃鱼。他只是笑,爱与不爱,是只属于自己的事,凭什么要与他人一样?
但他会将鱼处理得干干净净,烤得松脆喷香,递与风铃。
不爱吃鱼的人,却有最好的手艺。
然后他们会躺在湖畔,枕着皎皎月光,听水声起伏涨落,说平时不好向旁人说的话,骂平时不好骂的人。只是后来想想,多数都是他在讲,因为风铃从来没有可隐藏的话语。
但是这一天,他坐在湖畔等了许久,都没有再见到风铃。
临走的时候,秦苍将手中白石尽力抛向远方,轻轻一声,只溅起数点水花,便消失无踪。
*
三月初,小桃绽丹红。他听闻了按察使下江南后的种种传言,他们说那人虚有其表,不务正业,甚至接受富商们的贿赂,醉生梦死,流连风月。
只有他知晓,许云哲前来江南的真正目的,皇上钦点的按察使,也绝非浪荡子弟。
三月底,柳絮飞满城。从京城返回的漕运船队终于抵达镇江。他带领全帮长老、堂主前去相迎,码头上熙熙攘攘。庞大的船队缓缓驶来,跟船帮众们挤在船头,朝着家人大声呼喊。
哗啦啦铁锚定底,呼拥拥人群奔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搂一个,却有老妇焦急着寻不到儿子,也有孩童哭闹着要找父亲。
再然后,押船的堂主晦暗着脸色走了出来。济宁大雪那阵子,船上蔓延怪病,死十一人,无法运回故乡,就地掩埋。
哭喊声顿时铺天盖地,一声声尖利凄惨,刺破人心。秦苍站在人群间,看那些老幼妇女捶胸顿足,觉得自己已快要将巨石压倒。
“当初是谁硬要叫我儿去京城送粮的?!天杀的朝廷不给我们活路,你们这些堂主帮主,自己安安稳稳待在家里,就让我们的亲人去送死?!”绝望的老妇人认出了秦苍,跌跌撞撞冲过来,揪住他的衣襟拼命撕扯。
紧接着,又有许多人也红着眼冲上来,谩骂、诅咒、殴打,他像失去灵魂一样站着,周围的堂主也只是劝,几乎没人出手制止。
狠狠一记耳光,让他唇角渗出血丝,他却觉得自己该打。
四月初,芳菲谢一地。黄长老对他也日渐疏远,他竭尽所能调转银两,亲自将比其他府高出三倍的补偿送到每户人家。
随后,大病一场。
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又收到了南晴婉的来信。印着红莲花的信笺上,残留斑斑点点,应是泪痕。
他无力地看完,点燃油灯,无声焚尽。
四月中,黄莺婉转鸣。派去东太湖的仆人回转了,对他说,风铃曾经回来过,但很快收拾包裹,不知去了何处。
五月初七,弯月照澄江。帮中陆续有人离开,他重病初愈,披着青衫独坐在窗前。京城又来了信,密缄精封,文短意寒:许云哲,必须得灭口。
他看那信纸渐渐烧成灰,眼前满是迷濛。
一杯酒呛得咳嗽连连,辛辣的滋味烧彻心扉。
五月初八,秦苍苍白着脸色,去往东太湖。船在岛屿前随浪起伏,他坐在船头,遥望许久,几度想要上岸,终究还是隐忍回舱。
桨声吱呀,他坐在黑暗里,甚至不知风铃是否已经回来,是否正在岛上饮酒。
进不敢进,退无可退,就此别过,两相宁静。
五月初九,微雨连绵落,秦苍再到栖霞。早已等在望江亭的南晴婉精神恍惚,一见到他就忍不住落泪如雨。
看起来煊赫富贵的南家早已外强中干,兄长在外经商时胡作非为,奸污少妇,却没料想那看起来衣着寻常的女子有个当监察御史的远房堂叔,引来轩然大波。父亲为平息此事,又向交好的京官大肆行贿,那人却在最近遭到秘密弹劾,眼看就要自身难保。
秦苍听罢哭诉,静默许久,只问:“你知道,那个暗中上奏者,是谁吗?”
她怔怔坐着,眼神犹豫,想说又没敢说。
秦苍用指尖蘸了雨水,在石桌上慢慢写下了那个名字。
泪水再度迷濛了南晴婉的视线。她悲声问:“所以,你之前要我去结交他,是早就预料到今日?”
“他是官,我是民,他想查什么,要怎样查,我就算预料到了,又能怎样?”秦苍苦涩地道。
“那现在呢?”南晴婉哭道,“大厦将倾,我就这样等着家破人散?我去求他,好不好?他看着不像是坏心肠的人!”
“你以为,万岁钦点的按察使真是来江南游山玩水的?你去求他,怎么求?他奉的是皇命,要交的是重任,你以为像现在这样落了泪,他就会就此放过那一网即将被打捞起的大鱼?”秦苍异乎寻常地愤怒与焦虑,深深吸了一口气,定定地望着绝望的南晴婉,哑声道,“求人,是没有用的,晴婉。只能让他,无法再查下去……”
“那该怎么办?就我们两人做得了什么?”她浑身发寒,声音发颤,忽而一省,“你不能找漕帮的人想办法吗?”
他摇头:“只能我自己承担,一旦牵扯到帮众,漕帮将遭受灭顶之灾。”
“那你的朋友呢?!镜湖门的风铃!你以前不是说过,他是你最好的兄弟!”南晴婉濒临崩溃地求他。
他愣怔半晌,才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他顿了顿,又道,“这件事,只能亲自处理。”
望江亭中,他向南晴婉细细诉说,要她不露痕迹,与许云哲相约会面。再然后,潜伏在此的他会伺机行动,彻底解决此事。
“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南晴婉艰难地抬起头。
秦苍合拢双目,低声道:“你不需知道更多,只要将他引至这里,再找个借口离他远一些,最好什么都不要看……”
雨丝连绵,淅淅沥沥,滴落叶间。他与南晴婉分别,相约三日后的黄昏,在望江亭行事。
五月十二,生死在此。
【六】岛屿
五月初十,秦苍做好一切准备,心里既被堵塞满满,又觉无尽虚空。
五月十一,他反复推敲计划,不知为何,总觉心神不定。
五月十二天明后,住在客舍的他,从楼下闹哄哄的议论声中听到了昨夜栖霞山的大事。
盐商千金深夜坠下山崖而死,众人争论着慨叹着,无人注意到楼上那扇窗后的年轻人神色仓惶。
那天夜晚,他如幽魂般去了栖霞山。山风卷掠,吹透心扉。抬头望月,江声滔滔,黑沉沉山岩耸立,却有另一人盘坐其上。
“你?!”秦苍惊愕不已,“风铃?!”
“我想着,你应该也会来。”许久未见,风铃还是那副样子,淡漠慵懒,好似什么都没发生。
秦苍一步一步走向他:“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说呢?”他似乎有意不想看着秦苍,扬起脸,望向峰峦。
“昨晚的事,与你有关?!”秦苍竭力克制着自己,看着他那双幽黑的眼睛,“南晴婉死了,许云哲失踪,你到底……为何要参与进来?!”
风吹山林,枝叶起伏。
风铃坐在山岩上,撑着脸颊,淡淡道:“秦苍,你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千金小姐都能派上用处,却偏偏忘了我。”
秦苍听着这话,竟悲凉一笑:“那是因为……那是因为,我不愿长久与你没有联系,见面就是求你为我杀人!”
“求我?”他难以置信地看向秦苍,“你为什么,非要说求?我为你做事,替你分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不出手,杀人的,就是你自己!”
“那也是我愿意!”
“你愿意?有人不愿意。”风铃愤愤然说了一句,从山岩跃下,站在阴影里,“你大概不知道,是南晴婉找到我,她说她不想让你亲自冒险!你开春才大病一场,她……舍不得你!”
秦苍攥紧了手,说不出话。
风铃抬目望向夜空寒星,唇边浮起难以言说的笑。“你看,她真的,不愿让你有一丁点儿的危险。”
秦苍如鲠在喉,他想上前一步,可风铃很快又望向他,淡淡道:“我给她提供了下毒的东西,与此事脱不开关系了。秦苍,你往后,不要再与我见面。”
“你何必……”仿佛被什么重重击打了一下,秦苍心中隐隐作痛。风铃却只平静地安排着:“你回镇江去,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会想办法解决遗患。若是几年之后,此事再无人提及,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见。”
说罢,他利落转身,头也不回地往更黑暗的地方去。
“风铃!”秦苍站在原处,压抑着心绪喊他。
他脚步只一顿,再也没停留。
*
京城的信又来了,指责他没有将事办妥,许云哲生死未知踪迹全无,让人无法放心。
他暗中沿江苦寻,始终未能如愿。
不久后,坊间传言四起,都说是许云哲轻薄南晴婉,使得这姑娘含冤跳崖。他坐在街边酒楼,慢慢饮下这一杯苦酒。他不该如此毁坏她的名声,但只有这样,才能让许云哲身败名裂,就算活着出现也不被朝廷信任。
应天府终究还是查不出真相,草草结案。秦苍回到了镇江,只是这一次的回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他疲倦不堪。
途中他几次三番想去东太湖,最终还是未能成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风铃。
五月底,玉兰展清姿。他在漕帮日以继夜忙碌,累到极致就不用多想,困到极致倒头就睡。说来可笑,从应天府回来后,他再也没有做过梦。无论是南晴婉那澄澈双眸,还是风铃的不屑笑容,全都,没有了。
他的白昼黑夜,是一片虚无。
偶尔,仆人会好奇地问,风小哥怎么很久都没来找您?
秦苍出神片刻,不说话。
六月至,七月来,京城那边迟迟未有更改漕运法的消息。他起早贪黑去码头,安抚一个个帮众,七月末的时候,又病了一场。
病愈后的第二天,他独自一人拿着鱼竿,去了西津渡。
直至深夜,才提着空空的桶回转。
八月丹桂香。京城终于传来消息,万岁正在考虑更改漕运法。他拿着信,竟没有欣喜如狂,只是坐在了桌前,发了很久的呆,随后,落了泪。
然而就在第二天,又一道急信飞速送至。京城异变,皇上派出亲信前往应天府,似乎专为那事而来。
秦苍心神俱凉。
一如既往烧掉信件,他连夜乘船赶往东太湖,终于在星空寂寥的水岸边,找到了正在饮酒的风铃。
“要出事了。”秦苍气息未稳,急切道。
风铃带着醉意瞥过来,愠怒道:“不是叫你别再来吗?”
“朝廷派玲珑门的人来重查栖霞山的事了。”他眼神空洞,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风铃一怔,继而将酒葫芦丢下,作色道:“那你更不该再来找我!他们要查,最多也是查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与你相关怎么就不与我相关?!”秦苍怒喊着,声音都为之改变。
湖水一波一波涌来,轻拥浪花,层层退去。
他好似耗尽了全部力气,颓然后退。“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揽到自己身上?是一直觉得我无用,信不过我,非要将我的事抢过去做?!但我不会乐意!”
风铃看着他,过了片刻,才轻笑道:“想那么多做什么?兄弟之间,还说这些?”
秦苍闻言一怔,缓缓抬起头,看着他黑亮的眼睛:“风铃,你今夜就走吧。”
“走?我才在外面浪荡许久,现在累了,想回来休息。”
“等这件事过去再回来!说不定玲珑门的人也查无对证,过几天就走……你本就是江湖人,四海为家也不会惹人注意。”
“你这倒是为我着想了。”风铃又笑,捡起地上的鱼竿,在半空中甩出一道花,“那我……明天就走。”
随后,他大大咧咧地往灯火阑珊处走。走了几步,忽而停下来,回头道:“你今夜,不能留在这里吧?”
秦苍怔了怔,低声道:“不能,我马上得赶回去。”
“谨慎为好。”风铃点点头,站在那里没动。秦苍望了他一眼,往船只停靠的地方走去。湖水涌来又卷去,他脚步沉缓,直至行到船边,不禁转回身。
夜色下,风铃还站在砂石滩上,黑衣微扬。
“等我有空了,再去西津渡。”他还是带着玩世不恭的笑,扬起青竹竿,鱼钩在月色下闪出零星的光。
“……好。”
【七】归途
八月十二,夜雨打碧桐。
秦苍从深夜惊醒,没来由心神不宁,忽听窗棂被敲响,急忙披衣起身。打开窗子,外面却无人影,唯有一枚银镖刺在窗台,穿有纸条数寸长。
上面只有三个字。西津渡。
字迹却陌生,不是风铃所写。
秦苍心中一震,快步推开大门,唯见满院秋雨涟漪,怎有他人痕迹?思忖再三,还是腰佩长剑,头戴竹笠,匆匆而去。
马蹄踏碎一地积雨,自山道急转直下,径奔西津渡。
*
萧萧一声鸣,白马为缰绳勒停,腾起前足,止步江畔。
夜凉风生,雨势渐小,他翻身下马,慢慢走向渡口。长江潮来又潮去,暗夜沉沉不见月,那边长堤上,有人举着火把慢慢走来。
灰衫黑靴,一张陌生而略带沧桑的脸。
“秦帮主。”那人丝毫不躲避他的直视,散漫地打招呼。
“你是?”秦苍将手慢慢移至腰畔。
“其实早就认识,奈何不便,直到今天才见面。”那人从袖中取出一封信,“见到这个,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
手腕一扬,信封迅疾飞来。秦苍探手接住,借着火光一看那背后缄印,猛然抬头:“一直以来,都是你将密信投送至我书房?”
那人笑了笑:“正是,就像这样。”
“苏大人又有什么急事?”秦苍追问。
他却只摊摊手:“您可以自己看。”
秦苍心中掠过一丝不宁,拆开信封一看,白纸之上,毫无字迹。
他迅速地将纸正反又看一遍,讶然抬头:“为何一个字都没写……”
那人却毫不意外,淡淡道:“大人的意思,是问你有没有将事情处理干净。”
秦苍微微一怔,沉声道:“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京城来的人应是抓不到什么把柄了。”
“是吗?”那人扬起下颌,“是那个镜湖门的人,为你去做的?”
秦苍心头震动,却依旧保持着平静地反问:“你说什么?”
“栖霞山下,风真大。”灰衣人上前一步,慢悠悠地道,“你那位朋友,好像失败了。”
“……你说什么?!”秦苍盯着他再度追问,声音不由提高。
“不是你叫他去清除痕迹的吗?”灰衣人满不在乎地抬高手中火把,照得秦苍视线模糊,“他倒是胆大,竟然和前去查案的人待在一起。只可惜……最后应该是身份败露,被当场击伤。”
哗啦啦江潮涌起,直扑渡口木栏,撞出万千碎朵,四散飞溅。
秦苍背后发寒,哑声问:“那他现在呢?被抓了?”
“要是那样,我倒还得多一件事。”灰衣人忽而牵动嘴角,笑着喟叹一声,“他死了。”
又一波巨浪打来,重重拍击江岸,空余震耳回响。
雨滴从秦苍的竹笠上缓缓坠落。
永无止尽的江潮疯涌而来,又悲鸣退却,阴沉厚重的云絮压在江面,天地混沌,无可救药。
“你在说什么?……”他手心冰冷,几乎开不了口。
熊熊燃烧的火光中,灰衣人面容模糊不清,语声也似震荡飘渺。“我说,他死了,就在栖霞山下的长江边。”他顿了顿,回头望了望远处,“算是有江湖骨气的人,受伤之后,当即自尽。”
“我叫他走,永远不要再回来!”秦苍突然暴怒地喊,猛地抽出佩剑,颤着直指于他,“你说这些,有何目的?!”
“你不信?”灰衣人摇摇头,“那你觉得他会听你的,远走高飞吗?我用这骗你又有什么意义?”
灰衣人似乎还在说着,秦苍却已经什么都听不清。
“京城来的人,很快就要到这里。”灰衣人再次望了望远处,“阁老的意思是,不留任何证据。”
秦苍望向滔滔江水,沉缓往渡口行了数步,忽而站定,背向着他问:“长运法的更改,万岁同意了吗?”
灰衣人嗤笑一声:“朝堂要事,我怎会知晓?不过,听说先前是有所想法,只是如果阁老被参劾倒台,不就彻底没戏了吗?”
风雨掠过,秦苍的背影尤显清瘦。他缓缓点头,又问:“那自尽的人,临终前可有留话?”
灰衣人皱皱眉:“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是。”
“好吧。”他大发慈悲地道,“据说是讲了一句‘她很累’,但不知什么意思,说的是南晴婉吗?”
秦苍心间颤痛,紧紧攥着冰凉剑柄,许久才道:“我,知道了。”
“不会真要我动手吧?这样容易引人怀疑……”灰衣人话还未罢,又一波巨浪涌上渡口。飞雪碎琼间,唯见剑光一道,嫣红一抹,秦苍踉跄半步,跌入江中。
潮水汹涌卷腾,转眼间,便将那身影吞没。
灰衣人怔了怔,上前照亮渡口,唯余长剑染血,杏穗横斜。
他上前轻轻一脚,将那长剑踢入江水,转眼即沉。
远处官道上,火把晃动,车轮滚滚,一支马队正飞速驰来。灰衣人将火把投入江中,掠上秦苍的白马,趁着夜色疾行而去。
四下又恢复死一般的寂静。江潮冲尽血痕,轻抚西津渡口,好似万古不变;又似有无数言语,难以诉尽,唯有一夜夜辗转反侧,萦绕其旁。
东太湖漫山岛上,他也曾枕臂而眠,与风铃共望繁星江影。那夜远处有焰火绽放,粉紫流金,纷纷扬扬如花丝飘零,坠入江心。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云台山下,西津渡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年少,俯仰皆成非。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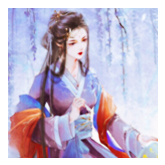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17 13:49:5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17 13:49:5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虎虎生威
:虎虎生威
 :虎啸云霄
:虎啸云霄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7-0 届
:风云537-0 届






































 Post By:2022/4/17 13:56:4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17 13:56:4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虎虎生威
:虎虎生威
 :虎啸云霄
:虎啸云霄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7-0 届
:风云537-0 届






































 Post By:2022/4/17 13:56:5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17 13:56:5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17 13:57:5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17 13:57:54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