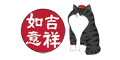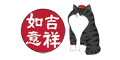城西立交四通八达,车辆在桥上聚合,再分离,而后驶向不同的目的地。
李渠安靠在车内壁,瘦弱的身体随着向心力登上立交桥顶。他俯瞰整个桥下,桥下像是个无底洞,洞中充满了不安与不安分。等到第二天再次经过,李渠安手里多了个大包裹,那是他爸爸的骨灰盒。
从那一天起,李渠安开始恐高。他爸是在工地上摔死的,在他叔叔的工地上。工地在广州市内,小高/层商品房。叔叔是亲叔叔,爸爸的亲弟弟。爸爸却不是亲爸爸。
上午火化完,叔叔对李渠安说了些后事。大约是李渠安爸爸岁数大了,在城里属于退休年龄,没有社保,所以谈不上工伤、工亡。又因为农村身份,伤亡补偿肯定达不到城市标准。不过,叔叔在工地上大小是个头,施工方领导多有照顾,基于人道主义,决定赔付16万。虽然甲方、乙方,各方现在都没钱,叔叔口头承诺,只要工程款下来,钱如数给他,现在就当是在叔叔那里存着。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遗产吧。李渠安顾不上想那16万,捧着骨灰盒呜呜咽咽,他不敢看骨灰盒上的照片,又忍不住多看一眼。父子俩平时话不多,每次打完电话爸爸总会丢下一句“安仔你要成器啊,不然以后就在工地上当个打工仔。”哭到伤心处,李渠安一手搂着骨灰盒,一手扯下孝帽,捂住了眼。
这一扯不要紧,吓坏了左近前来吊唁的工友。堂哥李渠风站在身后,望着堂弟四仰八叉绿油油的长发差点没笑出声。叔叔抢回了孝帽,又给李渠安扣了上去,嘴里嘟囔着,仔细数数六个字,大概是“不成器的东西”。
李渠风将堂弟拉到一边,两人来到一处亭下:“亲恩不如养恩。如今你十六,大伯六十一。我大伯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仁至义尽。那时候你没人要,我爸从路边把你捡回来,大伯正好没有儿女就收养了你,本来还指望到老了有个依靠......养老就算了,好在还能送终。”
李渠安瞪大了眼睛:“那我妈呢?不是说离婚了吗?”堂哥耸了耸肩:“那都是小时候哄你的,你哪有妈,我大伯那方面无能。”
李渠安回到老家安顿好骨灰盒,站在田埂上。绿油油的稻苗随着长发在风中律动,颇有意境。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很早就让给了别人种,现在,这片地依旧姓李,以后估计依然给别人种吧。无所谓,他本来就不会种地,村里的青年谁又会种地呢?种地又成不了器。
爸爸生前给的生活费只剩下两百,本来有三百,被他花去一百在村头“忘爱”发廊染成通体绿。如今染回来又需要一百,干脆就这么一直绿着,反正也没人在意,毕竟唯一希望他成器的那个人已经走了。
就这样省下了一百元钱,李渠安来到县里,想找一所美容美发学校,为了以后一头绿毛好打理,又或者将来真成了器,自己给别人打理。哪怕用最差的染发剂,这一百一百地收起来也会手抽筋。到时候把理发店开在村西边,跟村东边的“忘爱”发廊隔河相望。说不定手艺好了还能将对方挤垮,独揽全村少男少女的头等大事。
可能李渠安只接受过义务教育,尚不能理解学费这档子事。当他好不容易找到县里唯一一所美容美发学校,刚进门便被热情的学生们招呼过去,白白当了一回模特,而后被教务老师领到财务室,半分钟后又被无情地轰了出来。
在县里网吧待了一夜,出了门,李渠安打了个哈欠,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发蜡,仔细将一头绿毛一撮撮的捏在手里,慢慢搓出造型。这只发蜡是在美容美发学校当模特时的奖励。李渠安对着网吧外的玻璃审视自己,暗叹没能在发型艺术上有所造诣实在可惜。
艺术事业暂且搁在一边,李渠安来到叔叔工地时已身无分文。他望着刚刚封顶的小高/层打了个寒颤,愣了半天最终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见到叔叔,叔叔很开心,虽说无血缘,可谁又会拒绝一个青壮劳动力。亲戚嘛,肯定是要帮扶的。不过,李渠安婉拒了叔叔的安排,他可不想像他爸爸一样当一个架子工,万一......
最终,叔叔让他去了钢筋工组,跟着一个中年师傅后面学习折弯钢筋。
钢筋棚在平地,还有个棚。即使有遮挡,李渠安依旧每日汗流浃背,浑身湿透。钢筋师傅经常看着他笑,那么长的头发塞在安全帽里,能不热吗?师傅时常散烟,两人点上烟,聊一会,权当是休息。
师傅告诉李渠安,工地上有三种帽子,白帽子是监理、甲方,红帽子是施工方、乙方,黄帽子是普工。黄帽子怕红帽子,红帽子怕白帽子。中年师傅让李渠安好好干,有他叔叔这层关系,将来迟早要戴红帽子,到时候红配绿......
蹭了几天烟后,李渠安谎称自己嗓子疼,便谢绝了师傅的好意。他懂规矩,但实在为难。
下了工,李渠安来到项目部,叔叔正端坐在里面喝茶。李渠安还没开口,叔叔让他赶紧坐。李渠安看见桌上放着一盒中华,脸上的表情出卖了自己。叔叔很自觉,从盒里抽出一根烟,刚要递过去。
李渠安哆哆嗦嗦:“叔叔,工程款怎么样了,我爸那16万。”
叔叔将烟屁股塞进了自己嘴里,猛拍桌:“不是我说你啊,安仔,你才十六,花钱大手大脚,染了个绿毛龟一样的头发,还学人家抽烟。”
李渠安满脸不解:“叔叔,我也没找你要烟抽啊,再说了,堂哥不也抽烟。”
叔叔大手一挥:“你跟你堂哥比?你堂哥是正规大学生。好了,别说了,想想你死去的爸爸,不成器的东西。”
从项目部出来,李渠安暗悔。就不应提那16万,儿子是假的,他这个弟弟可是真的。当时就该在项目部里装孙子,老老实实求叔叔给他支取点生活费,毕竟累死累活干了十多天,要个烟钱总可以的。
随后半个多月,李渠安除了每日弯折钢筋,剩余时间就在棚子里捡一些废旧钢筋零碎。中年师傅心领神会,偶尔随手帮他捡几个。那天,李渠安取下安全帽擦汗,师傅看他低着头,滴下来的不知是汗还是泪,实不忍,摸出根烟丢过去。李渠安也没推辞,找师傅借了烟屁股斗个火。
师傅问他:“安仔,你还会别的吗?”
李渠安摇摇头:“跳街舞算不算?”说完,李渠安摆了几个动作。
师傅弹了弹烟灰:“跳舞又不能当饭吃。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他也喜欢跳街舞。”
李渠安猛吸了一口,侧过脸朝旁边吐去:“师傅,你儿子也抽烟吗?”
师傅无奈笑了笑:“还在上学,抽什么烟,打断他的腿。”不等笑完,师傅把烟屁股踩灭,叹了口气接着说:“哪里管得住啊。哎,希望他能读个大专,将来也能弄个红帽子戴戴。”
师傅重又回到钢筋折弯机器前,将一根钢筋摆上工台:“不然,就只能干这个。”
半个多月后,李渠安拣了一大麻袋废旧零碎,在废品收购站卖了一百多元钱。李渠安拿着钱买了两包中华烟,回到宿舍扔一包给钢筋师傅,说了声谢谢,便消失在广州的夜中。
那天晚上,李渠安想去小蛮腰。他穿梭在高楼大厦间,走了好久,总觉得近了些,可总也走不到,广州城实在太大了。小蛮腰也着实太高,随着目标越来越近,李渠安内心的不安被逐渐放大,这么高的电视塔得搭建多高的脚手架?
直入云霄的塔顶并没给李渠安带来多少开阔感,反而与身边高楼大厦一起,用钢筋混凝土筑成一道道围栏,将李渠安死死压制在路灯下。李渠安停在原地,没有继续向前,他转过身去,看着身后被压扁的影子被灯光拉成了一道长条。
李渠安没迷路,他知道只要向着塔尖的方向就一定能走到小蛮腰,可是他选择了更熟悉的车站。车站外,李渠安躺在石头凳上,掏出烟,又摸摸口袋,无奈,居然没有打火机。
第三次经过城西立交,李渠安不复往日拘谨、无措。记得第二次坐车的时候后座有对老夫妻,女的说:“哎呀,绿绿的,扑街仔,好衰啊。”男的说:“地贫啦,一畦韭菜好掂,长了就要割啦。怪你炒股啦。”
这一次车上没有老夫妻,连中年人都没有,全都是同他一般大小的年轻人。这一趟车坐得无比自在,车上没人说炒股,也没人说韭菜。李渠安回过头去,看着后排五颜六色的头发绚丽多彩,炫目得压过了昨晚小蛮腰上的灯光。
一路向南,没多久,广州城郊。车子停在一片小广场旁。车门前迅速围上几人,这些人短袖衬衫黑西裤,脖子上挂着个工牌。李渠安主动走近一名短袖衬衫,撕开香烟包装,对方正在忙,见有人投烟问路便放下手头事,欣然接过香烟。
李渠安摸了摸口袋,这才想起自己压根就没买打火机。不过不要紧,短袖衬衫有,而且何止有,他有一口袋。短袖衬衫从无纺布袋中掏出一把打火机塞给李渠安:“靓仔,我这有。”说完短袖衬衫挥了挥手,表示自己正忙,又指了指打火机,随后转身去招呼一位画着烟熏妆,额前接了一绺紫发的女生。
离开广场,顺着打火机上的地址找到了门面------振辉人力资源。刚想进去,大门紧锁,他贴着窗玻璃朝里望了望,没人。
一下午李渠安都在网吧里泡着,这儿的网吧比县里的网吧好很多,机器好,游戏速度也快,最主要没人查。过了十二点,网吧里依旧鼎沸,噼里啪啦键盘声此起彼伏。李渠安昨夜夜游广州,加之白天坐车身体困乏,在座位上打起了瞌睡。结果轰隆一声把他吓了一跳。隔壁座位另一位靓仔睡着了,双手搭在键盘上,靓仔换了个姿势,不小心将键盘连带着显示器拉倒在电脑桌上。那么大的声响也没吵醒靓仔,靓仔直挺挺躺在座位上,像极了一具死尸。
李渠安顿感浑身冰冷,慌忙关了游戏结账下机。出门找了家便利店,用仅剩的钱买了碗泡面。李渠安端着泡面晃荡在振辉人力资源门口,一边吃着泡面,一边借着灯光咀嚼着招聘信息。“暑假学生工一小时28 ,长期工4000-6000一个月,包吃包住,五险......”
“哎呦?”
李渠安循声望去,振辉人力资源的玻璃门从里面打开,白天那个短袖衬衫走了出来,短袖衬衫站在门口,一只手毫无顾忌地理着西裤裤裆。
短袖衬衫掏出根烟架在李渠安耳朵上:“靓仔,明天来找哥哥,哥哥给你安排。”说完转身走到巷子里,巷子里随后传出一阵放水声。
包吃包住不是免费吃住,只是提供吃住,钱还是交的。李渠安没钱,找短袖衬衫借了五百。和所有电子厂一样,同一批进厂的青年不到一个月走了一半,也有个别三五天都没坚持下来,一分钱也没挣就提桶跑路。李渠安也曾跑路,他知道工地上虽然免费吃住,不过工地一般到年底才结账,他哪能熬到那个时候。再说了,到了年底,他叔叔未必就能施舍多少,毕竟叔叔没跟他签合同,更不会给他买保险。厂里就不一样了,厂里是签有合同的。当然,合同签的什么他一个字没看,看也看不懂。
好不容易熬到月底,李渠安只拿到两千,问了一圈,原来加班时间不够,良品率不够,外加扣除借短袖衬衫的五百连本带利,以及服务介绍费。工作倒不是很难,真就如同中介门口写的那样“工作简单,一学就会”。至于其他什么5s培训,其实就是小组长每天早上训话。小组长挺有意思,名叫吕笑笑,人长得好看,脾气和她名字整好相反,不如叫吕哭哭。
李渠安第一次挣这么多钱,钱拿到手第一时间跑去网吧包夜,第二天昏昏沉沉免不了被吕笑笑一顿臭骂。那天晨会,吕笑笑直接将李渠安踢出了组,话说得难听的要死,什么不想干就滚蛋,生产线上不差你这么一个人......两天后李渠安又被调回来继续打螺丝。没等李渠安滚蛋,线上又跑了俩。李渠安心里清楚,不过是混口饭吃,拼什么命,谁还能指望打螺丝发财?
这段时间李渠安也没时间去包夜,产能安排得满满的。每天加班加点,收工时候被吕笑笑骂上一顿,回到宿舍倒头就睡。睡完了第二天早晨回到工位开晨会,再被吕笑笑继续骂。李渠安恨吕笑笑不是个男人,又恨吕笑笑不抽烟,不然以他的社会经验,闲下来的时候递上一根中华,吕哭哭也会陪着笑。
李渠安没跑路也有其他原因,比如在宿舍学到了递烟以外的社会经验,什么n+1,什么失业保险等等。他想着反正自己不能跑路,就算滚蛋也要等别人让他滚。只不过好久没去网吧,每天被钉在生产线上打螺丝,打着打着自己就成了螺丝,且越拧越紧,挪不动步子了。
连续打了三个多月螺丝,厂里突然放了一天假,李渠安哪也没去,在宿舍闷头睡了一整天,晚上跑去网吧玩游戏,许久不玩竟然生疏了。一个多小时后返回宿舍,还没进门,里面吵吵嚷嚷响彻楼道。一个四川舍友正和一个安徽舍友骂架。大概意思是四川哥在安徽哥床前看到一截娇子香烟的烟屁股,四川哥认为安徽哥偷他烟抽,安徽哥不承认。这两人都在李渠安上游那个工作组,平时就不对眼,四川哥处处踩安徽哥一头。
到最后安徽哥大嚎一声:“抽你根烟会死啊?”。
李渠安打开衣橱锁,从橱子中拿出一盒中华,晃了晃烟盒,最后两根,川皖两边,一边递了一根。随后把烟盒捏扁扔进垃圾桶,大迈迈说了句:“不就一根烟嘛,抽我的。”
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李渠安还在睡梦中,咚得一声,房门被撞开了:“不好了,小安徽跳楼了。”李渠安惊得从床上跳了起来,第一时间望向四川哥,四川哥满脸惊慌,不住摇头。等到他们冲到楼下,一匹白布直挺挺地躺在水泥地上。
这一天晨会李渠安魂不守舍,好在吕笑笑从头到尾没发脾气。大家也都发现了生产线上的一些异样。昨天停工一天,厂里做了些改造,原先安徽哥和四川哥那组被新安装的机械臂取代了。
下了工,一群人围在宿舍楼下,不会又有谁跳楼了吧?李渠安走近一看,宿舍楼的走廊上已经装上了不锈钢防盗栏。人群中有人说,总共六层楼,只装了三四楼。二楼摔不残,五六楼一摔就死,三四楼摔得半死不活的最要命。
李渠安哪敢多看,生怕哪个想不开的又从上面掉下来砸到自己,这时候可连顶安全帽都没有。他赶紧绕过人群,蹬蹬蹬跑回宿舍。宿舍里其他人都拉着个脸。四川哥早已不见踪迹,床单都没有了。晚上宿舍里一位稍微年长些的北方人抱来一箱啤酒,喊着大家一起喝。
李渠安喝了两瓶,不胜酒力,早早躺倒睡着。夜里不知几时,李渠安起来上了个厕所,觉得闷热,跑到走廊上吹风。还好三楼装上了围栏,恐高症被锁在了安全范围以内。一阵夜风吹过,李渠安打了个哆嗦,正准备回屋睡觉,楼梯拐角处一道人影飘过,是个女人,马尾辫,还挺好看,不会是女鬼吧,不对,那是吕笑笑。
李渠安鬼使神差跟着人影来到六楼天台,看着吕笑笑掏出钥匙打开天台铁门。之前天台是可以进去的,平时大家都在天台晒衣晾被,今天早晨出了跳楼事件,厂里就把天台门给锁上了,没想到吕笑笑居然有钥匙。李渠安躲在铁门旁,借着月光,看着吕笑笑走近天台边,她拿出一枚硬币往空中扔去,又从地上捡起,再次往空中扔去,反复三次。随后一只脚正欲跨过护栏。
“别跳。”李渠安冲了过去,一把拉住吕笑笑,安慰道:“不就是钱嘛,我借你。”结果劲没用好,自己脑袋探出围栏,望了一眼楼下,瞬间晕倒。
第二天宿舍楼里都在传,李渠安被安徽哥“传染”了,夜里也想去跳楼,结果被夜间巡楼员吕笑笑及时发现。不过这一说法既没得到吕笑笑证实,也没得到李渠安证实。
吕笑笑跟没事人一样,晨会没开,一大早就被叫去办公楼开会。当她回到车间时找到李渠安,吕笑笑给李渠安放了三天假,并且不扣他工资。李渠安拍了拍胸脯表示昨晚英勇行为实属本能,并感谢组长给假。吕笑笑没领情,依旧冰冷着脸,她让李渠安老实呆在宿舍别乱跑。
下午,李渠安跟着吕笑笑还有其他十几个人来到会议室。工会主席坐在台上:“最近我们厂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李渠安捅了捅吕笑笑,小声说:“吕姐,工会主席是什么?没听说过这个部门啊。”吕笑笑没正眼看他:“有,兼任的。别说话,听着就行。”
台上工会主席继续说:“ 为了丰富广大职工的业余生活,我们决定在厂里搞一个联欢晚会,我从个人信息表里面挑出了你们,你们都是有特长的。到时候在晚会上一定要好好表现。这次破例给你们三天带薪假,你们好好练习。到时候还会有领导莅临指导.....”
那天李渠安到底有多风光,台下领导们的频频点头赞许给出了答案。尤其是今天的主角,来自华南工程大学机械专业的方教授,他在台上讲话时一个劲夸李渠安舞跳得好。
那是当然,李渠安跳得舞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locking&poping,介于锁舞和机械舞之间。而方教授今天来参加活动也原因如此。厂里为了产能考虑,买了几台国产机械臂设备,这套设备有方教授背景,所谓产学研一体化。晚会上,方教授还带了一批研究生参会,另外还有两台人形机器。人形机器在舞台上同李渠安一齐跳舞。
听说电视台也来了,李渠安同机器人一起在电视节目里露脸了十几秒。按照节目里的解说,即反应了高科技在现代产业中的应用,又反应了当下电子厂工人丰富业余生活。
皆大欢喜。
从此,全厂都知道了安装组有个会跳舞的螺丝工,也看清楚了吕笑笑的真面目。晚会进行时,吕笑笑作为工人代表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她在电视中的笑容,虚假、违和,像是被人操纵的傀儡,用两根线提拉着笑肌,皮笑肉不笑。
至于安徽哥,他的故事已渐渐被人淡忘。生产线上,随着机械臂标准化操作,上游的零部件被机械臂安放到履带上,传至下一个工组。再由李渠安们拿在手里,拧上螺丝。这些零部件拿在手里的时候,仔细感觉,不带有一丝温度。
李渠安并没有因为这一次闪光而改变什么,打螺丝的时候可不许跳舞,生产线有节奏却没有音乐。无聊时李渠安偶尔会模仿机械臂动作,一顿一顿地打着螺丝,为冰冷的车间带来一丝欢笑。快乐总是短暂,每当吕笑笑巡视时,车间又迅速降温。
好在厂里开花厂外香。没过多久,李渠安接到个电话,事出紧急。等李渠安来到办公楼下的时候,楼里走出个差不多年纪的学生。李渠安光顾着盯着他的鞋,学生看到李渠安一头绿油油长发满眼放光。学生拉着李渠安往厂外走,随口说了句:“别看了,明天我送你一双。”
两人来到一家饭店,学生从书包里翻出两包中华,随手丢给李渠安一包,又拆开一包递上一根。一气呵成,期间不带一句废话。李渠安明白,对方是懂规矩的,既然懂规矩,话就有得聊。
学生自报家门,他叫张宇浩,厂长是他爸,兼职工会主席是他妈。张宇浩点了四五个菜,六七瓶啤酒,两人边喝边聊。李渠安很好奇,问他:“你爸妈不管你吗?”
张宇浩摇头晃脑:“我都多大了,还用管?再说了,我看过你的个人信息表,你不也十六,你不也抽烟喝酒。”
李渠安咂了咂舌:“能一样嘛,你是厂长的......”
厂长儿子怎么了?年轻人都是一样的。说着张宇浩又起开一瓶啤酒:“我也跳舞,跟你舞种一样。不过没你跳得好,我找你就是为了跳舞,明天你陪我去一趟华南工程,帮我撑场子。”
李渠安识相地敬了一杯酒,又解开香烟包装,递上去一根。张宇浩点上烟,吐了一个烟圈:“鞋的事包在我身上。”
张宇浩今年高二,跟同学组了个街舞社,社团周末会在商圈广场跳舞、聚会。前两天来了一拨华南工程大学街舞社的社员,一开始只是围观,后来一时技痒,跑上去切磋了一下。大学生没打算发力,点到为止。可张宇浩要强,非要跟大学生一争高下,他拉着两名同学跟大学生battle,连斗三台,结果输得一塌糊涂。输完后同学们灰心丧气,都说周末不愿再去商圈广场跳舞了。张宇浩一看队伍将散,想来自家厂子里有个高手,赶紧搬救兵去了。
第二天晚上,张宇浩和李渠安在厂门口打了个车前往华南工程。一路上李渠安都在摆弄自己的头发。张宇浩看不下去也闻不下去:“你这什么发蜡,味道怪怪的,等下了车找家店我送你瓶好的。赶紧把鞋换上,旧鞋子扔了。”李渠安哪舍得换:“下车再换吧,旧鞋子等会放鞋盒里,上班还要穿。”说完,李渠安盖上鞋盒,朝窗外望去,车子刚从城西立交桥驶下。
张宇浩提前踩好了点,今天华南工程大学街舞社在学校公园里举行社团活动。街舞社一伙见张宇浩背着个书包身后还跟了个杀马特,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根本就不准备给张宇浩切磋的机会。李渠安哪见过这种阵势,他倒是在村头跟小伙伴们斗过舞。舞台经验也是有的,厂里晚会那样的舞台说大不大,说小其实也不小。
可这是大学。有那么一刻,叔叔说的话飘过脑海:“你怎么跟你哥比,你堂哥是正规大学生。”
张宇浩见李渠安怂了,膝盖狠狠顶了他一下,在他耳边小声说:“怕什么?大学生算个屁,毕业了不还是上工地、打螺丝。干他们。”
李渠安几乎是被张宇浩推进场的,大学生们见状迅速围了过来,其中一个大高个伴着音乐节奏在李渠安面前不停做着舞蹈动作,动作中不乏挑衅。一曲结束大高个做了个抹头发的动作,意在嘲讽李渠安的发型,人群中又发起阵阵嘘声。李渠安被逼无奈,等到下一曲开始,跟着音乐抬了抬手,节奏是跟上了,却一点力度都没有。他心里清楚,大高个舞技了得,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年龄上的差距直接体现在肢体力度上,如果别人跳得是变形金刚,自己就是个变形金刚玩具。
大学生们见李渠安开始摆出舞蹈姿势,全部散开将舞池空出来。这时,一位穿着嘻哈服的学生跳了出来,学生各个关节如同缺油的齿轮不断卡顿,正好卡在了音乐节拍上。李渠安聚精会神,盯着他的动作。终于等嘻哈服跳完,李渠安摆动起来,人群中一阵惊呼,而后又是一阵叫骂。
张宇浩本来躲得远远地闷着头抽烟,听到人群中惊呼,扔了烟赶紧跑过来。李渠安正随着音乐将嘻哈服学生跳得那段重新复刻了一遍。按规矩,这是一种藐视,你跳得我也会,说明你拿不出东西。李渠安本意并非如此,他是真不知道跳什么,又被当成鸭子赶上了架,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嘻哈服后面现学了一段。
这一跳不要紧,大学生那边炸了锅。被一个十几岁的杀马特踩场子,用这种手段battle实不能忍。等到新曲子切换进来,舞蹈社社长亲自下场,他也不跳,摆了个请的姿势,意思是让李渠安先手。李渠安愣了半天,社长又摆了摆手,曲子过半,李渠安没有任何动作,急得张宇浩在旁边直跳脚。
人群中又是一阵嘲弄。李渠安抬头看着灯光闪耀,音乐不停在耳边轰鸣,整个人目光呆滞,僵硬地矗在原地。
“哎哎,动了动了”人群中渐渐骚动起来。
李渠安动作迟缓,面无表情,目光所到之处,大学生们渐渐模糊起来。张宇浩变了模样,变成了大背头,变成了厂长,大学生们一个个都成了工友的样子,他们面无表情的在流水线上打着螺丝。李渠安此刻化身为机械臂,站在上游,不停挥动臂膀,将一个个配件放到履带上,履带缓缓向前,将配件传递给下游。
休止符到,音乐停。李渠安的右臂仿佛延长音,在音乐外颤抖着,手掌伸向舞蹈社社长。此刻,社长从工友变回了学生。同样的曲子再次响起,他张了张嘴,向前迈了一步,始终不敢接近李渠安的手掌。
张宇浩咽了口唾沫,大气不敢出。小花园的空气凝固,所有人都在等社长的下一个动作。音乐没有停止,社长身上的电拉了闸。
一片哗然,一声惊呼,张宇浩兴奋地叫喊出来。赢了。
人群散去,两人在花园里点上烟,一齐回味刚才的盛举。李渠安嘴里叼着烟,换上旧鞋。张宇浩猛地拍打李渠安肩膀:“我就说这帮大学生啥也不是,就这学校,我躺着都能进来。对了,你这舞在哪学来的?”
李渠安没回过神:“网吧里,街舞游戏啊。”
“什么街舞游戏,我说你最后那套,打得社长动都没动的那套。”
“哦,SRT2000。”
“什么?”
“就是你家厂里新进的那套机械臂。”
张宇浩恍然大悟,鼓起掌来:“犀利、犀利。你赢他们就是洒洒水。我跟你讲,他们最多是在跳机器舞,你就是个机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黑暗处一句颤抖声音将两人吓得汗毛直竖。花园暗处走来一道人影,是一位阿姨。阿姨穿了身旗袍,特别得体,脖子上挂着一只玉佛,手腕上缠着一串佛珠。
阿姨五官扭曲在一起,猛推开李渠安,牵起张宇浩的手,颤抖地说道:“成成啊,你长这么大啦?哎呀,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啊。”张宇浩吓坏了,挣脱开:“你干嘛?”“成成啊,我是妈妈啊,你别跟那个绿毛坏孩子玩,他会把你拐走的,听话,跟妈妈回家......成成,你别走啊,成成,你快回来......”
跑出校门,张宇浩惊魂未定,非要拉着李渠安喝酒压惊。两人在大学城附近找了家餐馆,李渠安一直无话,被张宇浩灌了两瓶啤酒。
李渠安点上烟,舌头打着结:“你刚才对那个阿姨那么凶干嘛?”
张宇浩喝多了:“疯子一样,吓人。李渠安,再干一杯,你今天超赞啊。”
李渠安哈哈大笑:“我跟你说,我爸都不知道我会跳舞。前段时间回家里给我爸安坟,上完香,我给他跳了一段。结果,被同村的看见了,说我坟头蹦迪。”
“他们哪懂,这是艺术。来接着喝。”张宇浩醉得一只手撑在桌子上,依旧逞能。
李渠安摸了摸自己头发:“对,这是艺术。来,干了。”
张宇浩迷离着眼望向李渠安艺术感十足的发型:“你去过洗头房没?”
“怎么没去过,我们村头有一家叫忘爱,洗剪吹一条龙服务,价格便宜,技术一般般。我后来还差点进了正规军,科班的。”
“忘爱?什么?一条龙服务,这玩意还有科班?”
“怎么没有。”
“好好,今晚跟你混,我请客,你带我去长长见识。走,结账。”
两人酒还没醒,从餐厅出来稀里糊涂一路闲逛,张宇浩领着李渠安走近一片霓虹闪烁。街中间一栋五层欧式建筑金碧辉煌。李渠安抬头看去,一字一顿:“维,多,利,亚。”
张宇浩拽着李渠安摁着头往前走:“这是澡堂子。走,我们去洗头。”没走三十米,一条巷子里灯光昏暗,粉红暧昧。张宇浩两眼乱瞟,躲在李渠安身后,时不时把书包带子紧了紧。李渠安看见前面一女子红发红唇,想都没想,领着张宇浩拐了进去。
李渠安将鞋盒放在台子上,打了个酒嗝大喊一声:“老板,洗个头,吹干,然后用我这瓶新发蜡。”
张宇浩戳了戳李渠安:“用什么发蜡啊?”
李渠安被张宇浩戳疼了:“不是你送的嘛,干嘛啊?哎呀。”
红发红唇哭笑不得,估计眼前两位还是个初哥,就算不挣钱,肉到嘴边哪有飞走的道理,想着想着就把李渠安往里拉。
“完蛋。”李渠安酒彻底醒了,攥着张宇浩衣领就往外跑。张宇浩大惊失色,回过神来时,大街上的警笛声已经越来越近。
两人跑到巷子口,看见维多利亚洗浴中心门口停满了警车,警车前有几辆大面包。估计面包车上的便衣已经结束行动,警车来收网了。欧式大楼的铜门敞开着,到了门口,便衣给涉案人员一一戴上头套,李渠安跟其中一个对了一眼,仔细看了看,嘴巴长得老大。
张宇浩刚才跑太快,喘着粗气:“你认识?”
李渠安点点头:“我堂哥。赶紧走赶紧走。完了,我的鞋。”
张宇浩推着李渠安:“什么时候了,还顾着鞋。”
李渠安被张宇浩推着往前,还时不时回头看,街对面挤满了人,都在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人群中,一道人影好不眼熟,那人正和自己对视,纳闷了,今晚怎么都是熟人?
“吕笑笑?”
李渠安怀疑自己喝了假酒,大清早的完全抬不起头,反正他不敢正眼看吕笑笑。吕笑笑照例劈头盖脸,还行,一句话都没呼到他脸上。后来好多天,晨会上吕笑笑都没批评李渠安。反倒是李渠安,活干得越来越差,班加得越来越少,到手的工资也越来越低。
这段时间李渠安下了班就跟张宇浩混在一起,张宇浩带着他到处踩场子。跟着厂长儿子后面混,不愁吃喝。
李渠安彻底膨胀,那天晨会,他甚至主动找吕笑笑搭话,那欠抽的表情大概是说:“组长骂我吧,好多天没骂我了,我好难受啊。哎?有本事你骂我啊,你知道我朋友是谁吗?张宇浩,你知道张宇浩他爸是谁吗?他爸是厂长。吕笑笑,你赶紧哭吧。让你之前一直骂我。”结果,吕笑笑什么话都没有答。
第二天,毫无征兆,李渠安下完工被叫去人事,从人事出门回到宿舍卷铺盖走人。下楼时碰到吕笑笑。吕笑笑面沉如水:“不用这么着急,先去找个地方住下,再找份工作。小安徽是因为借了很多网贷还不上,活不下去了。你还小,别学坏。”结果,李渠安什么话都没有答。
前因后果李渠安多少知道一点,似乎是因为产能,又或者产品质量原因,厂里最近辞了很多人。只不过李渠安天天跟张宇浩混在一起麻痹了神经,变得后知后觉。同样后知后觉的还有张宇浩。几乎同时,张宇浩不再联系李渠安,李渠安本想打个电话问一问,打电话之前他去了趟商圈广场,周末,广场上好多人,唯独跳舞的人不在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大概这些天抽惯了中华,李渠安麻痹的神经仍再继续。他没去找新工作,当然,新工作是指工地搬砖、进厂打螺丝那种。他也想过出路,他跑到舞蹈培训中心觅求一份街舞教员的职务,希望能在培训中心碰到张宇浩那样的街舞爱好者。可惜求职的是一家少儿培训班,家长们看到他避之而不及。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州确实大,机会确实多。李渠安终于在一家培训中心的广告牌上看到了成/人两个字。只不过,他没有当上街舞教师,反而花了两万多学费。那所培训中心美其名曰网红孵化基地。李渠安交了学费,每天上午学舞蹈,下午拍短视频。也许是SRT2000的功劳,李渠安的街舞视频还真有人点赞。只是SRT2000毕竟带有程序,没有新程序输入,永远都是重复的几套动作。七八个视频拍下来,李渠安的程序用完了。
签他的经纪人不过20岁,艺名六总监。六总监跟李渠安有代沟,但沟壑不算太深。不是李渠安太新潮,而是六总监太时尚。六总监是看好李渠安的,2万块钱学费实打实,一点成绩没有也说不过去。六总监一直提醒李渠安,要会整活。李渠安才16,哪有那么多绝活?
六总监常说看中了李渠安身上的气质,要给他打造一套人设。忙前忙后,准备了一个多星期,攒了一群人,编了四五个本子。六总监带队,在番禺找了个农村。李渠安站在菜田里,飘逸绿发随着地里的韭菜翩翩起舞。六总监好不得意,马上,一个农村青年自学街舞成才的励志故事就要火遍全网,这么多天精心养育的苗终于要收获啦。上午跳完舞,下午六总监让李渠安下田,沉浸式割韭菜。李渠安不会用镰刀,姿势不对,摔了个狗啃泥,镰刀磕飞起来,差点切了六总监。
六总监大怒:“你他妈还想割我?”
六总监越想越气,眼前的农民居然不会种地。那喂猪会吗?也不会。养鱼会吗?更不会。
六总监骂骂咧咧:“你到底会什么?”
李渠安被吓到了,交了学费学了这么久,不发工资就算了,还发这么大火,脸上表情比吕笑笑还难看。李渠安也没多想:“总监,我会弯钢筋,还会打螺丝,打螺丝要熟练些。”
六总监差点被他逗笑:“妈的,拍你进厂?那我不得改剧本,成本超了你出啊?回去吧,不拍了,你不是进过厂吗?也行,你就当主播吧。”
李渠安不解,自己又不会整活,学也没上过几年,赶紧问道:“总监,我播什么?”
“卖惨!”
接下来的一周,李渠安被安排在一间房里,做起了跳舞主播。每天跳街舞,跳完舞就开始讲故事,故事都写在提词器上,照着念就行,不认识的字六总监都贴心地让文案标上了拼音。
可是编出来的故事经过李渠安的嘴终究会变成事故。起初直播间还有人关注,屏幕前偶尔会飘过几条类似绿毛猴子之类的弹幕,到最后弹幕都没有了,没人愿意看一个杀马特念经。直播间经营惨淡,人数几乎为零,不知道剩下的个位数到底是谁,大概是些更惨的人吧。
那天跳完舞,李渠安又被钉在座位上,对着提词器。屏幕上写的是“梦想”,他就这么机械地念着,念着念着念不下去了。
李渠安抹了抹额头,正欲摘下耳机,屏幕前突然一道尾焰特效。李渠安不敢相信,这是他直播间收到的第一件礼物:“感谢SRT2000送上的一架小飞机,谢谢,谢谢SRT2000。”
“好像也没有那么惨吧,我居然也能收到礼物。其实,说到卖惨,惨需要卖吗?我没上过什么学,只读到初中,不过我爱跳舞。而且我不仅会跳舞,我还喜欢跳高。初中时候,我是学校田径队一员,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弹跳力好,在学校运动会还拿过跳高第一名。体育老师告诉我,跳高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运动,因为它永远只和自己比。你每跳过一个高度,杆子就会上升,你就有了三次新的机会去尝试。至到最后一跳失败,才能衡量你的成绩。相反,惨呢?假如比惨也是跳高,每跳三次,失败了,杆子会往下降一点,再失败三次,再降一点。总有一个高度你会跳过去。你要相信,你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那一个。终有一个高度可以证明你的精彩。我出身在农村......”
李渠安下播时,公司所有人都在门口等着他。六总监满脸堆笑:“好样的,下场开始带货,你还没播完,一家化妆品公司就联系了我们,下场我们卖发蜡。”
李渠安到底挣了多少钱他自己也不清楚,一切都由六总监打理。六总监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
梦想?也许有吧。李渠安的梦想即刻到来,公司出面给他买了一套房子,首付款就是李渠安这些天挣的钱。
其实李渠安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可当六总监问他的时候,那个答案几乎脱口而出。
还好是现房,李渠安拿房的时候五味杂陈,他走进售楼部,取了钥匙,跟着售楼小姐去验房,同行中还有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对于这位绿发新邻居并没有另眼,甚至赞许有加。售楼小姐也多美言,这么年轻就坐拥一线不动产,年少有为啊。
走在小区里,绿草茵茵,花团锦簇,李渠安努力寻找着,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初钢筋工棚所在的位置。一行人跟着售楼小姐走到楼下,有一双眼在不远处紧盯着他们。售楼小姐似乎也注意到不远处的情况,赶紧带着他们往楼里走。李渠安回过头去,另一栋楼前,几名业主指指点点,正与一名红安全帽为房屋质量问题扯皮。李渠安验过房,站在窗户前,也许是梦想的力量,此刻竟战胜了恐高症。他俯瞰整个小区,隔壁楼下,红安全帽已经消失在花团锦簇中。
李渠安刚回到公司就被六总监将钥匙扣了下来。他被人举报了,未满十八周岁禁止进入主播行列。六总监也很无奈,这种事不告不发,民不举官不究。不知道动了谁的蛋糕,或者得罪了谁。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跑路,没有沮丧,内心毫无波澜。他知道,自己的杆子还可以往下降一降。自己也不想和谁比,拿了一手烂牌,出完就是胜利。
虽说花了两万块钱,却学到了许多经验,比如未满十八周岁不仅不可以进入主播行列,未满十八周岁也需要在监护人的带领下才可以买房,这些可不是一根中华烟就可以换来的社会经验,这学费交得值。
但他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十八岁才可以上网吧,十八岁才可以买烟,十八岁才可以做主播。
十六岁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一名农民工?
李渠安一刻也未停留,他要成为农民工,他也只能成为农民工。李渠安又一次坐上巴士,在城西立交桥上转着圈。回到工业园已是夜晚,李渠安顺着街道走下去,看着中介门口一张张招聘启事,玻璃墙上再也没有张宇浩家的信息。
“吕姐,别!”
就像在天台上,李渠安冲向吕笑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打火机:“你疯啦?”
吕笑笑真的笑了,仰天长笑:“怎么又是你?”
李渠安要请吕笑笑吃夜宵,吕笑笑没同意,她在便利店买了一打啤酒,两个人坐在电子厂门口,就着电子厂紧闭的大门,以及大门内曾经发生的故事喝了起来。
吕笑笑要了根烟。李渠安犹豫半天,最终还是将这根迟到的烟敬了出去,李渠安问道:“会抽吗?”
吕笑笑摇摇头,又伸手找他要打火机。
李渠安掏出刚才抢来的打火机,看着打火机上的字,振辉人力资源。“你也有?”
吕笑笑点上烟,猛吸一口,咳了半天,点点头:“何止有。”
不等李渠安开口,吕笑笑说:“厂子没了。机械臂的问题,经常坏。后来又进了一批机器人设备,调试阶段发生爆炸。”
李渠安嗯了声:“听说过,没想到这么复杂。你和振辉中介是怎么回事。你刚才干嘛要那样,纵火可不得了。”
吕笑笑冷哼一声:“你信命吗?”
李渠安愣了愣神:“总有好命歹命,也总有更好的命,更歹的命。”
吕笑笑接着说:“那人又在骗小姑娘,以招工的理由连哄带骗,骗到里面去玩弄。很久以前,那个小姑娘就是我。”
李渠安赶紧从吕笑笑手中夺回打火机:“别啊,烧死人怎么办?”
“怎么办,就是命。”吕笑笑又咳嗽几声,接着猛灌一口酒:“我信命。从小学到初中,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是每一次考试,次次都是第一,这样的概率能有多少?可是我家里穷,妈妈多病,爸爸烂赌,你说碰上这样的父母概率能有多少?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是老大,生了一个是女孩,再生一个又是女孩,这样的概率能有多少?读完初中,家里就不许我上高中,只让我去读技校,学费几乎全免,因为半工半读。差不多从开学第一天就在打工,不仅被厂里剥削,还要被学校剥削。挣到一点点钱还要供妹妹,还要供赌鬼爸爸。刚毕业,这个男人说帮我找工作,我什么也不懂,被他骗,欠了他好多钱,利滚利,还不起就只能拿身体还。你说,摊上这样的命概率能有多少?”
李渠安叹了口气,又递给她一根烟,为她点上:“所以你要报复?”
吕笑笑哭了:“你以为就这样?之前谈了个男朋友,在建筑工地工作,他请我吃饭,还带上一个朋友。他们非要让我叫上二妹。我二妹当时被我从村里带了出来,在广州读卫校,二妹才十六岁啊。吃完饭,那人说送我妹妹回学校,我心想,一个大学生应该不会太差,就同意了。结果他欺负了我二妹,还让我二妹染上了脏病。出了事之后,男朋友跑了,他也不认账。这样的概率又能有多少?以前在生产线上,每天看着你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浑浑噩噩,我就好恨,我就想骂醒你们,非要浪费生命吗?可有什么用?想想你们也是命苦,都是命,谁都躲不过。”
李渠安猛地将啤酒甩在地上:“畜生。那天晚上在维多利亚洗浴中心......”
吕笑笑哭着哭着笑了:“对,是我报的警。我很奇怪,你和他的名字就差一个字,老家也在一个地方。为什么你的个人信息表里面家庭成员那一栏是空着的。”
李渠安扔掉烟屁股,狠狠踩了踩:“可能也是种概率吧......”
李渠安说完自己的故事,吕笑笑泪也流完了。
“后来,我二妹疯了,人也找不到。我妈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我爸头上,我爸又新欠了一屁股债,下辈子也还不完。讨债的要来我家抢我三妹,我妈活不下去,点了煤气罐。那天我去天台,结果遇到了你。这就是命吧。”
故事说完,吕笑笑起身离开。李渠安也站了起来:“吕姐,其实那天在巷子里,我和张宇浩什么事都没有做。真的,百分之一百。吕姐,厂子关了,你以后怎么办,我们还会见面吗?”
吕笑笑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元硬币递给李渠安。李渠安接过硬币,学着吕笑笑在天台上的模样往天空抛去,捡起来又往上抛,连续三次。结果都是反面。
吕笑笑对着李渠安抿了抿嘴,转身离开。
“吕姐,你听我说,吕姐,吕姐......”李渠安一边说着一边往天空扔出硬币。
“吕姐,你快看,这次是正面。真的,再试一次,你再试一次啊。哪会那么巧,再试试嘛,总有一个高度你会跳过去的。”
所有的不期而遇都很神奇,就像是概率。张宇浩本来刚补完课准备回家,李渠安则在大学城营业点送快递。两人骑着电动车背道而驰,在同一道斑马线前停驻。
这顿饭是李渠安请的,有烟没酒。吃完饭,张宇浩提出一起去华南工程大学故地重游,晚上学校里有毕业演出,李渠安欣然答应。
毕业晚会很热闹,街舞社的舞蹈很精彩。
李渠安和张宇浩站在最后一排,李渠安问道:“还跳吗?”
张宇浩苦笑一声:“哎,学习紧,不跳了。你呢?”
“我也不跳了。工作忙。”
张宇浩一脸惋惜:“跳啊,哪怕当一个爱好,他们......”张宇浩努了努嘴:“他们当时都不如你。哎,我也想站在上面,我相信五年后站在上面的人就是我。”
李渠安眼神注视着前方,看着舞台上的大哥哥们,那场比拼,好像赢了,又好像从来没赢过。李渠安缓缓说道:“不跳了,总不能一辈子做一台机器。”
看完晚会,两人出了校门准备告别。
张宇浩大咧咧笑着:“没事,我家其实还好,杆子往下放一放,能撑过去。你以后准备......”
李渠安低下了头:“再说吧。”
“别再说。再说,广州城那么大,你非得在大学城送快递?”
“嗯,准备先上个五年制大专。”
“先把头发理了。”
“好。谢谢你送的小飞机。常联系。”
“最小的礼物了,等我发达了,请你抽中华。常联系。”
那枚硬币再也没有抛向空中。在大学城附近的一间理发店,李渠安用一元钱享受了一次一条龙服务。他始终记得,当他推开理发店大门时,有位姑娘,冲着他笑。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7/29 20:4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7/29 20:45: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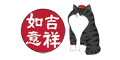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3-0 届
:风云523-0 届
 Post By:2022/8/1 21:17:2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8/1 21:17:26 [只看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