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肯将碧血写丹青。千古,侠之大义自古已有之。文人,在人文方面,创造者,思想者。侠,俜,孤独,武艺高强,见义勇为,舍己助人的品行。梦,难以实现,在本文中,我更愿意把“梦”引申为突破。
如此,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意思,自古已有,思想者创造出的一种从善意角度出发的突破。
肯将碧血写丹青,这句原也是从突破角度而来,侠客梦多半“有违”,有违于现实,有违于制度,有违于社会背景,执意,碰得头破血流,原也并不稀奇。
少年,我们都有侠客之梦,然于时光的荏苒中,噬血淡去。这是一种想要突破和改变的豪气,这是一种善意的执拗,而为礼法制度所囿禁。这其实是一种对俗事和已成世界的挑战。
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人以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用暴力触犯律例。当然,韩非子本身是法家的代表,且是有一番治国兴邦大志,决意力挽狂澜于未倒的皇族后裔,它的观点从自身立场出发,为自身目的服务,未免有些偏颇。
首要说,儒家和法家最初建立思想体系服务对象就不同。孔子游说六国,宣扬的儒道是以仁治国,仁政,是对统治者的要求;法家最早的创始人已无证可考,有说最早可以追溯至夏商,有规则,有限制,就是法家。而规则和限制是管理者对被管理人的要求。
其次,儒家重在扬善,法家重在惩恶。儒家强调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以礼待人,人之所以为贵者,以其有礼有信。圈重点,注意看这个“贵”字,它教导人类向上向好,以善出发,塑造一个更美好的个体。法家强调的是法制,定分止争,虽然法与儒同样是治理国家,它规定是做人的一个下限,圈重点,注意这个词“下限”,即你不能够坏到哪里去。你坏到一定的限度,就要受到惩罚。
第三,修儒修法,起点不同,所要的结果和目的也不同。儒家以德教诲世人,强调自身之完善,美好,以儒道修身,达到一定境界,你便从心所欲不逾矩。法家以制度管束世人,它不管你的德性如何,甚至不太专注你的初心,只用尺度衡量,你是不是超越了底线。但世事多复杂,有词曰:情有可原,在法与情冲突之下,就会出现韩非子所说的那个“乱”字和“犯”字。
曾经和朋友谈东野圭吾,乃至日本悬疑文学,普遍的一个存在,为犯科者鸣冤。朋友说,这是日本文化中的一种传承,同它的侘寂、幽玄、物哀一样,在法与情的冲突之下的或可谅解,平淡悠然。纵使不能为所谅解,亦让闻者心生恻隐,难复追讨谴责,一种避毁就誉的恕罪心态。
我未见认同朋友所言,然向往以善意出发观世情百态,向往以美好修身,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如前述,侠之中有“有违”因素,有违是好是坏呢?这要看“法家”的“法”是定点还是动点。有人说,在先秦诸子诸家之中,唯独法家的思想,要献出生命以践诺,流出碧血以祭奠,它们称法家为“血染的思想”,每个法家思想的立起,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如商鞅,如李悝,如吴起。
既为“变革”,那么,“法家”的“法”其实是动点,是可以变的。认为“法”是定点,不变的,认为我们被教育既成,只能遵守,是因为我们是被管理者,文人不是政客,也被束之于此。然,文人又是有思想的,有创新意识的,他可以无边无际的想,却在现实中因为各种“有违”而碰壁。
于是造出了“侠”,我根深蒂固地认为,“侠”这个词,是文人造出来的,之后以精神宣讲传于世人,而有世人模仿其精髓、骨胳、皮肤,将文人“破”、“立”之存想托付于世间。
这种想,解决法律、制度排于外之世道不公,有之;解决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却要凭揽日月之光辉普照人间的鸿志,有之;解决忠义、道义之树立彪炳人物,有之;解决凡人之所不能,却寄托美好之愿景,有之……一种柔软地“有违”向现有制度发起的挑战,一种己所不能幻想超人式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
如此,侠义之精神永存。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法”原本是很难完善的,思想者、创新者善意出发的“破”“立”之道,有助于世间的向上与美好。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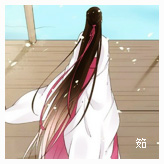



 :涵空日月
:涵空日月
 :陶白阁
:陶白阁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0/2/11 17:25:4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0/2/11 17:25:44 [显示全部帖子]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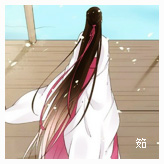



 :涵空日月
:涵空日月
 :陶白阁
:陶白阁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0/2/11 17:26:23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0/2/11 17:26:23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