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辛的家在一个破烂的矮篱笆围成的院子里,那一年的月光总像是叽叽喳喳的鸟叫,散落在院子各处,聒噪且张狂。
田辛趴在破旧的窗棱上向外张望,月亮的清辉洒遍大地,远处成片的塔柏矗立在微风中,组成一道屏障,似乎有某种力量在塔柏那头冲撞、胶着,像杰克的魔豆一样妄想肆意疯长,却被面前这一道翠绿裹挟。
塔柏的那头是一片坟地,田辛去上学时,塔柏是他忠实的听众,沿着土路向西,哼着原生态小调,田辛的求学之路并不孤单,但是到了夜晚,比如此时,嗅着发蓝的月光,望着肃穆的塔柏,他却感到了忧伤和惆怅。
该睡了,睡一觉就好了,他这样告诉自己。
第二天睡醒,同往常一样去上学,沿着塔柏一路向西,不同的是,意外发现散落在塔柏树下的狗粪,一处,两处,细数竟有十多处。
往后的日子里,塔柏树下的狗粪未曾消失,可田辛却从未见过这群狗,仿佛它们是神秘星球移民的邻居,在日光里穿行却留不住身影,唯有零星的残迹可以追寻。
田辛没有父亲,和母亲住着红砖老房。
原本他是有父亲的,他的父亲在城里修楼房。十二岁那年的暑假,他去父亲租住的阁楼里住了三天。
城市的夜晚霓虹灯闪烁,他从阁楼窗户里,看见对面门口涂着腥红色唇脂穿着艳丽短裙的迎宾小姐、虫鼠随意穿行的垃圾堆以及头发光亮笑容和蔼的男人们。
这些灯红酒绿都被迎宾小姐身后那半开的玻璃门隔绝于外,门里是大片大片的黑暗,以及偶尔亮起的明黄色光点。
田辛伸着脑袋看,他看见了父亲的左手搭上那半开的玻璃门,准备进去时却犹豫着看向他的阁楼,田辛急忙缩回脑袋,趴在墙壁上,心脏拍打着墙壁,他真怕父亲听见咚咚咚的声音。
又迅速转身爬回床上,用被子裹的严严实实。他的脑袋里是迎宾小姐笔直白皙的腿,那么长的腿,像极了矮篱笆院子里看见过的流星拖尾,让他惊心动魄。
还有父亲的手,用力推门时小臂上呈现的肌肉。
那几夜,长腿和手臂交替在他脑中出现,似乎有种神秘生长的力量在田辛体内凝聚,像疯狂生长的枝丫顺着血液在身体里横冲直撞,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有父亲的日子持续到那年冬天,雪花飞舞,白蝴蝶一样的雪片翩翩落地,一落地就死了。
他的父亲在高空作业时及时拦住了失足的同伴,自己却从几十米高处坠进尘土里。
白蝴蝶翩翩起舞的时候很美,田辛在矮篱笆围城的院子里昂着头,看天,白蝴蝶落在他的脸上。
父亲摔下去那会儿,会想起他的吧?会想起母亲吗?他凝视着素白色纷飞的世界,又望向凛冬里那排翠绿的塔柏,一定是那片塔柏树裹挟了他的情愫,不然为何他的眼里有悲心中却无伤。
如果不是那些奇怪狗粪的出现,田辛对于塔柏树里面的世界,并无好奇只有敬畏。满月、狗粪、呜咽、伴随着窸窸窣窣声,撩拨着时常在夜晚惆怅的他。
这夜月明星稀,幽蓝色的月光打在身上,驱散着周身的温度,田辛终于安耐不住,寻着塔柏树附近的狗粪,仔细辨别着窸窸窣窣声,一头钻进塔柏林深处,松针划过脸颊时便用手去挡,又刺痛手臂。
脚下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随着呼之欲出的真相即将到来,原本他以为的窸窸窣窣声,已经像波涛一样汹涌。
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塔柏尽头的空地上,匍匐着成群的野狗,那是野狗们的低鸣声,月光像破碎的玻璃渣一样在野狗们的眼睛里跳跃,它们耸动的身影,被照落在地上,连成起伏的山丘。
田辛惊呆了,错愕的立在那里,听着自己心脏狂跳的怦怦声,像是等着被主人发现的小偷。
野狗们听见动静,整齐的回头,忽然一双手将他拉向塔柏林里,又急又猛。田辛跌倒又慌乱爬起来,看见一张清秀的脸,女孩子的脸,田辛想不起来她是谁,此时被她扯起胳膊,两个人头也不回的一路奔跑,松针刺的很疼,身后犬吠声此起彼伏。
他们被恐惧、未知、羞赧支配着步伐,唯有奔跑时风的凉意,可以稍微安抚。待到出了塔柏林也听不见狗叫声,两个人各自拍着胸口大喘气。
静谧的夜晚,零星的蛙鸣,他听见女孩说:“田辛哥,我不是故意要跟着你,是怕你有危险。”
田辛终于想起来这张清秀的面容是谁,绵花,隔壁邻居三个女儿里最小的孩子。
绵花看着田辛的眼睛,表情严肃,说的诚恳,也只有攥着衣角不住摩擦的手透露出紧张与不安。
田辛个子高过她一头,便也强装镇定的说:“以后可不许这样,我没事,你快点回家。”
于是绵花走在前面,田辛跟在后面,快到家门口时,田辛叫住绵花,叮嘱她今晚的事儿不能随便与别人说,不好。
绵花眼睛亮亮的问:“算秘密吗?”
田辛错愕着回:“算吧。”
绵花雀跃的心情和她的麻花辫一样藏不住。
多年以后,田辛在城里娶妻生子,依然习惯性的入睡前,行至阳台,更开阔的视野,透过黑夜的薄雾探究某一片远方。
而他的妻子则箍着他的腰,与他相依偎。
记忆的洪流里岁月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显斑驳,父亲的手臂,绵花的辫子,却偶尔能在他脑中略过。
田辛知道,那是警醒亦需要珍惜。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冠冠
:冠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1/9/5 20:30:0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0:0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2:1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2:1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2:2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2:2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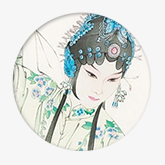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2:5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2:5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短路中……
:短路中……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2:5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2:5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4:4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4:4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6:0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6:0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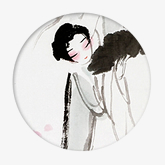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6:1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6:1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7:0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7:0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7:2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7:2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8: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8:4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8:4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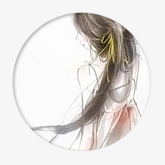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9:0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9:0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39:3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39:3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1/9/5 20:40:1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1/9/5 20:40:13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