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
寺庙梵音渐歇,诵经人方听到外面的雨声,淅淅沥沥地。
“无尘,你拿把伞到山门去。”
“是,师父。”
小沙弥自去拿伞离开了静室。诵经的人继续垂眸敲响木鱼,一下一下的木鱼声,是超度浮图塔断了的魂,是阻断几重山门倾塌的心。
“师父。”小沙弥回来了,“那位施主收了伞,不肯打开,说了一句话,转告师父,晴天淋雨,其觉也易,雨中淋雨,其觉也难。“
木鱼声断了两息,小沙弥不敢多言,只知自打他上山以来,每年的这个雨季,那人都会出现,天晴了离开,师父给他送的伞,他从来不曾打开,师父也不提其他。小沙弥以为师父如既往般不再说话,准备告退。
“无尘,请他到静室外避雨罢。”
“是,师父。”
到静室需过经堂,玄衣男子跟着小沙弥一路行来,伫立经楼廊下,对小沙弥说,他在此处等候。小沙弥挠挠头,心下觉得不太对,可眼前的客人一身煞气如吹毫可断的刀,小沙弥未敢多言,合什离开。
眼前琉璃瓦角,耳边梵呗隐隐,玄衣男子一瞬间恍了神,似乎回到十余年前,一身黄袍的青年隐入门内,一圈又一圈的御林侍卫层层守护,不许闲人踏进一步,尤其是他。巅峰的繁华一朝遁入了空门,徒留一夕又一夕的冷梦辗转,让他默默地年年来等,等那人出来,等,历史转身。
水月门内影子一闪,白衣人撑着伞停下脚步,是方才诵经的和尚。看着不远处的玄衣男子即使随意坐着,亦不掩绝世锋芒,那是十六岁领兵代守边关,以摧枯拉朽之势覆灭漠北十部,二十岁挥兵西域气吞山河的青年。十余年过去了,他在寺内诵了十余年的佛经,前尘依旧历历。
“我年年来,便是想跟你道一声歉。”玄衣男子对水月门内伫足不前的白衣人说。
白衣人嘴唇动了动,却不知该说什么。
“十年前,我罔顾皇家颜面,累你受苦,把你的忍耐当纵容,这后果,本该我承受,是以定要亲自来说一声抱歉。”玄衣男子涩然一笑。
白衣人心中一痛,终于出声:“每年你来,我都任你在山门外淋雨,我虽有怨恨,但并非全部怨你。”
玄衣男子心中大震,要逼眼前人说出一丁半点的情尤其是怨可不容易,不敢接话,只盼他再多说一点。
白衣人似是瞧出了眼前男子心事,微微一笑:“我自陷心魔,明知你执著是苦,我逃避亦是苦,却无计可施,只能困在空门。”
玄衣男子知白衣人有了决定,这决定可能未能如他所愿,唯试探地说:“我既不甘心你不出来,也高兴你不出来,你不来,我便可知你对我们之事未有选择,既未选择,于我是便尚有希望。”
白衣人摇摇头:“今日见你之后,我即离开此处,他日有缘还会相逢,若相逢,再说其他吧。”
语罢,他即转身走了,白衣轻渺如云淡风轻。黑衣男子却悲喜莫明,心中空荡荡的不能着落,如这纷纷的雨,淅淅沥沥打在石板上,回荡的水花,一着落便碎了。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11/8 20:30:0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8 20:30:0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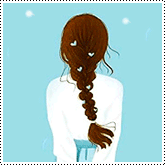


 :云深不知处
:云深不知处
 :阿湛
:阿湛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11/8 22:26:2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8 22:26:2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3 届
:风云0-3 届




 Post By:2022/11/10 18:19:4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10 18:19:42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