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看《翦商》时,关于吐蕃旧事,我便想起了曾经看过的松赞干布时期的一些旧事(或可说是传说)。
当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政权后,迎娶了泥婆罗的尺(赤)尊公主(也有说此事是书杜撰的),公主携带了一尊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其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而文成公主带来了一座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
据传,尺尊公主想修建一座寺庙,用来供奉佛像,结果修一座倒一座,后经卜算,发现西 藏地形为魔女仰卧之形。传言,罗刹魔女为凶神,如若不镇,则永无宁日。于是当时的王松赞干布命人修建大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修建小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另修建了其余诸多寺庙,称镇魔十二神庙。
如果将此传说与《翦商》和《叫魂》联系起来,那么赵无忧大概算是罗刹魔女附身?
铁勒王后所言:“沙州的佛门三百年来,一直帮着赵家人镇住地下的东西。”所谓的“地下的东西”难道就是魔女本魔?
其后,我又去搜索了一下西 藏的其中一个古老教派苯教,因为吐蕃原来就信奉的苯教,其中便有“役使鬼神”这一活动。可惜当时太困,脑子有点不清醒,加之被宏大的设定所震撼,未能细究。
但我依然想说,作者在写这个系列时,必定是花了比我要多的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查询资料。
而我在看的时候,只能呐喊——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叫魂》将《翦商》的剧情又往前推了一大步。
《翦商》中,只存在于背景的铁勒和拜火教,缓缓显出。沙洲第四阵营,以一个出乎意料的方式登场。
当我以为拜火教将有所大为时,却发现拜火教居然面临了被灭的绝境。以王后为首的拜火教,和以拔野骨漠罕为首的“真神”教(作者还没写什么教,姑且这么称呼)之间的博弈,应该是宗教线上的另一条支线。
拜火教的真正出现,算是开启了沙洲板块上的宗教间的正式博弈。佛教、拜火教、吐蕃凶神,还有拔野骨漠罕派的“真神”教,按照其目的而言,佛教与拜火教为一方,吐蕃凶神与“真神”教为另一方。(或者,所谓的“真神”其实就是吐蕃凶神,甚至就是沙洲地下的“那个东西”)
至于程子安的巫僧这一派,他们是击杀妖魔的急先锋,按理说,他与佛教的目的应该一致。沙洲的十六座寺庙,镇守着地下凶神(或许还有罗刹魔女)。百年来,用尽各种方法,护住沙洲的平静。既然巫僧的职责是扫尘(也就是除魔),为何他却试图对十六座寺庙赶尽杀绝?从目前情节来看,是因为“最后一个赵家人”——神秀。
赵家人,首先是赵梦鼎,已死。他肩负着不能透露半分秘密的使命,活得极其疲惫,耗尽心力,最终被杀。
赵无疾,赵梦鼎的儿子,已率领沙洲士兵出征,三千骑兵,五千匹马和骆驼,且沙洲久无征战,此等阵仗,真的不是在儿戏吗?赵无疾哪来的自信和勇气,能“创造比昔日李长钧还壮烈的盛举”?(梁静茹给的吗?)
赵无忧,赵无疾的胞妹,一个自小就被众人迁就,只为她不生气的存在。她是释放凶神的重要中间商。她从沙洲被“瞬移”到铁勒,又从铁勒回到了沙洲,她到哪,凶神就能跟到哪。(感觉带了一群保镖一样)
赵妙音,赵梦鼎的妹妹,小普善院的院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什么重要的都不知道的半知道者。她与程子安之间的纠葛,好狗血……当年赵妙音为了赵家,辜负了程子安,而如今,程子安为了他的目的,背叛并囚禁了赵妙音。(脑子里自动想起一句话:风水轮流转。又想起了杨子的那句台词:苍天饶过谁)
神秀,赵梦鼎之侄,十二岁起便遁入空门修禅。神秀的出场极其简单:“一尊佛,一个蒲团,蒲团上一个年轻的僧人。”这个年轻的僧人便是神秀。不难看出,慧因法师对神秀抱着极大的期望,他需要神秀在时机到来时,成为可以镇守并维护沙洲的“佛”。
赵无疾、赵无忧、赵妙音和神秀,这四位是已知现存的赵家人,程子安为了要抓神秀,或者说是为了赵家人,不惜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位活了超过三百四十二年的巫僧。他的目的,我至今还没参透。(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看帖的时候,正值最想睡觉之时,所以忽视了一些重要情节。)
如若他想斩妖除魔,原本是可以和沙洲的佛教联手,可他却为了一个神秀,或我还不知道的目的,走到了佛教对立面。这让我很困惑。他对赵妙音说:“而且你是赵家人。佛门在沙州的最后结局,你应当在场。”这句话里,充满了对于赵家、对于佛门的不满。这种不满来自于何处?
当年李长钧镇压龙神郭日那保,以程子安的巫僧能力,确实可以手到擒来,况且这么多年,他又习得了别的法术。赵妙音猜程子安是拜火教的教主,程子安也间接承认了,但这么多年拜火教各自为政、群龙无首,这样一盘散沙的西域,又为的是什么?难道不应该联合起来吗?当年大晋公主的懿旨到底是什么?
怎么办,脑子实在不够用了!
而今,程子安在发现了神秀的能力后,他说:“那我只好再替佛门,寻找一个体面的退场。”啊,这个“退场”是什么?是佛门最后被灭的结局吗?又“体面”在哪?
然后,他和赵无疾一起出征了。好吧,以程子安的能力,只要他想,匈奴确实不够看,别说赵无疾只带三千骑兵,哪怕赵无疾一个骑兵都不带,只要程子安在,他就只会胜,不会败。
程子安最后与赵妙音说:“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这句话,有种宿命之感。再也不会见,是因为他笃定沙洲会被灭?
啊,余晓风,你在哪里?你画了一洞的各种像在哪里?
程子安对阴其文说“我也是”,意思是他也放心了,他放心个什么啊?阴其文难道不知道龙神要出来了?难道不知道佛门要面临困境了?难道不知道沙洲地下镇着的东西也有可能要出来了?如果那东西出来,大家一起game over了,还放心个什么?阴其文既然都知道,他是打算赴死吗?所以程子安的放心,是说让他安心赴死?
又一次被自己蠢哭了。
如果问,宗教博弈中最让我震撼是什么,那么我会说是葛萨娜娜的那句话。
葛萨老爹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命么贱得很,祖祖辈辈还不是这样。”一辈子没做过坏事的葛萨老爹被剁成了肉泥,成为了“羊肉”。面对接连灭掉的火,面对降临的黑暗,葛萨娜娜有着极度虔诚又极度坚定的信仰,她说:“世界不该是这样。错,就是错。罪,就是罪。黑暗,就是黑暗!真神就该无垢光明!世界属于真神。我属于真神。”于是,她便成了可以对抗黑暗的“真神”。
葛萨娜娜自杀这一段,太震撼心灵。少女对“真”的向往和对“善”的追求,成就了光的到来,那是任何黑暗和邪恶都无法打败的东西!
正如王后所言:“信仰无善无恶。但人要有信仰才能活,而人有善恶。这是我们生而为人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此句在我看来,是在呼应本篇的开头,并由此提出了本篇的其中一个主题。
清代的秘密宗教颇多,且或多或少存在反清的苗头,所以清代对这些教派同场只用一种手段,严厉打击和镇压。
而王后的话,对这些教派从根本上定了性。
佛教也好,拜火教也好,吐蕃凶神也好,“真神”也好,当你心存善念,那便带来善,当你心存恶念,那便带来恶。“神”需要人的信念之力,善的信念造就了“善”之神,恶的信念造就了“恶”之神。
于是,葛萨娜娜的善带来了光明,拯救了差点被黑暗吞噬的铁勒。而不知道谁们的恶,带来了黑暗,黑暗带来了黑色的魔神,他们吃人。
杨元西差点成了吃人的魔神。
他有着纸扎的牛头,他的魂被塞进这样一个容器里,成为了可以被龙神郭日那保唤醒的牛头魔神。那么,还有多少魔神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唤醒的?叫魂,叫醒了杨元西,让他知道,他还有人类的臂膀,他还是个人。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谓的魔神,也不过是“人”,只不过他们没有被叫醒,他们没有了人的魂。
如果说《翦商》中,政 治博弈和宗教博弈之间的三线并存,那么到了《叫魂》中,明显是宗教博弈为主。
秋延宗承担了本篇的全部笑料。
他真的聪明,但在宗教的博弈中,他又显得极其渺小。从沙洲到铁勒,再从铁勒回到沙洲,他的存在始终处于“说重要吧,也确实有那么几分重要,说不重要吧,也确实不怎么重要”的状态。
他带着几个姑娘,一路上就是一个“联合国”:一个大夏的使团副使,一个匈奴草原的公主,一个铁勒的普通少女,还有一个沙洲节度使之女。(当然还有一个婢女,一个葛萨老爹和一群羊)
这样一行人,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他们的信仰不同,出身不同,却能和谐地组合到一起(秋延宗耍宝被揍不算),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事。由此可见,人其实能很好地相处。抛开政 治和宗教,抛开身份和地位,这一段旅途,是整篇中能让人嘴角上扬的部分。
相比之下,政 治和宗教的博弈就血腥得很。
赵梦鼎、曹知礼等都死于政 治博弈。
慧因法师涅槃,葛萨老爹被杀,葛萨娜娜自杀,安七哥变成龙神第八只手中的骷髅,还有无数没有姓名的人,在宗教博弈中丧身。
借助信仰之力诞生的“神”,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心怀各异的追随者,还有普通又虔诚的民众,在这样浩瀚的背景下,组成了一幅幅黑白交织的图,成为传说与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粒沙。
当年两位公主带去的佛教,与吐蕃本土的凶神博弈,这何尝不是一种新旧之争。盛极必衰,只是这一场衰是有心人人为之。而多年后,已经站稳了脚跟的新教,又对上卷土重来的旧教。两个教派之间的博弈,绵延这么多年,又怎会轻易就结束。
慧因对程子安说:“无中生有,从有而返空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一句,我以为是讲尽了这段故事的因和果。
只是,当那些传说带着血和泪,借由作者的笔展现在我面前,宏大、奇幻、深邃,而我,在被震撼之后,却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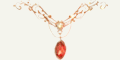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4/18 9:45:5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8 9:45:5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4/18 12:55:4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8 12:55:4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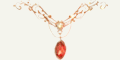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4/18 13:41:4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8 13:41:4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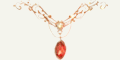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4/18 13:42:3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8 13:42:37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