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说,人生不过是片刻的欢愉,片刻的痛苦,剩下的都是逝去流年的虚无。
倘若我还是鲜衣怒马的年龄,还是衣着单薄,却偏偏爱站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的惨绿少年,听到罗老师这句话,我定然有知音难觅、相见恨晚的壮烈情绪,恨不得将这句话刻在门头,早晚跪拜,奉作人生圭臬。
因为那个年纪的人类幼崽,正肆无忌惮地朝着四面八方伸出触角,从一朵花的枯萎,一片叶的凋零中,接收到时间变幻的寂灭,又从一句银铃般的笑声,一声无端而来的斥责中,体味到人际关系中的无常,这寂灭和无常,组成的不正是生命的“虚无”吗?
这“虚无”是如此纯粹,没有对未来和现实的考量,纯粹是一个懵懂的生命对周身环境感知后,作出的最原始的判断。倘若将“虚无”理解为人生的主体,那我们在十八九岁的年龄,便早已洞透了“虚无”的真相,往后的岁月中,不过是用各种现实理由,将这“虚无”装扮得花枝招展罢了。
然而,人生的奇妙在于,那早早体会到的“虚无”或许并非人生的真相,那只是一个听起来很酷的词语,一个将自己隔绝于普通人之外的壁垒,一个生命体对无力干涉现实后,用于安放自我的巢xue。
“虚无”不是万能的,“虚无”是自以为洞透人生的幻觉,嘴上挂着“虚无”,便意味着可以放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便意味着可以毫无愧疚地虚度光阴,可以将自我幽闭的感知,无限地向外延展,以此来掩盖内心的脆弱。
“虚无”不应该成为对人生的概括。
当“虚无”逐渐被各种琐碎所填满,这“虚无”便丰盈成为了生活本身,若是一直执着于宇宙的幽深无解和人生的瞬息即逝,又如何能从寻常的日子中寻找到快乐。
逝去流年的虚无,这说法渗透着浓浓宿命式的宗教意味,仿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间和往后将要经历的时间毫无意义,仿佛时间只是时间,只是从每个人身上无情地碾过。
它完全消解了人生存在的意义,用大而无当的“虚无”概念去解释一切,换回来一声声唉声叹气的喟叹,又从这些喟叹声里,再获得几分洞透人生的满足。
若说成长,现在与过去,我所改变的便唯有这些一家之言的看法。当精神已经“虚无”,现实再如何惨烈,依然能置身事外,这就是虚无一派的唯一意义。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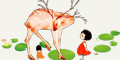

 :娱乐圈顶流嗜睡演员
:娱乐圈顶流嗜睡演员
 :花小獾
:花小獾
 :一片林深时见鹿
:一片林深时见鹿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11/2 16:31:54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3/11/2 16:31:54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