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盏午夜街头 昏黄灯光
照亮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
借一寸三九天里 冽冽暖阳
融这茫茫人间刺骨凉
借一泓古老河水 九曲回肠
带着那摇晃烛火 漂往远方
借一段往日旋律 婉转悠扬
把这不能说的轻轻唱 ”
易行坐在大巴车上摇摇晃晃,这山路十八弯,弯多却不算陡峭,柏油路也修得平整,听着耳机里毛不易的歌声,看着车窗外朝阳缓缓爬上山坡,他打了个呵欠。大清早就被父母喊起来坐车赶路,回老家祭祖,他还困着呢。易行将头在靠背上一歪,睡个回笼觉先。
“旺旺旺!”什么动静!易行一惊,腾地坐起来,眼前一摸黑,怎么回事?这是哪里?一串问号飘过,他有些懵。随之又是一串弹幕在脑海飘过,等等,太快了,没看清……弹幕又重新飘过,这次降速了,易行睁大眼睛:“1943年冬,放鸭老汉,兼做摆渡艄公,任务完成,方可醒来。”
我穿越了?什么跟什么啊,这是!还是在做梦?易行揉揉眼睛,这触感真实,似乎不是梦。再看周围,双眼已经习惯黑暗,模糊中可以看出他正身处一个草棚,坐在竹床上堆的干稻草上,再摸摸自己的手,青筋暴起,手掌皆是老茧,一双老汉的手。再摸摸下巴,几缕稀疏的胡子,他长叹一声,看来这真是穿越了,还变老了,但没变强。他站起来,伸伸胳膊,转转腰,不错,这身子骨还挺硬朗,是个劳动人民。
“汪汪汪”,又是一阵狗叫,易行钻出草棚,喝斥一旁木桩拴着的狗子,可狗子还是朝某个方向咆叫着。易行随之望去,浅淡月色下,一个身影正缓缓走向河里。不好,这是要跳河!救人要紧!易行不假思索大声喊道:“哎!站住!”那个身影一愣,正茫然中,易行已跑到她身边,架住她,拖往岸边。是个年轻姑娘,衣衫单薄,裤子已经湿了。易行将她拖到岸边沙石滩上,大声呵斥道:“年纪轻轻,就不想活了!”
那姑娘身子一软,瘫坐在地,嚎啕大哭起来。易行不忍,又不会劝,手足无措间,忽然一想:救这姑娘就是我的任务吧?救了她,我也就醒了!那我说啥也要救她!相信光!
“别哭了,闺女儿。我那棚里有干衣服,你先去换了吧。”
姑娘抬起头,泪眼婆娑,她摇了摇头,说:“大爷,你是个好人,可我活不下了!”
“说啥呢!世道艰难,更要活着熬!熬过去就好了!”
“熬不下去了!家里没人了!我爹被小鬼子……”姑娘捂住脸,呜咽着。
易行沉默了,好一阵,缓缓道:“这世道,哪家不是家破人亡……还得熬,不熬怎么报仇,活着才能报仇,相信我!”
姑娘沉默了。河水呜咽,不知何时,飘起了细细的雨。
易行忽又问道:“闹鬼子,村里姑娘都跑上山了,你怎么回村了?”
“我爹病了,村里大叔上山传信给我,我采了草药,趁夜回家,想给我爹熬药。谁知被村里二鬼子晓得了,带着鬼子搜上门来。他们,他们!把我给……我爹去拦,被一脚踢死了!”姑娘捂住脸,一声声嚎啕。
易行嗓子头也哽住了,他不由地握紧双拳。
“小鬼子走了,我爹死了,我躺了两天。今儿白日挣扎起来,村里叔伯帮衬着将我爹埋了。我……我就来追我爹了。”
又是沉默,沉默如这漆黑的夜,刺骨凉。
易行努力搜索自己那点有限的历史知识,这里是苏南,过了河,翻过一个山头,那边就是新四军的驻地。有救了!
“姑娘,你去投军吧!找新四军!我送你去!”
“我……新四军……”姑娘还是茫然。忽地眼睛一亮,说道:“村里二毛就投了新四军。去年偷着回村,说那边给穷人分田分地,打鬼子!”易行激动起来,点点头,对对,就是新四军。
“大爷,你说……他们要我吗?我……”
“怎么不要!都是天下受苦人!闺女儿,去吧,去了好报仇!”
“嗯!”
“走,趁夜就走,我带点干粮,咱划船过河!”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河上起雾了,一阵欸乃之声,易行熟练地摇着船桨,无师自通,不愧是个老艄公。姑娘无言坐在船尾,身影单薄。前路漫漫,雾气沉沉。
母亲推醒易行,到站了。易行揉揉双眼,他还在大巴车上,回来了?回来了吗?那姑娘呢,一场梦吗?
昏头昏脑下了车,跟着父母回到祖屋,易行一路沉默。祖屋已经被村里婶婶提前打扫干净,父母放下行李,打量起墙上挂的老照片。父亲指着其中一张,对易行说:“这是你太奶奶,你太奶奶当年收留了你爷爷。”易行看那黑白照片,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底下一排字,1978年摄于某某照相馆。
“我爷爷是太奶奶收养的?我怎么不知道。”
“你爷爷是个孤儿。那年月,孤儿多了。你太奶奶在新四军的幼儿园里带孩子,一直未嫁,好像身体不好,就收养了你爷爷。”
“哦。”易行并不在意,转身开始收拾行李。忽然手中一停,几步跨到那照片前,细细打量,拂去岁月的烟尘,那眉眼似乎有些相似呢……
夜晚,躺在祖屋的木板床上,易行失眠了,窗前一轮明月,听,是谁又在唱:
“可是啊 总有那风吹不散的认真
总有大雨也不能抹去的泪痕
有一天太阳会升起在某个清晨
一道彩虹 两个人
借一方乐土让他容身
借他平凡一生”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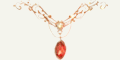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1/23 21:21:0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1/23 21:21:06 [显示全部帖子]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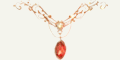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1/23 21:21:53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1/23 21:21:53 [显示全部帖子]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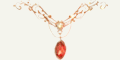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1/23 21:22:06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1/23 21:22:06 [显示全部帖子]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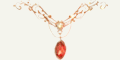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1/25 12:09:13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1/25 12:09:13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