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不破 是相逢早铸因果
待消磨 却成谁心魔
纵难舍 旧时月色亦蹉跎
书尽几册
西风扫落窗外枯叶,飘飘荡荡,孤零零地坠在地面。
这一幕落于醉君楼上的一位凭窗独酌的客人眼中,不禁一声垂叹。这客人长相甚是粗豪,身材魁梧,虬髯圆目,剑眉浓重而短促。将杯中酒饮尽,粗豪客人将目光自窗外收回,双目一翻,凛然生威。有因好奇而打量他的客人忙将眼转向别处。这醉君楼自来便是风雅公子聚集之处,甚少有江湖中人来此落脚,客人们虽是为他目中威势所镇,仍忍不住偷眼望来。
粗豪客人在楼上扫视一周,最后将眼定在墙上的一幅画上。
那画上一溪浅水,绕过满是金叶的树,碧波微起涟漪,两片金叶翩翩应风而落,堪堪滑在地边。直似两只翩翩枯叶蝶,缠绵凄然坠落,旁题一行小字: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
只双眉一蹙,暗暗摇头。
那边远远地一位锦衣公子见此,执起酒杯,向这窗边移步。一众客人又窃窃私语起来。
粗豪客正持象牙箸去夹一道“金藤绾玉”的点心。忽觉身旁有人站定,不着痕迹地将手按上座边的龙吟宝剑,另一手将点心纳入口中。
锦衣公子朗润的声音响起:“这位兄台,可愿与在下共饮,以慰独酌悲秋之情?”
粗豪客侧目,见是一介文弱公子,目中精光却显示着他的武功不弱。但听他说得直爽,疏懒地点头。右手却仍按在剑上。
锦衣公子似是浑不在意,一拱手,拂衣落座:“那在下便叨扰了。”顿了顿又道,“在下金陵风净痕,见兄台凛然一表,一时兴起,欲与吾兄结纳,不知吾兄怎生称呼?”
风净痕的名字在江湖中甚是响亮,金陵风家,独掌南方武林,提起风家少主风净痕,江湖上几乎无人不晓。
粗豪客面上依然淡淡的,却不似方才那般警戒与蔑视,道:“沈疏。”
风净痕“啊”地一声,江湖人常将“南风北疏”并谈,早心向往一见,今日竟有缘在此相会,不禁喜上眉梢:“素闻沈大侠文武全才,不想竟是这幅威豪之态,倒还真出乎在下的意料。”
风净痕此言不虚,风沈齐名,风家世代定居金陵,在地方亦算上是豪门大户,风净痕作为世家子弟,自是多辗转于外交场合。沈疏却是不同,一介孤胆游侠,神龙见首不见尾,独来独往,识得他的人不多,名声便也略高些。江湖上将他的文才武功传的神乎其神,皆道他温尔文质,风度怡然,哪知却是这般的绿林草莽之相。
沈疏微微一笑:“江湖谬传,不足为信。”将点心向他一让。
风净痕点首为谢,挽住衣袖夹起一片,轻咬一口,放在玉盘中。沈疏冷眼看着,只觉说不出的优雅舒适,而今算是信这江南风家,名声不虚。
待口中点心咽下,风净痕又呷酒作漱,方又道:“方才在下见沈大侠所望,可是墙上那幅《临溪落叶图》?在下于这酒楼流连数日,所见多有名画真迹,然这幅图景似是无甚特别之处,不知沈大侠为何独睐此图?”
沈疏一怔,口气仍是若即若离的疏淡:“临溪落叶,不过是应此时之境罢了。我自二十岁离开塞北,第一次在江南有树落叶如此之多。”眼瞟向窗外的那树。这十多年来在江南流连,不由生倦,只觉这江南的温柔乡消磨豪侠之气。小桥屋檐,不若塞北开阔的旷野,容得人一生纵啸。
只听风净痕笑道:“那树似是得了什么病,在下初时亦是惊讶,闻说往年并不如此。”见沈疏垂眸不语,又道:“方才在下亦见沈大侠摇头默叹,可是这画哪里不对么?”
“那倒不是。”沈疏复向那图一望,“只是画上所题诗句太也小家子气,令人不够痛畅。”
风净痕转首端看半晌,浅笑:“确是凄凉了些。依沈大侠来看。题些什么好呢?”
沈疏知他意欲借此机会试探自己的才情,素知风家风雅,一时也起了好胜之心,想与风家世子试试才情高低。略一思索,便道:“扫尽浮云风不定,如何?”只言一半,便这般望向对面之人。
“扫尽浮云风不定。”风净痕低低重复道,又微一沉吟,赞道,“沈大侠果然疏朗,在下不才,斗胆再添一句——欲挽长江洗清秋。”
沈疏正转动把玩着手中的琉璃酒杯,闻言手上略缓,把眼定定看着风净痕:“风公子志向不小。而今与我这外人道出,不怕我对你不利么?”
风净痕淡静地笑着:“当此乱世,群雄逐鹿,我风家早便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沈大侠是难得的人才,令在下一见如故,颇为心折,不知沈大侠可肯助在下一臂之力,共图富贵?大侠是磊落君子,在下相信,即是不应亦不会对在下不利。”
“风家果有此志,楚越区区之地等闲而已,自是要逐鹿中原,一洗清秋。愿你们功业得成。”沈疏静静将风净痕之言听罢,将琉璃杯置在桌上,然而话锋一转道,“至于我,并无那心性,这几日便欲回转塞北,疏狂一世,也自罢了。”
二人志向不尽相同,因而初时沈疏只是淡淡的。许是有缘,而后论及文艺武学,却是愈谈愈欢,直至夜深酒楼打烊,二人仍是意犹未尽。风净痕道:“你我惺惺相惜,倾盖如故。沈大侠若无下榻之处,不若到在下别邸一宿,也好联床夜话,秉烛而谈。”
因与风净痕投缘,沈疏又在江南盘桓了几日,二人日日联酒谈话,风净痕外貌儒雅文弱,对武功江湖与天下大势却是了如指掌,颇有指点江山之风。沈疏亦是深有奇才,不仅熟识武学兵法,亦懂得奇门遁甲之术。二人愈谈愈将对方引为知己。风净痕又数邀沈疏与他共赴金陵举事,沈疏归乡心切,均以性子不喜束缚为由婉拒。二人不忍别离,又于江南游玩数日,待风净痕之父催他回转,沈疏才准备回往塞北。
临别前日正是中秋,风净痕在别邸后院中摆了一张八仙桌,与沈疏把酒赏月。
月光流转,清朗皎洁。酒盏莹莹,似是盛着满盏的月色。沈疏酒入豪肠,心扉大开,抽出身边龙吟剑,于月下起舞。剑身如水,反射出一片寒光。沈疏蓦地一声长啸,左手食指于剑身上一弹,剑作龙吟。作了一个掠势,剑锋缓缓展开。手腕陡振,一套剑法霍然起势,剑影翻飞,如繁星匝地,搅乱满院的月光。动作开阖疏朗,一时如青山凝稳,一时如怒涛奔涌,披着如霜月色,只看得风净痕不住叫好。各家剑法均以轻灵见长,而龙吟剑于沈疏手中却尽显刚稳沉健,劲风扫过院中树木,未见枝摇,叶却直直坠落。
蓦地沈疏又是一声长啸,长剑对月掷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长虹贯月后,如流星坠地,远远地直没至柄。风净痕击掌赞道:“好剑,好剑法!沈大侠内力超凡,使起剑来果是雷霆震怒,江海凝波。”
沈疏道:“什么大侠在下的,听着叫人生分,如此良夜,清风朗月为证,不若你我结为兄弟如何?”
风净痕欣然赞同,叙了齿轮,沈疏长风净痕五岁。二人对月拜了几拜,又各将一杯清酒洒在地面。风净痕重将各自金樽满上,一饮而尽。又跃到庭中,轻轻一勾,将宝剑取出。袍袖飘飞,似欲凌风乘月而去,双脚一旋,稳稳落在沈疏身前,将宝剑递上。
沈疏并不接剑,只是将酒斟满,一面感慨道:“往日中秋我只是顾影独酌,一向独来独往得惯了。只有这龙吟剑伴着我,从未离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宝剑便赠予贤弟,权作我这当大哥的一份心意。”
风净痕却之不恭只得收了,又着人取了其他宝剑给沈疏配上方罢。
一年后。风家自于金陵起事已有不小起色,已将江南全部收入大楚版图,与林佑安的苏州大周政权划江对峙,相持不下。
风家发动长江之战,欲强渡过江。风家亲兵虽惯于水上征战,只是料敌不足,起了轻敌之心,一时不察,中了诡计,受制于人,被周军困在长江中心。
眼看着包围圈越缩越小,风净痕所带亲兵死伤无数,周军却越战越勇。冷不防两箭并排射来,直取风净痕双眼。风净痕此时正独战三名周军将领,腾不出手来,一咬牙,龙吟剑狂舞直欲与敌人同归于尽。却听叮叮两声,不知从何处飞来两枚透骨钉,将冷箭打落。
敌将大惊,透骨钉比箭小的多,竟能将箭打落,这人的手劲不容小觑。风净痕只觉耳边萦绕着沈疏的声音“贤弟莫慌,愚兄来也。快指挥亲兵自东北冲出。”知是沈疏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在指点他,心下一喜,又得沈疏暗器之助,结果了两个,松缓了许多。不暇细想,自怀中取出一面令旗,向东北方向招摇。又回身一剑刺死第三名敌军将领,带着亲兵向东北撤去。
沈疏已一路斩敌开路等在那里。风净痕下令按沈疏所言的迂回之法回营,便自入舱内与沈疏叙话,相见之下自是大喜。风净痕道:“今日一战亏了大哥相助,只是大哥如何会在这里?”
沈疏道:“中秋将至,忆起去岁与贤弟的共聚,甚是思念,又闻说贤弟正与苏州林家对峙,便来一探,所幸来得尚及时。”
风净痕闻言叹道:“小弟不才,近日屡战屡败。若不是大哥惦念着,怕是再无相见之日了。”
沈疏沉吟半晌,方道:“贤弟若不弃,我便留于大楚营中助你,也好多一份力。”
风净痕便是要他这一句话:“大哥肯帮,自是最好不过了。小弟在此谢过了。”便要下拜,沈疏忙扶住:“你我兄弟,何必客气。”
风净痕带沈疏回营,引荐给父亲风玦。风玦讶于沈疏的文才武功,有此等人相助,自也是喜不自胜。
沈疏于兵法阵法无一不精,对攻下城池亦整治有方。不久,楚军便打过长江,两年之后,风家便一统天下。风玦登基称帝,定都金陵,国号大楚,立风净痕为太子,沈疏为定国王。沈疏不受欲辞,念及天下方定,便又留在朝中。
沈疏贵为王爷,又是太子的结义兄长,朝中自是争相逢迎。且他虽长相粗豪,为人却是疏朗中蕴有礼数,朝中的正直之士也乐与他结交。初时风净痕时时微服出宫与他把酒叙话,日子久了,来得次数也渐渐少了。沈疏知他事忙,也不以为意。
然沈疏终是不惯于仕途之事,待天下稍定,便欲辞官,重自浪迹江湖。风玦虽是不愿,仍是准了。
当夜风玦将风净痕召至御书房。
“明日沈疏便欲回转塞北了。”风玦翻动着沈疏的奏折,头也不抬,话锋忽地一转,“你这一年来在这朝野上下历练得如何了?”
风净痕不知如何答话,只是唯唯应着。
“天下得之不易,守之更不易。”风玦将奏折一扔,“为君者,要有杀伐之决断,不为私情所扰,不为眼前之利所惑。静则波定风平,动则江海扬澜。眼下便有一件事可试出你是否适合做着天下之主。”
风净痕心中一动,仍是恭敬地听着。
“沈疏这人实是罕见之奇才。治国安邦之道,攻城野战之术,奇门八卦之法,他无不精通。若是能久为我所用,怎愁天下不定,四海不安。可惜……他却要走。太子,你说该如何是好?”
这最后一句语气甚是严厉,风净痕一凛,一咬牙道:“依儿臣愚见,该将其软禁起来。”偷眼瞧了瞧父皇的神色,见他若有所思,续道,“如今天下初定,塞北却是不宁,若是放他回了塞北,恐会埋下祸端。但若杀了他,恐令天下寒心。”
风玦长叹一声:“本以为这些年来对你施行冷血教育,你该有所长进。你还是太重情啊,早晚会毁在这妇人之仁上。你可知沈疏虽自小受着我们汉族的教育,却并不是汉人,骨子里流的就不是我们汉人的血。今日若不斩草除根,以他之力,若是不慎让他逃出,怕是他会毁了我们辛辛苦苦经营的大楚。”
“沈疏他不是汉人?”风净痕甚是惊异。沈疏与风净痕都是并不在意胡汉之分的人,沈疏也就没有告诉风净痕此事,倒不是他有意隐瞒。而今通过风玦之口说出,却教风净痕不得不心生怀疑。
风玦见他动摇,点首道:“痕儿你记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日你去为他送行,亲手杀了他。若是你有一丝犹疑不忍,也不必回来见我了。”说罢,龙袖一拂起驾往后宫去了。
月下,风净痕静静立着,宛若一尊雕像。
沈疏离开的日子正是中秋。因沈疏素来甚得爱戴,夹道送行者不可计数,直是万人空巷。风净痕一路郁郁寡欢,沈疏只道他是不忍离别,反过来安慰他。
出了京城,便只剩了风净痕与沈疏二人并肩而行。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况如今你贵为太子,还是莫要远离京城的好。”沈疏停住,转身关切地道。
风净痕犹未下定决心,道:“且再走一程。今日一别,不知何时能够再见。”
秋风掠过,丝丝凉意沁骨。
沈疏亦是感慨唏嘘不已,便同风净痕又行了一段:“太子殿下莫要再送了,有缘自是能再相会,我就此别去。”又对风净痕叮嘱一番,才转身离去。
风净痕望着他的背影,父皇的话又鼓荡在耳侧“若是你有一丝犹疑不忍,也不必回来见我了”。痛苦地闭眼,龙吟剑呼啸着掷出。
沈疏听见声音,回转过身,龙吟剑挟风而至,因风净痕终是不忍,掷出时手腕微颤,龙吟剑并未伤到心口,只没入左肋。他不可置信地望着风净痕:“你……”
风净痕睁眼,见沈疏所伤并非要害,紧缩的心也稍稍放松,缓缓道:“父皇令我杀你,我不得不从。我不再伤你,但你……生死由命。”
残阳斜斜地挂在天边,凄婉苍凉。
沈疏蓦地明白,气极反笑,一用力将龙吟拔出,鲜血喷涌:“呵,好,好一个无情无义的净痕太子。你且放心,我定会好好活着,只要你们父子不再来招我,我自在塞北过我的日子,永不相犯。我们,便算作是从未相识过,还给你的剑。”沈疏离开时将风玦所赐之物皆封在府中,只带了风净痕当年所赠宝剑,此刻连龙吟一并掷在地上。决然曳着步子艰难离去。
晚日跃入地下,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
“世事沧桑,白发如新……”一滴泪自风净痕眼中缓缓滑落。
这一夜,金陵城郊城内的叶尽皆调坠,洗尽清秋。
酒醒天寒 遥记兰台月落
小炉候火 不信陌路白首
相约蓬山 闻说结婆娑花果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喵呜~
:喵呜~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465-4 届
:风云465-4 届













 Post By:2024/4/15 0:25: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15 0:25:4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白衣沽酒
:白衣沽酒
 :泛小酸
:泛小酸
 :绮罗生
:绮罗生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2 届
:风云0-2 届







































 Post By:2024/4/19 22:48: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19 22:48:0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云深雪杳
:云深雪杳
 :以雪为名
:以雪为名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3 届
:风云0-3 届


 Post By:2024/4/20 22:15:5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20 22:15:5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云深雪杳
:云深雪杳
 :以雪为名
:以雪为名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3 届
:风云0-3 届


 Post By:2024/4/20 22:16:1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20 22:16:1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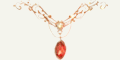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4/20 23:08:0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20 23:08:0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花五刀
:花五刀
 :花生
:花生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5/27 20:01: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5/27 20:01:16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