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天空上,摇摇欲坠,却威力不减,凡是被阳光照射到的地方,无不燥热难耐。树木、花草、禾苗都耷拉着脑袋,恨不得跟鸡犬一样,能长腿逃到地球的背面。昆虫躲在树荫里,还要防备突然飞过来乘凉的鸟雀,张皇四顾,不敢出声。
春生手里提着一双鞋,光脚奔走在乡间小路上,脚上全是厚厚的茧子,虽然石子路又烫又硌脚,他也舍不得穿上鞋。身上汗衫已经薄透得近乎透明,却干干净净。春生一边用搭在脖子上已经磨损得没有毛的毛巾擦着汗,一边抬头看看天空,西边是火热的太阳,而月亮已然爬上了东面的树梢,淡淡的,圆圆的。
离家最近的药店在十里地外的场镇上,两年前,撤乡并镇,这个场镇的行政区划已经归属到另一个乡镇,乡政FU以及乡卫生院都跟着撤并到了另一个乡镇。少了到政FU办事和到卫生院就医的人,场镇就慢慢萧条起来。方圆十几里也还有百十来号人因为各种原因故土难离,场镇上就还保留着赶场日,还有一个小小的超市和药店。药店老板是药剂师,也是赤脚医生,随性开门营业,有时可能在场镇上跟街坊打麻将聊天,有时可能背着药箱走乡串户给人看看小毛小病。去药店能不能买到药,全凭运气。
春生爹昨晚开始有点不对劲。平时春生房前屋后田间地里忙着,春生爹寸步不离地跟着。有时候也能拿一把小锄头有样学样跟着春生翻地,把庄稼当成田间野草给拔了。这种时候,春生就会给他爹用草编一个小玩意儿让他独自坐田坎上玩,就跟他爹小时候哄他一样。春生做饭的时候,他爹就老老实实坐在灶前烧火,有时候会塞一灶孔的柴火,闷一屋子的浓烟。可昨晚,春生爹一直蔫蔫的,坐在门槛上耷拉着脑袋,春生以为他下午在田里追蛾子蟋蟀跑累了。等到做好饭,叫他吃饭也不理,春生端着晚喂了两口,他就不张嘴了,春生这才注意到他爹两颊坨红,一摸额头,已经滚烫。春生赶忙去院外田边上掐了两棵苦蒿,熬了浓浓一碗苦蒿水哄他爹喝下。苦蒿水退烧,还是春生家里祖传下来的偏方,还从来没失效过。偏偏这次,春生爹喝了,先是安安静静睡了,半夜摸着好像高烧退了,早上起来也正常进食,只是一直没什么精神,也不跟人走了,坐在小板凳上发呆。午饭后,春生爹不仅又浑身滚烫,还上吐下泻。
未完……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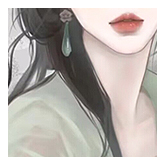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7-0 届
:风云527-0 届

 Post By:2024/5/24 21:33:17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4/5/24 21:33:17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