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青苔斑驳的石板路,一滴,两滴,数雨珠。
复古雕纹的菱形窗格外,一斜,两斜,飘雨丝。
是绣娘遗落的银线吧,是乌篷船摇晃的倒影里,织就的新衫吧。
瓦当排列如琴键,雨滴匝落成指尖。它们叩击黛色陶片,在空蒙烟雾里敲出清越的调子。
我站在客栈二层的木栏杆前,看雨水在飞檐翘角间作画。檐角铜铃铛晃啊晃的,风起又涟漪。
雨帘层层荡开,水乡,你何故躲进青灰色的纱帐里,你也羞怯了吗?
巷口卖茉莉的阿婆,打着油纸伞,伞上的水珠一颗颗坠落,在青石板上,绽起莲花。
她掀起蓝印花布盖子,白瓷碗里的花串沾了雨,倒像是新折的带着露。
阿婆背后的木廊柱,雨珠从檐角滚落,在茶褐色的木廊柱上蜿蜒出曲折的溪流。
雪山
我向北去,在雪落满山时住进半山腰的木屋。
屋檐上垂下的冰棱像水晶帘,风过时叮咚作响,或碎落,或残缺。
那一片雪花落在睫毛上时,我屏住了呼吸,山也屏住了呼吸。
山里的枯枝,裹上糖霜,松鼠的脚印,开成梅花。
而远山呢,正被云絮般的雪雾,重新勾勒。
何时成画,我却不知。
晨起,推窗。
雪粒被风卷成漩涡。
惊见山雀掠过,刹那间,翅尖扫落雪粉,便在阳光下化作尘光。
最难忘那个暮色猩红的黄昏,我踩着及膝的积雪往高处走,听见冰层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雪音。
我高喊一声,松针便托着雪团簌簌坠落,而我的掌心,正接住几片雪花,它们的凉意冲进我的血脉里。
成为
那永恒的颤栗。
沙漠
我向西行,黄沙成形,漫过天际时驼铃摇着落日。
风在沙丘脊线上刻下的波纹,漩涡,比江南水巷更曲折缠绵。
我躺在沙脊看流云,沙粒钻进衣褶的褶皱里,一粒一粒。
大漠,你莫不是在与我诉说情话?正午的沙海,像被熔炼的金子,黄昏时又似沉年的宣纸。
起起伏伏里,晕染着赭石与藤黄。
那天,遇见骆驼群,它们踏起的沙雾又像极了江南里的雨雾,夕阳穿透时,恍若佛经里描述的琉璃光。
你见过琉璃光吗?你见过北极光吗?我跟着它们,行走了一段,那些沙粒跑进靴筒里唱起歌来。
最是荒凉处,亦有私语时。
万物
如果星辰坠落沙海,风会不会搬运整个宇宙的尘埃去打捞。
当烛火在窗纸上摇曳,你能猜得到屋外是,雨水、雪粒,还是黄沙?
记忆匣里打开的珍珠,一颗,一忆。
茶汤蒸腾的热气中,不同的水声在茶器里流淌,雨滴叩击陶罐的叮咚,叮当。雪水渗入山岩
的淙淙,潺潺。以及沙粒从指缝滑落的簌簌,沙沙。
我路过的应当不是江南、山峦与大漠。而是清雨、融雪、尘沙写给异乡异客的情诗。
我所谓的漂泊,也不过是从天地间,汲取爱的能力。
爱青砖黛瓦下垂落的雨帘,爱枝头雀鸟颤动的雪霰,爱细长指缝中漏过的细沙。
万物皆在行走,河水不可能倒流,最美的,一定是曾路过的,
那时那刻你爱的,
也爱你的段段光阴。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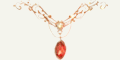
 :许诺
:许诺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46-0 届
:风云546-0 届








 Post By:2025/2/24 21:26:37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25/2/24 21:26:37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