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碎片》
一 八百里望尽,是秦川
我走过八百里秦川,总想有一天,把枯骨撒落山间。
半坡遗址中,把陶罐打碎的女子,踩着夕阳走了。
多年后,在潼关的沙尘里,第一次听到,陶瓷彩绘带着三千人,唱着三千年前,寻找那位便嬛的女子。
渭河流域的无数次翻滚出来的塬,链接着黄土的黄,雄浑,辽敻。
农耕文明像孕妇一样哺乳着子女,妊娠纹的褶皱里,满是生命的棽俪。
游牧民族在这里,把渭河的水和天上的月,装进口袋。于是,关中千里沃野,在周人的怊怊悒郁中,留下山峰,如伤口一道道的冷厉,悄怆。
于是,白马归来,岐山脚下的长风,一遍遍地裹挟着泬寥的月光。
陇南油菜,峬峭妖娆,但仍然打动不了黄土高原,被黄沙淹没的凌厉与孤傲。
而谁会在塞外,见大漠落日,高举狼烟,呼唤八百年周朝,再度来袭?
此时,秦国的女子,青色长袍,手握羌笛,在崤山,或陇蜀,把《道德经》,念了八百年,念到枯草衰黄,渭河成沙。
三千年里,三千年相思,三千年不见。
陶埙吹着最初的姿态,朴拙而细腻。诸侯的酒杯与鲜血交融,在八百里秦川,百家争鸣,鹿死谁手?七十二个帝王的怒吼与泪水,在渭河的浪涛里,一截分裂,一截重叠。万里河山和将军的夜,都在酒里,沸腾,鲜红如血。
关中,关外。
横断山脉的风吹来,秦川人家的小院里。
高粱熟了,麦粒饱满。
二 一壶老酒吼秦腔
撕开所有人的皮与魂,秦腔就在那里怒吼。
秦皇汉武,苏武牧羊,一声断了一声长。
谁家的媳妇在田野里一泡尿,阳刚的男子一头扎进地里,怒吼的秦腔带着金属的声音,麦苗的腹部,藏满了春色。
牛羊咀嚼着夕阳,壮士解甲,女人煮酒。
孤独的山川和浅薄的诗歌,在青铜文化和周礼的老腔里,煮了渭城的雨。
关中平原上,仰天大诵一遍《禹贡》,粟米一碗,牲畜满山。酒肆的心思,在长安的街道里,望去都是牡丹花。
这一声吼啊,唱到《周仁回府》里,早已把奉承东碎尸万段。
这一声吼啊,在《下河东》里,早已旌旗招展,随着呼延兄妹挂帅出征。
这一声吼啊,躲在《藏舟》中,看那渔家女子,在江边长歌当哭。
这一声吼啊,在关中沃野,在渭水流域,在汉阳的青山绿水之中,仰文,止武,生息,歌舞,还有和深爱的女子走进黑暗中的打谷场,走进月光遮盖的角落。
声泪俱下的调子里,杨家将血战沙场,王宝钏苦守寒窑,多少公子小姐,爱断肠,哭凄凉,到头来,都是月亮瘦了,残了夕阳。
古老的青砖,爬满了青苔;斑驳的老瓦,湿透了渭城的雨。
多少年后,还能否在黄土地上一声吼:贤愚忠佞,悲欢离合,都是一壶老酒。
你看陇上的小院外,黄花开了。
青花瓷的碗里,黄河的水,缅邈,又粗犷。
三 粉墨登台,皆是皮影戏
市井口里,火和喝酒声,还在揣摩着傀儡的喘息。
二胡,唢呐,或竹笛,把女子的浅笑,羞赧,流眄泼到影子里,或许可以看到春天的蝴蝶、燕子、还有白兰花,卖力地摇动着诱惑的句子。
酒鬼还没醒,绣花婆娘已在镜前,梳妆着浓妆艳抹的一天。
舞女的衣衫乱了,巫婆的挂签断了,书生的扇子只剩下骨架,贵妇人的腰又臃肿了。古铜色的老男人扮着壮丁,挥剑的将军满目充血,孟姜女跪倒的姿势,让长城的砖战战兢兢。
而那件青色的长袍,如冰雪,散落在门外。门外的海棠,已经枯萎。
楚人之狙不甘心为奴,郢人斤斧削鼻粉而不伤;布影下沙,挥酒如雪;虞姬的火焰,弄玉作凤鸣,都在秋风和落叶里,滚滚入尘。
于是,躲在黑匣子里的人们,安安静静地愤怒,诙谐聒噪里哀伤,随影入戏,却又逃不了戏里人生。
多少年,多少人,来不及掂量亲情和国土,来不及深爱和厮守,来不及把春天的种子,种在秋天的田野,就在第一片雪花来临时,面朝河山,眼含热泪,孤寂站立。
肝肠寸断,又作奈何?
或许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把故事挂在皮上、纸上,然后和时光厮守。
好好厮守。
四 沉默的,都是青铜
青铜,以某一种情感定义,成为文化。
经历火与水千年的煅烧和洗涤,从厚重的泥土里来到这个闹市,见繁华灯火,人流入海。看见三千年前的太阳在愤怒或咆哮,而听不见氏族社会女人的矜持,在甲骨文上,与原始的欲望挣扎。
而青铜器没有,还是古铜色,还透着泥土和火的芬芳。
虽然在青色的骨骼上,看不到泥土,但能看到粗暴的手和暧昧的抚摸,张牙着贪婪,填满了油头粉面的报告:我们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蠢蠢欲动的目光里,肮脏的,卑鄙的,都停留在你身上。圣洁不见,庄严不见,被那污浊的手,翻开,敲打和展览。
谁在你面前讴歌,谁就是铜铸上的囚徒。
殷墟的记忆,应该是内敛的,这记忆里是祭奠,酒,是抹不去的庄严。
而你看到太阳的炙热和月光的清冷之后,那个胖子、瘦子,即使像被下了巫蛊,也不会露出半点惶恐和彷徨。
在四面高墙之下,看到殷墟的血在你身上流淌,看到文臣武将,看到青蓝色的火焰燃烧着一个民族的图腾,看到春花烂漫的原野,秋草苍黄的庄园。
就是不见了,那陶铸的窑子和匠人,弯曲着古铜色的臂膀,唱着调子。
看见的,也应该能看见,那老去的唏嘘和斑驳的记忆。
和泥土的声音一样,沉默于地下,是最好的酒和星辰大海。
而谁能想到,历史一边堕落一边张狂,你只能惊惶地打量着充血的目光,惊恐地躲避污浊之手,我们或许会发现:
先贤死去,肖鼠活着。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公主发财
:公主发财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0 届
:风云528-0 届








 Post By:2024/6/9 21:23: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23:23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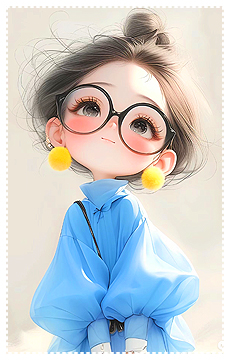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魏源SM
:魏源SM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5 届
:风云528-5 届
 Post By:2024/6/9 21:24:4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24:44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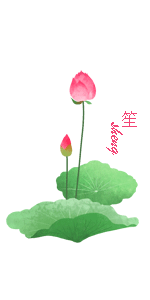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魏朴SM
:魏朴SM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6 届
:风云528-6 届









 Post By:2024/6/9 21:26:0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26:0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7 届
:风云528-7 届
 Post By:2024/6/9 21:31:3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31:3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5 届
:风云528-5 届
 Post By:2024/6/9 21:32: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32:2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5 届
:风云528-5 届
 Post By:2024/6/9 21:33:4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33:4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5 届
:风云528-5 届
 Post By:2024/6/9 21:34:2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34:2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玄族郡主
:玄族郡主
 :曜仪SM
:曜仪SM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1 届
:风云528-1 届
 Post By:2024/6/9 21:49:2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49:2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玄族郡主
:玄族郡主
 :曜仪SM
:曜仪SM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1 届
:风云528-1 届
 Post By:2024/6/9 21:49:5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9 21:49:5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7 届
:风云528-7 届






 Post By:2024/6/10 15:28:3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0 15:28:3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8-7 届
:风云528-7 届






 Post By:2024/6/10 15:28:5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6/10 15:28:52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