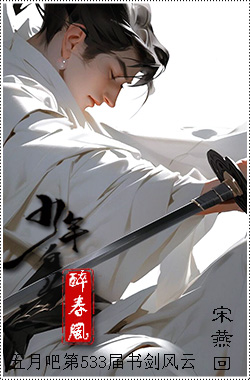明明已经有了秋意,却燥热的不行。说好的雨,一滴也没有下,路面干巴巴,只有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寻找着食物。
小时候的这时间,我应该是在外婆家的。
外婆家是在山里的,上学时,每到暑假我就会去那里度假,那时实在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外婆才会承担起起看孩子的重任,爸妈则是在家忙里忙外,赚钱养家。
我呢,乐得其闲,喜欢的还是山沟沟里在燥热的空气中,透出的一丝凉意,我会在河边的大榕树下,摆上小桌子,听着流水和远处鸭子嬉戏的声音,水牛不时“哞”的一声,会牵走我的思绪,当我安静的把一天的暑假作业完成,而后,就会在河边捡一些扁扁的、薄薄的鹅卵石,打起水漂,运气好时,一串涟漪能散到对岸。
有伙伴那就更好了,我也会壮着胆子,和他们一起爬到树上,虽然颤颤巍巍,但总能在他们在上面玩够的时候,慢慢爬到他们的位置,然后擦擦汗,跟着他们开始慢慢往回爬,在外婆喊我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总能安全的抵达地面,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非要让自己做自己那么恐惧的事情,也许童年的快乐就是这样,有着欢笑和让自己无所谓的未知吧。
再后来,树我是不爬了,因为胆子实在是小,很好奇为什么小伙伴会那么迅速的在粗壮的树枝上,上蹿下跳,无比快乐。树上还是阴凉好多嘛,不过湿漉漉的枝干,也确实危险,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恐高的,只是那时候不知道而已。
热衷的另一件事儿,就是在河里洗澡,那时候学校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安全这么重视,三天两头的在群里通知家长注意防溺水,基本上放假了,学生就撒丫子跑了,虽然学校没有怎么关注这些,但外婆是个很谨慎的人,是坚决禁止我下河洗澡的,河湾子那里有一片被河流冲刷的浅滩,孩子们都在那里游泳嬉戏,但再往里一点就深深浅浅,是连大人都不一定能探到河底的深度,最要命的是,曾经有村里的小孩子在那里独自戏水,最终人捞上来的时候,已经直挺挺了。
外婆怕,我也怕,但我禁不住河水清凉的诱惑,在外婆不注意的时候,我会小心的躺在浅滩上,让河水浸过自己的胸脯,看着小鱼虾在身边游来游去,甭提多惬意。舒爽够了,我会早点从水里出来,晾干衣物,以为这样外婆就不能发现,但每次小心的回家时,都会被外婆看出端倪,然后温暖又严厉的警告我一番,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每次去河里玩,外婆都会远远的看着,如果伙伴多,她就踏实一点,我呢,虽然是个无知无畏的年龄,但总会在有很多伙伴的时候才会下河玩耍,给外婆添乱,但也让她放心。
从来没挨过外婆的打,即便下河玩耍回来后,也是一桌子香喷喷的饭菜等着我,外婆就这样一直陪我度过了这个童年。
再后来,外婆没了,在葬礼上,我痛哭失声,从此,我少了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人。之后的每年,我都会去给她扫墓,但再也不会去曾经游泳的那片浅滩。
宋燕回弑杀:
少了一个人,空了一座城。
繁华笙歌不再,
入眼的荒芜一如不远处枯井边枯树枝桠撕扯住的破风筝,
一切似鬼蜮,昏黄的月掌上了漆黑的灯。
少了一个人,空了一座城。
炽热的炎日被沙尘遮掩得朦朦,
不再有商旅途过,
驼铃悠悠散入旧时遗落的梦。
少了一个人,空了一座城。
城中过往点滴被沙土尘封,
在隔绝了光源的亘古,
那位公主是否被绑缚在冰冷的刑柱上、泪滴随风?
少了一个人,空了一座城。
城墙上累累斑驳的坑洞,
是否是公主的瞳?
千年的岁月匆匆,
你缄口默然,不动如钟。
在这被遗忘的时空,
承受着交替的炎热与冰冷。
寻城、寻梦?
在醺黄的视野里,
我微眯双眼,求索你的影踪。
空城的影迹渐渐浮现,
我看见、枯井边枯树的枝桠撕扯着的风筝,
一如当年淹没楼兰的那场浩劫中、
落泪的你、身穿霓裳、那抹凄美的胭脂红。
一个人行走在林芝
林芝,一个安逸而浪漫的地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切美好的事物构建出的一块世外桃源。这里的人们朴实而祥和,在这块土地上悠闲浪漫的生活着,对着山水静美,固守一份安然。
春天,山上的桃花烧成一团耀眼的红色,焚烧出大片胭脂香味,飞鸟轻盈的穿飞林中屋角,它们在欢笑,生活多美好。他们在歌唱,蓝天多明净!
夏天,这里没有其他亚热带区域的酷热。天空像是最调皮的孩子,永远猜不透他什么时候会哭泣、什么时候破涕为笑。而在晴朗的时候,天空中随意涂抹着的云彩,也像顽童画出的最烂漫的图画,或是点染,或是涂抹,或是淡雅,或是喷涌。天空一角时隐时现的彩虹,就是这个季节最美丽的符号。
林芝的秋天总是格外的短暂,当树上的叶子镶上了一围金色,到它猝不及防的就坠落于泥土——冬天到了,山上和山下仿佛是两个世界。远远望去雾茫茫的山顶吹撒着雪花,山下还是一片慵懒的晴朗天气。雪花飘不到人间,属于北方冬天的寒冷朔气,近在咫尺,却又只能想象。
一个人行走在林芝,会被这里的气氛感染,闲适的散着步,即使无酒无花,也能咀嚼到千年前五柳三径的一味安逸。
林芝,清醒在梦境。林芝,沉醉在天明。
窗外的天气变得阴云密布,狂风吹起道路上的尘土,迷得路上的行人微闭了眼睛,很快,预示着一场暴雨,很快就要来了。
又是阴天。天空被大块大块的云团遮蔽得严严实实,这些看起来丝丝缕缕有梦幻感的生物。带着密密匝匝的吸盘,触在原本干净的蓝天上,攫取着、狞动着。却发现天空早就是干涸的了,没有一丝血液,一滴泪水。
站在阳台上,打开后窗,涌进了一大片风,风意冰凉,我却只觉着清爽。四围都是山,他们似乎像我的眼神一样,挣扎奔跑着,却逃不出这个狭小的囚笼。我又想到了远行——和前几天一样,麻木穿行于汽车和火车之间奔波,眼中流入的风景,同一瞬间,从眼角流出。
从S城,到L城,我坐了十个小时的汽车。一路的风景现在想来大部分都麻木了。唯一记下的,是天地中奔跑着的灰色,以及被一簇簇灰色撕扯到欲支离破碎,挣扎扭曲的红柳。那是怎样的一种姿态,风烛残年的老妪,伸出手,像是攫取、像是索求、像是推拒。驳杂羸弱的枝干还未着上一丝绿色——也许,它们已经在挣扎中死亡了吧。死亡的事物,才会这样枯槁,失却了灵魂中一切可以表示温润的色彩。客车驶过,尘土带起一阵不耐烦的风。我想,视线以外,它们仍在荒芜中,缓缓战栗。
晚上九点下了车,拖着重重的箱子,装着满满的疲惫,朝单位走去。大门没有关,像是长得极大的嘴,呵着大口大口的寒气。他虚伪的打着招呼:“你又回来了啊……”
“是啊,我又回来了。”
单位院子很大,对于将要到来的春天,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没有一点的准备,光秃秃的枝杈,树下堆积着去年的叶子。脚下随时会出现一块块落叶,踩上去“咯吱”一声。这些没有了一丝水分的叶子,在月光下隐约呈现出的是一种扭曲的轮廓,像是缩成一团的昆虫,我尽量避开他们,不去打扰已死之人的宁静。
回到住处,有的同事已经到了。楼上星星点点亮着几户灯光,我径直上楼,回到我的房间。房间里很凌乱,我不由想到那时近乎逃离的心态,对于这里的一切都想就此甩开,不管不顾。可是,我是逃不掉的,还是这个狭小逼仄的房间,昏暗的灯光嘲弄的看着我,狼狈,麻木地收拾这里的一片狼藉。
收拾就绪,躺在了床上,熄灭了灯。我睁着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黑色的空气,空气有点微凉,我扯了半截被子,盖住身体。渐渐感觉到,黑色越来越浓重,又开始慢慢透露出微光,世界又重新光明了,我的身体慢慢漂浮起来,从围山的罅隙中飞了出去。还是熟悉的山山水水,从瞳孔流入了心底。路两侧的红柳居然也舒展开来,青绿色的枝条萌发出了卷俏调皮的叶子,我的身前抱着千里江南,身后是遗忘的万水千山。
脸上微凉,我回过神来。居然下雨了,我关上阳台窗户,怔怔的走进屋里坐在床上。那晚那个该死的梦,让我连着几天都未缓过神来。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也许,这个梦里又会逃离,也许,这个梦醒我会放弃。闭上了眼睛,灵魂游走,开始试图沉溺于过去的某些痕迹。
虽然曾经有人说过,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过客,来来回回不过都是虚妄,但是如果不是过客就一定会回来的。可是现在你回来了,我却要离开了。对不起,我注定只能当你生命中的过客。珍重,再也不要见了。因为纵使明月不曾是两乡,我们也注定是要山水不相逢了的。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3 届
:风云533-3 届








 Post By:2024/8/26 13:15:2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3:15:2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3:27:2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3:27:2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3:40: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3:40:2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人世儒仙
:人世儒仙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6 届
:风云533-6 届
 Post By:2024/8/26 13:40:2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3:40:2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8 届
:风云533-8 届
 Post By:2024/8/26 13:49:5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3:49:5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人世儒仙
:人世儒仙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6 届
:风云533-6 届
 Post By:2024/8/26 13:56:3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3:56:3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6 届
:风云533-6 届
 Post By:2024/8/26 14:01:0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4:01:0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我的欢喜你懂得
:我的欢喜你懂得
 :莫衣SN
:莫衣SN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9 届
:风云533-9 届
 Post By:2024/8/26 14:37:0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4:37:0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3 届
:风云533-3 届








 Post By:2024/8/26 15:43:3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5:43:3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君玉SN
:君玉SN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8:35:1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35:15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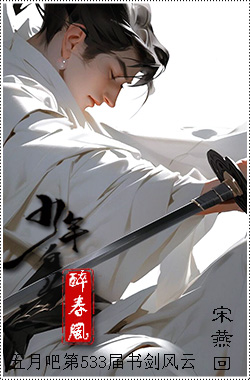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君玉SN
:君玉SN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8:37:1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37:12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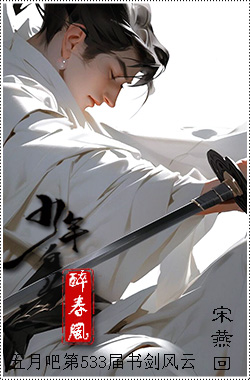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8:38: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38:2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君玉SN
:君玉SN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8:44:4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44:49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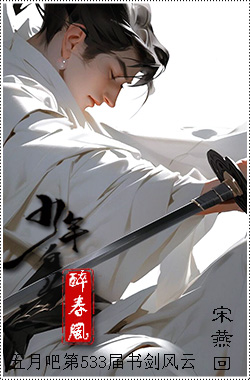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3 届
:风云533-3 届








 Post By:2024/8/26 18:54:1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54:1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君玉SN
:君玉SN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8:56: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56:19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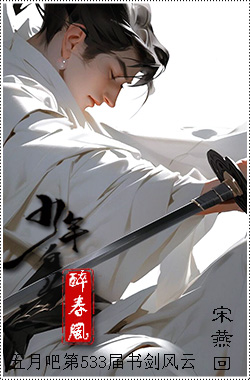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萧若瑾SN
:萧若瑾SN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3 届
:风云533-3 届
 Post By:2024/8/26 18:56: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56:2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君玉SN
:君玉SN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33-7 届
:风云533-7 届





 Post By:2024/8/26 18:58:4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8/26 18:58:43 [只看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