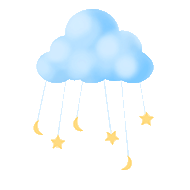自从全省各地开始出现静默、封控措施以后,母亲每天都要给我打至少一个电话。
渐渐地我开始还有些不耐烦起来。我想我这么大个人了,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工作生活了三年。
我有单位,有同事,有朋友,住处虽然是租的,但也是我合法拥有的独立私人空间。就算是我们这里也被封控了,我又能有什么事呢?
不过我知道母亲对我的牵挂。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所以我在和母亲通话的时候,还是尽力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尽力用平和的语气回复她那千篇一律重复的老调。
比如出门要记得得口罩啊,家里要记得备足退烧药啊,每天坚持喝连花清瘟啊,要尽量早睡不要熬夜好增强抵抗力啊……
母亲甚至连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忽然要被抓去方舱隔离”的事情都交待到了。她要我取点现钱在身上,还有收拾好一个背包,装好常备药品和换洗衣服……想了一想,又交待我千万不要忘了包里还要装上口罩和卫生纸。
因为她听说,方舱里除了发连花清瘟,好多地方连退烧药都没有。
我听得有点好笑。我在这城市工作生活了好几年。我有单位,有组织,有同事,有领导……
而母亲呢,除了我在这边安*定下来时和父亲一起来看过我一回,甚至连家乡的县城都没去过几次。
不过为了让她放心,在电话里她说什么,我都是敷衍着说好好。
事实证明母亲真的是闲操心了。直到全面解除风控,我也没有被抓去方舱隔离。
虽然我上班的公司所在的区域也曾被暂时停工过,我租住的小区中间也静默管理过。
封控和静默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混乱,但也不至于完全没法生活。
然而在全域解除疫情封控、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之后的第三天,我阳了。
高烧、咳嗽、全身乏力,喉咙疼得如同被一万斤碎玻璃渣一遍遍划过一样,连咽一口水都让我痛不欲生。
我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量过体温39度6,连爬起烧壶开水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试图通过手机求购退烧药,然而到处都是“断货”。
四周安静得可怕,我想我可能要死了吧。
忽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我艰难地抓起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是“妈妈”,那一瞬间我忽然泪如雨下。
母亲照例的一天一个电话啊……
当时我已经高烧得有点迷糊了吧,我不记得我和母亲在电话中都说了些什么。挂断电话之后,我再也坚持不住,沉沉昏睡过去。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母亲来了。我艰难地下床,迷迷糊糊地给她打开门,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起来。
母亲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安慰着我,象我小时候一样哄着我说:“不怕不怕,妈妈在呢……”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艰难地睁开眼,赫然发然母亲真的坐在我的床边,正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慈祥地看着我。
“妈……?”我惊喜地叫着她,却发现喉咙仍然疼痛得难受,几乎发不出声音。
原来我在电话里,给母亲说了自己“阳”了,高烧,已经几乎动弹不得,还买不来退烧药,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母亲当即就着急了。她什么都顾不得了,花高价包了一辆小车,直接赶了过来。
因为家里父亲也阳着,村子里退烧药还能买到,所以母亲来的时候,是带着各种药来的。
原来我先前的梦,并不是梦。母亲来到后叫门,我起来给她开门,都是真的。只不过我烧得迷糊了,记不真切,把这些当成梦境。
在母亲的照料下,两三天之后,我退烧了,喉咙疼痛也渐渐地恢复了好多。我知道我不会死了。
这天夜里,我真的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还是童年的模样。我在母亲的怀里撒着娇,笑着闹着。
而梦里的母亲好高大啊!她轻轻地抚摸着我,慈爱地看着我笑。她像山一样伟岸,为我挡着了所有的风和雨。她那慈祥的微笑,如同温暖的太阳一般光芒万丈。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26 20:30: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26 20:30:0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可可
:可可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26 20:35:0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26 20:35:0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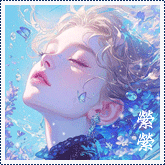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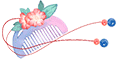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28 14:51: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28 14:51:21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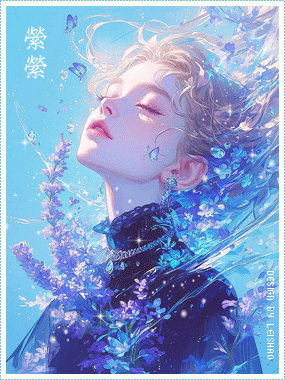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灯,等灯等登!
:灯,等灯等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28 19:56:3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28 19:56:32 [只看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