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叫来附近一位环卫工,废品拱手相送,让环卫工妥善处理。环卫工投桃报李,将路中间散落的泡沫碎屑等垃圾清理干净。
又冷又饿。我跟着师父重新回到串串店。毋庸置疑,我们的串串连锅底都找不着了。我问店长,店长也无奈:“你们跑出去那么久,再说了,你们也没付钱啊。”我好悔恨,为什么提前把串串一股脑扔进了锅里,现在连尸体都找不到了。说好请师父吃饭,绝无虚言。算了,再来一遍吧。一来一回一反一复,又少了三百。今天总共佘了六百,权当盘亏。
我和师父依旧临窗而坐,锅底尚未煮沸,我无聊地四下张望。
“来了,来了,来了。”
窗外,大爷骑着三轮车,大妈坐在车斗里从窗边经过,停在了环卫工面前。钱货两讫,三轮车重又装得满满当当,老两口一前一后,一骑一推。不多久,消失在视线中。
随后三天,我和师父时而坐在岗亭内,时而分站在四岔路口的对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除了极个别骑电瓶车不戴头盔的顽固分子被师父拦下口头教育外,城西路规矩得像是个老实孩子。我不知道师父那双神目电眼到底在搜寻着什么,反正我在等大爷大妈。我倒要看看大爷骑着破三轮载着大妈从师父面前经过时,师父该如何应对。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自己说的。
第一天,大爷骑车经过十字路口,没发现大妈。
第二天,如昨。
第三天,无影无踪。
有些费解,我问道:“师父,今天一整天没发现大爷大妈。您看到了吗”师父没说话,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的天啊,山无棱天地合,师父来请客。这水喝得诚惶诚恐,这得算盘盈了吧?师父没搭理我:“想什么呢,不是我买的。听同事说,中午一个骑三轮车大爷送过来的,两箱。”
第四天,第五天。直到第六天,我没忍住,我戳了戳师父:“师父,大爷呢?送完水怎么就见不着人影了?大妈也不见了。”师父点了点头,继续面无表情。我凑过去:“不会大妈摔那一下子摔出了什么问题吧。”
师父翻了个白眼:“没见过收破烂穷成这样还不耍秤的,挺老实一人。别瞎咒。回头照顾照顾生意吧。”
怎么照顾生意?师父借口找得好。师父让我搜罗了一堆废纸,比如往年学习笔记,还有支部里废旧报纸杂志。
找到赵大爷很简单。师父下班后在串串店对面等到了环卫工,电话号码环卫工那儿有。我和师父以卖废品为名登门送货。好在赵大爷家住得真不远,与城西路岗亭相隔三百米。
那是一间披厦,比咱们的岗亭稍微大些。位于一片矮楼角落,四岔路口靠北。披厦破烂程度堪比三轮车,卷帘门同屋内屋外众多废品融为一体,乍一看还以为卷帘门也是收破烂收来的。赵大爷正在屋内给大妈喂饭。屋内只有一张床,大妈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不能动弹。
大爷甫一见我们赶紧迎上来:“警官,来啦。”
我把废纸放在屋外地上。没办法,屋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师父寒暄了几句:“大爷客气了,送了我们两箱矿泉水。”
大爷一脸惭愧:“后来,后来环卫又把纸壳子卖给我了。你们对我挺好,我不好意思占这个便宜。”
师父点了点头,望了眼,问道:“大妈是上次摔的吗?”赵大爷摇摇头:“没摔着。精神问题。”我揷了句嘴:“大妈前两天不挺好。”大爷叹了口气:“哎,铃铛坏了。”
赵大爷拿出铃铛给师父看。一只铜铃铛。赵大爷说,这只铃铛是大妈的命根子,跟了她好多年,寻常就用一根红绳系在腰间。大爷害怕大妈走丢,反正铃在人在。结果那天,大妈在串串店门口摔了一跤,把铃铛给摔瘪了。大妈心痛成疾,病情加重,现在心理问题又变成了生理问题,连床都下不来了。
“我试试。”
师父技痒。他蹲在地上,找大爷要了柄小锤,仔细敲打铃铛,大爷陪在一旁。我闲来无事四下张望。
这大爷真有点意思。床头放着好几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摄/像头使用说明书,一本侦探小说,最下面居然还有一本童话故事。
屋子里没有电视机却有一台路由器,再抬头望向墙面,一根电线伸出墙外。我顺着电线找了出去,赫然,墙头上摄/像头监视着路口,全方位无死角。
师父喝了一声:“你干嘛呢?”
我回过神:“瞎看,师父,修好了吗?”师父摇摇头,样子复原了,摇着却没响声。赵大爷指着摄/像头:“我老赵平生三大爱好,摆弄摄/像头,看书,讲故事。”赵大爷咧开嘴:“这不是老婆子精神状态不太好。我怕她丢了,就装了个摄/像头。她也爱看监控,喜欢看里面的人走来走去。我爱看书,尤其是刑侦方面的书,这都是我收破烂收来的。她还爱听童话故事,我每天说童话故事哄她睡觉。”
师父点点头,问道:“你们没孩子吗?”
赵大爷的笑容凝固在空气中,嘴角不住颤抖。这儿不是聊天的地方,没有任何铺垫,他俩默契地走到了屋外墙角,我跟了过去。
赵大爷苦着脸:“有一个男孩,很多年前丢了,就是因为孩子丢了,老婆子精神受刺激,才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赵大爷长叹一口气:“孩子丢了,老婆不能没啊。老婆要是再丢了,我一下子去寻摸两个人,太难了。所以,我先装个摄/像头,还有铃铛提醒,防患于未然,保证老婆子不丢。至于孩子嘛,快四十年了,认了。不认咋办,日子得过。她疯我不能再疯,我得扛着。”
说着,赵大爷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重又咧开嘴,露出一嘴黄牙。
心有戚戚焉。我一直关注着赵大爷表情。从伤心、沮丧,到失落、颓唐,再到后来麻木、僵硬,最后变成了妥协,无奈。还好没看到绝望。
临走前,卖废纸那一茬绝口不提,师父让大爷留步,师父说:“大爷不送,回去好好照顾大妈,以后我们那儿要是有废品还给你。不过呢,丑话说在前头,车得换,换个斗子大一点的,或者电瓶车,双人座。前提是合法合规,上路了也没人拦你。”
等到大爷回到大妈身边,师父掏出手机迅速朝着门口的二维码上扫了一下。我悄悄跟在他后面,冷不丁也扫了一下。
休息日,难得清闲,却被师父相邀,一同拜访另一对老人。
路上,师父打量着我:“精神点,才几天功夫,你那傻劲呢?”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师父笑了笑:“刚入职时候都愣头,我以前比你还愣。这份职业嘛,注定你一生中会遇到无数个家毁人亡、妻离子散,天灾人祸、喜怒哀乐。以后就习惯了,不过习惯不等于麻木。我们麻木了,别人怎么办,我们绝望了,谁还有希望。大爷说得对,他不能倒下。我倒是挺佩服大爷,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他都能咧开一嘴黄牙,生活如果嫌弃我,我就笑给你看,谁也别嫌弃谁,哈哈哈。所以我们站岗是为了啥?就是为了像赵大爷那样的人能一直笑着。”
师父拍拍我的肩膀:“放松点,没什么大不了的。天王老子来了咱不是也没怕过。走,带你去见见我师父的父母。”
师父的师父的父母?一路上我盘算着辈分。到了地方,师父先开口:“愣着干嘛,叫伯父,伯母。我师父比我大不了多少。”
听师父介绍,伯伯姓肖,是一名医生。伯母姓徐,是本地福利院院长。今天事出有因,徐院长约了师父,说有事交代。
四人坐下,徐院长一边泡茶一边说:“我本来五十五岁退休,因为返聘,直到上个月才闲下来。你肖伯伯年初退了。后浪推前浪,真好,安松都有徒弟了。这段时间我将肖同的遗物又清理了一遍。有些东西一直收着没拿出来。可能你们的单位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
师父赶紧问:“什么事?”
徐院长添了水,继续说:“其实肖同并不是我和你肖伯伯的亲生儿子。他来我们家时已经十四岁。他应该是本地人,幼时不知何故被带到了外省。”
徐院长从盒子中取出照片,指着照片说:“你看,这是肖同周岁时在城西路照相馆拍的周岁纪念照。我们怀疑,肖同父母是在取照片回家途中将他弄丢的。后来,肖同依凭封套上的广告找到照相馆原址,结果照相馆早就关门,店面几经转手,后来转给了一家串串店。肖同也找过公安局,可惜失踪报案的档案早已失效。找到福利院时,我们这儿也没有任何有效信息。那时候肖同年纪小,又身无分文,我和你徐伯伯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我们一直没有孩子,见他聪颖好学,长得又好,干脆认作儿子。就这样一直培养到上大学,工作。后面的事你也都知道了。前几天看到这张照片,想到照片中的日期,今天正好是你师父的生日,咱俩好久没见了,叫你过来吃个饭。回头他的东西,你看交警队怎么处理,放到墓中也行。尤其这张照片,他在世时唯一的念想,我想应该放在他的身边。”
这顿饭吃得五味杂陈。从徐院长家出来时,我和师父一路无话。趁着月光,瞥见了师父的侧颜,我从未见他如此憔悴。师父发现我在偷看,正脸对着我:“你是不是想问他是怎么去世的?”
时间回到八年前。
王安松刚入警队时可没有偶像,他对师父肖同更是望而却步。肖同如果说有什么爱好,可能就只有说教。王安松每天起床三件事,刷牙洗脸吃饭,随后上午听师父教诲,中午听师父教诲,下午听师父教诲。甚至全天候不定时,不论是否在岗。肖同说了:“如果连你自己都反感说教,那你如何去说教别人?”肖同还说了:“说教是这个世界上可以付出的最低廉的代价,如果说教没有意义,那只有罚单才可以警醒。如果罚单还不足以警醒那就只剩下无尽的创伤、残疾、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显然,王安松愣头愣脑并没有将师父的教诲记在心里。在王安松一次出警失误后,肖同作为师父负连带负责。肖同被领导派去做交通宣传教育工作,王安松跟在后面拎包。半年后,师徒二人被调到城西路与三环路交叉口,全城交通环境最差的地方。
晚班前,肖同请王安松吃了顿串串,就在岗亭东面。肖同说,他从有收入开始,就常来这儿吃,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
入夜,城西路尘土飞扬,一辆辆渣土车飞驰而过。肖同捂着嘴:“妈的,开这么快。”王安松呛得咳出了声:“师父,你看。”透过烟尘,红灯迷蒙。肖同怒了:“当着交警的面闯红灯。”王安松清了清嗓子:“师父,他们好像跟上面打过招呼了。”肖同不屑一顾:“他们不仅闯红灯还超速,把它们扣下来,问问他们招呼打给谁了?”王安松迈不开腿:“师父,真扣啊?”肖同朝他吼道:“天王老子娶媳妇遇到红灯也得候着。快去,你开车,呼叫下一个路口的兄弟,准备拦停。我去拦住后面的。检查装备,保持手台畅通。”
王安松拧着手台调节旋钮:“完了师父,我手台坏了。”肖同叹了口气:“咱俩换,拿我手台。快,别让他们跑了。”
五分钟后,王安松配合下一路口的弟兄成功拦停渣土车。王安松钦住按钮:“师父,任务完成,已拦停,你那边怎么样?”呼叫几次无果后,王安松等着城西路驶过车辆,见再未有车辆驶入,王安松估计师父那边也已经拦停。
不多时,王安松准备驱车返回,手台忽然响起,王安松至今记得那段简短的、夹杂着强烈电流声的呼叫:“喂,喂,喂。”那不是师父的声音,更像是一名中老年男子。三声过后,再无音讯。
等再见肖同,是在医院,天人两隔。肖同被一辆酒驾车撞倒在漫天扬尘中。
我一时无话。师父先开了口:“你现在知道我那些外号的来由了吧。别嫌师父啰嗦,每一句说教背后都有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只可惜,这个故事与我有关,我的外号带着血。肖同生前节俭惯了,他余下来的钱几乎都捐给了福利院,离世后,我接过了担子。不过他身世的秘密,确实让我惊讶。”
“师父,你电话响了。”我打断了师父的沉思。
是赵大爷的电话。“喂,喂,喂。是王警官吗,求求你帮帮我啊。”
师父呆立在原地,那三句“喂”如同一根麦芒刺入耳朵。师父张大嘴巴浑身不能动弹,任凭赵大爷在电话那头焦急呼喊。我抢过手机:“大爷,您慢点说,怎么啦?”
我也呆住了:“师父,糟了,大妈丢了。”
事到如今,我终于理解师父说过的每一句话。当我们需要调取监控时,代表着事故已经发生。在大爷家,我盯着大爷手机,监控里大妈神情恍惚,晃晃悠悠离开了家。
赵大爷哭出了声:“都怪我,没把铃铛修好,我刚才困了,睡得死沉,她走了我都不知道。”
师父恍恍惚惚,觑着眼望着大爷,说不出任何话。我急得转圈,瞎指挥道:“大妈朝东边方向。赵大爷,你的监控范围太窄,我们先确定大方向,再分头去找。”
赵大爷拉住师父衣服:“不要,三十多年前就说分头找,我儿子就是这么丢的。我就一个摄/像头,你们交警队有那么多摄/像头,就不能帮我找找吗?求求你们了。”
赵大爷跪下来,噗通一声。
我赶忙拉起大爷,我也无奈:“大爷,失踪人口报案有时效,调取监控更需要走流程。”大爷歇斯底里,扯着嗓子喊:“等手续办下来,人就没了。她不是普通人,她精神有问题啊。儿子丢了,我亏欠她一辈子。她要丢了,我下辈子也饶不了自己。王警官,开个后门行吗?我付钱,我付钱行吗?”
我也急了,这一次,我竟然在大爷的眼中看到了绝望。我扭过头去:“师父,咋办?想想办法啊。”师父依旧无话。
赵大爷急得跳脚,对着师父吼道:“你跟你们领导说,好几年前我在城西路十字路口遇到过一起车祸,救过一名交警。肇事司机跑了,那么多渣土车司机在旁边,眼睁睁看着,没一个人帮忙。我骑三轮车送到医院,一分钟都不敢耽搁。将心比心。”
师父累了,嘴唇动了动,有气无力地对我说:“给局里打电话,调监控。”
我拨通电话,三言两语后,望向师父:“师父,局里说要走程序。”
师父冷哼一声:“他娘的,这时候来说教。跟局里说,就说我妈丢了,王安松的妈丢了。”
十分钟后,人找到了。就在城西路,离我们不过几百米远。
当我们赶到时,已经有兄弟替我们守在大妈身边。大妈静静地坐在串串店门口,手里拿着铃铛。师父仔细盯着铃铛,连我也发现端倪。
几乎同时,师父取出照片。照片右下角写着周岁快乐,照片中的婴儿甜甜地笑着,手中握着一只铃铛,一模一样。
我哭出了声,师父眼中噙着泪水,说:“大妈,回家吧,大爷来找你了。”
大妈痴痴地笑:“不回家,我带我儿子来照相,今天他过生日。”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21:39:5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21:39:56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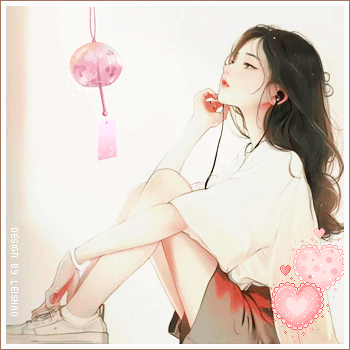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南墙撞了,故事忘了
:南墙撞了,故事忘了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4 届
:风云0-4 届












 Post By:2024/3/16 21:40:0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21:40:0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21:40: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21:40:0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21:40:0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21:40:06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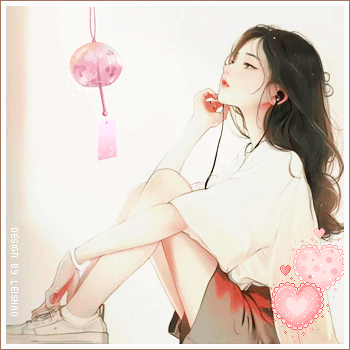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21:40: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21:40:2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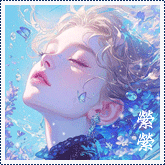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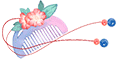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21:40:3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21:40:33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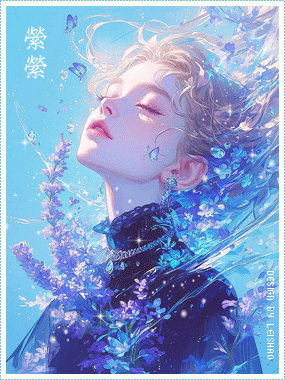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21:41:5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21:41:51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