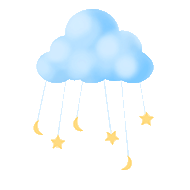代号:奥本海默
巴黎的雨夜静谧而轻柔,仿佛此刻它不再是时尚与奢华的中心,而是一个宁静的村落。维尔纳独自坐在香榭丽舍街头一家昏暗的咖啡馆角落,手中握着一杯温热的咖啡,指尖微微泛白。咖啡的苦涩和窗外的湿冷让他暂时忘却了内心的动荡。雨声如丝,如同巴黎的低语,又像是维尔纳心中那道难以解开的疙瘩。
此时,距离曼哈顿计划成功还有三年,距离德国无条件投降还有五年。时间在历史的齿轮下显得格外沉重。维尔纳默默凝视着手中的笔记本,思绪如同飘在雨中的伞,摇摇欲坠。笔记本封面上盖着日内瓦国际原子物理研究所的标志性钢戳,扉页上简洁地写着《等离子体物理与高热原子核反应》。他缓缓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矩阵和公式,犹如一张通往未来的地图,而每条路径似乎都通向毁灭。
雨滴轻轻敲打着咖啡馆的窗户,仿佛为维尔纳的思绪伴奏。咖啡馆的灯光昏黄而温暖,与外界的冷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份温暖并不能驱散他内心的阴霾。
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望向窗外的雨幕,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感。每一个公式,每一个矩阵,都是他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但同时也可能成为毁灭的种子。当他发现核裂变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了无法逆转的转动。核打击的时代已然可见,战争将被彻底改变,不再是士兵在战场上的拼杀,而是摧毁城市、泯灭人性的无情打击。尽管核弹尚未被发明,维尔纳却早已感受到那份悲剧的重量。
突然,咖啡馆的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寒意涌了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那是他的老朋友阿尔伯特。阿尔伯特脱下湿漉漉的外套,甩了甩上面的雨水,走到维尔纳的桌旁坐下,微笑着说:“我亲爱的朋友,看样子,德军又有了新的进展,对吗?”他的声音中带着轻松,但眼神却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
维尔纳微微点头,将笔记本推到阿尔伯特面前。“德军,你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祖国吗?”
阿尔伯特低头一看,认出那一行行让他无比熟悉的符号,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只有当国家把民众视为人民,民众才会视那里为自己的祖国。那么,我的朋友,是什么让你一路从柏林来到巴黎?”
维尔纳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仍停留在笔记本上的某个公式上,眉头微微皱起,仿佛在思考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我点燃了火焰,”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缓慢,“但现在我无法控制它的力量。你应该知道,这代价有多大。”
两人陷入了沉默,只有雨声和咖啡馆里轻柔的音乐在空气中回荡。阿尔伯特凝视着窗外的雨幕,心情沉重而复杂。过了很久,他深吸了一口气,坚定地说:“好吧,如果我们无法阻止那个时代的来临,那么我们就要提前为那一天建立一种制衡机制。”
维尔纳的心猛地一沉,“核威慑?阿尔伯特,我们不能这样,这太荒唐了。为了阻止核战争的发生,我们竟然要将其制造方法告知交战双方?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新科技投入战场,最终的代价将是双倍的毁灭。”
阿尔伯特的目光变得坚定,“比起破坏本身,更可怕的是不被制约的力量。维尔纳,我们别无选择。与其让一个疯狂的独裁者掌握全部的毁灭力量,不如在各方之间建立一种平衡,避免最终的浩劫。”
“阿尔伯特,我们是科学家,不应该去考虑牺牲谁、平衡谁的事情。那是政客的手段,我们的职责是探索真理,不是操纵战争。”维尔纳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
“可我们已经身在其中了……从你发现核裂变开始——从我们使用物理学揭示事物的规律开始,我们就应该知道,任何学术发现,都可能被当作战争用途,这也是一种客观的规律,就像质能方程一样不可被否定。我们能做到只有尊重这些客观规律,然后尽最大的可能去在已知规律下寻找方案。”
“是呀,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战争计划的一部分了。若非如此,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又何必自杀谢罪。”维尔纳绝望地喃喃自语,“阿尔伯特,我们要学着像上帝一样扔骰子吗……可我们是人,如何做神的裁决?”
1945年,美国新泽西州,新泽西自然历史博物馆。雨水仍在敲打着窗户,博物馆外;玛加丽塔,细雨燕双飞……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9/13 20:30: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9/13 20:30:2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灯,等灯等登!
:灯,等灯等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9/13 20:30:4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9/13 20:30:49 [只看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