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茶
“茶醉”的说法,最早由祖母口中听来。她见我一大早喝大杯茶,早饭后喝小杯茶,出门回来换茶叶继续喝,便说,这么喝,可会得茶醉了。我说不会。心想,老人家说的茶醉可能是茶瘾,并非“酒醉”那种。
有次几个朋友来访,随意地无主题地高谈阔论,配着茶点,换了好几种茶叶,到了窗外天色暗下来时,分明觉得说话不利索,脑袋晕晕的,像极了饮酒醉的状态,不困乏却眼睛睁不大开。我很艰难地说,喝茶也喝醉了。回想起祖母所言茶醉,大有恍然之意。
那一次醉过,隔一段时间,会想尝试再喝一场茶醉来。然而,不论是一个人喝二个人喝多人喝,不论喝多少茶水,都不曾喝出睁眼不开说话不利索的“醉”意。便有点怀疑茶醉是不是真实发生过。
2018年元旦,两个朋友相约喝早茶。去一家没去过又满有口碑的老茶楼,我们各自带上一点茶叶,从上午喝到中午,从早点吃到午餐,二点多出来,太阳下,蹒跚一晃,是晕乎了。明白了,两次茶醉,醉的不是喝多了茶,而是说了太多的话。上次便是她们和另一个朋友一起来,我们讲得不停,与发酵的茶叶一样,脑袋因言发酵,便以为是喝茶醉了。真相大白!
每天早上起来先喝茶,是少年时的模仿秀延续至今成了习惯。据说谭嗣同在北京的浏阳会馆被捕的那天早上,他烧了一壶水,倒在盖碗里,悠闲地坐在太师椅上喝着茶等着前来抓他的官兵。书中描写的谭公的气度折服了少年,一些意气便萌了芽,当下找父亲要了一个不值钱的盖碗用,慢慢地有了早晨喝大杯茶的习惯,只是茶碗换了多回,越来越简单了,能用便好。
醉酒
不沾酒很多年了,是以看到题目而第一件想到的是茶,然而,总还是想起一二件过去饮酒的事情,譬如,在风云拿剑时,与小爱在屏幕两端,一边喝酒一边瞎抓。当时喝的是清酒,好似便是小爱推荐的。酒是喝的高兴了,虾也屠的尽兴了,结果不出意料地阵营输了。输也输的开心。
有回周年庆,我们和蛤蟆77一起拿剑。代号是各方菩萨,当时便觉得代号太庄严了,四人要被反噬吧,果然,我先拿着地藏菩萨的塑料剑上楼,一上再上,紧接着,蛤蟆跳剑救我,被上楼,77只好接着跳剑救两个高票的剑……前面几轮的票楼光折腾联剑了。至今想来都是好笑。那时候还没戒酒,看到蛤蟆跳剑救我自己搭上票楼,一口酒直接笑喷了。不出意外,阵营又输了。输也是输的开心啊。有几年没听到蛤蟆的消息了,77偶有听到。忽然,便想再喝一口酒了。
醉花
朋友培育的无名月季,开花了。粉紫色一朵,叫做空濛。粉紫色的花瓣薄且几乎透明,于叶间盈盈一朵,清新寂静。瞬间就爱上了。
朋友爱花,尤爱养花。那朵让我瞬间爱上的空濛,本是云南花场包邮的花苗,花农剪下来的不要的多余的散枝,并非名种,打包放淘宝包邮,极便宜,但几乎养不活,遑论开花。
他的静气,时常让我歆羡。泰山崩于眼前依然在松土,或者,对已经衰亡的海棠,依旧默默地为其换盆。我曾形容过他,最静是种花最清越是抚琴。那句形容的句子,一晃过云了十三年。不论为海棠换盆,抑是形容他的诗句,均曾在风云杀人时写过。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他养了十五年的花,我的兴趣换了一拨又一拨,而他在生活的轻描淡写里,依然是栽花种草,单就月季的种类养了不下二十种。恐怕我在风云提刀杀的人,累加起来不及他培育的花开,更不及他送走的花谢。那天他说入冬前的最后一拨昙花有八朵。我说可以煮水加冰糖,明晨给娃喝。
瞬间想起小时候,有天大清早,刚起来,先祖父喊去倒昙花羹来喝,顿时杵在回忆里,微微一醉。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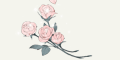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482-3 届
:风云482-3 届








 Post By:2022/11/4 17:19:2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4 17:19:2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也许明天。
:也许明天。
 :四时昼恒新
:四时昼恒新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3 届
:风云0-3 届




































 Post By:2022/11/6 12:29:1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6 12:29:1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江山还似旧温柔
:江山还似旧温柔
 :神秘空间10号
:神秘空间10号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11/11 10:37:5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11 10:37:5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江山还似旧温柔
:江山还似旧温柔
 :神秘空间10号
:神秘空间10号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11/11 10:38:1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11 10:38:1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2 届
:风云0-2 届















 Post By:2022/11/11 11:27:5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11 11:27:5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11/12 21:12: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1/12 21:12:1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