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区野花》
这个题目毫无道理,开在无人区的必然是野花了。但转念一想,有人与无人确实也有差别,就像双缝干涉实验一样,能因是否被观测而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有人区的野花,有被欣赏的机会,无人区的野花就是一种存在的概念,可是花朵的绽放,本来就不是为了给人欣赏的。野花的“野“字,便已经有了挣脱束缚的自由意味,前面“无人区”的定语,倒略带了人类视角的傲慢。
从什么角度看一朵花,在思维作出判断的千分之一秒里便有了答案,由一双眼睛出发,在光的折射和散射里捕捉花的形状和色彩,再由大脑从“我”里对将现实的花与概念的花相互对应,我们说“看到了一朵花”,其实是“遇到了一朵花”,花存在的状态不因“看不看得到”而改变。我之所以如此强调“我”与“存在”的关系,是因为我常因过分地在乎“自我”,而无法做到冷静地看待客观事实。
这种表现之一便是“文字羞耻症”,我常羞愧于笔下的文字,不论是将文字示于他人,还是承认某一段文字是出自我的手笔时,内心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羞耻与惶恐,这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惯性,它们在暗处隐隐地逼迫我对那些文字作出决然的切割,仿佛它们的存在一旦与我产生关系,便会如病毒一般入侵神经系统,对我的生存产生无法控制的危机。这种“文字羞耻症”一度困扰了我很久,我拒绝承认它们与我是同样的一个整体,我将它们封存在厚厚的箱子里,每次打开时都要忍受厚厚的鸡皮疙瘩。我过分关注自我了,时时刻刻都在无微不至保护着它,它是一朵野花,不愿接受外界的观察。
打败“文字羞耻症”的是年龄,更精准点说是时间,环绕在野花上方的玻璃罩子是有保质期的,它会渐渐适应窥探,不在乎窥探,会像不断弯折的金属进入疲劳的临界点,继而出现裂痕,当玻璃罩完全破裂的时候,野花才真正成为了野花,会发现它本就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它是一种存在,一颗雕琢过的石头,但终究是石头,作为一颗石头,鹅卵石和火星上的岩石并没有本质区别。
没有去过无人区,但是见过花,想来不同地方的花也没有多大区别,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与上一代和下一代也没有区别,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独特的灵魂呢?它们只是走着不同的路,赶赴的却是同样的终点。我不该如此悲观,若换一个角度看,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平庸的,独特的是那个能与你产生共鸣的人,没有他的出现,也就无所谓独一无二了,在两条路或无数条路径的交汇点,是理解和共鸣将我和他人区分而开,于是生活终于突破了“自我”,可以从“他者”身上寻找定位,这种寻找他者的期待,总算让“文字”并非变得毫无意义。
小时候,女孩子看到路边的野花喜欢摘下来别在头上,男孩子喜欢拿一根木棍将野花统统斩断,这是对待花的不同态度,我觉得被踩在脚下的花,比挂在枝头的更美。
——0327








 :在大风吹来之前
:在大风吹来之前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
:

















 Post By:2024/3/27 16:41:30 [
Post By:2024/3/27 16:41:3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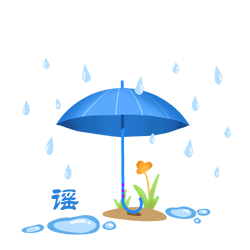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