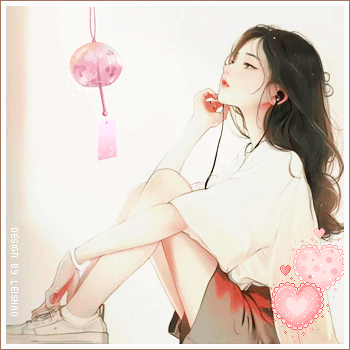沿着宽阔平整的马路一直往北走,沿途种满了花草树木。
花有一株一株的月季。这些月季的花株一般都不高,不像庭院种植的那般高大,但是跟所有的月季一样,每年至少有三个季节,它们都能五颜六色地开着;也有灌木的花丛,从根部伸出一条条长的触手,这些触手没有遇到墙壁或者粗壮的可以攀援的树干,它们只能将伸出的手臂擎着,向左或者向右,好似在给归家的人指明道路,又似一个个孤寂的旅人,在风中摇曳着。还有一树一树的,花团锦簇。我分不清是樱花还是桃花,春天的时候放眼望去,路两旁竖起了两座粉墙,到花朵落下,树上也会结出桃子一样的果子,但是它们跟我印象里的桃树又不同。
路旁还有松树,缀满了大大小小的松果。秋天的时候很多人来摘,这种松果果仁很小,人们摘了不是拿来吃的,是为了生火,松针富含脂肪,烧起来滋啦啦响。
这是一条回乡的路。沿着这条两旁种满花草树木的马路一直往北走,大约走二三十里路,便能看到一座村子。进了村,柏油路换成了水泥路,行不多远,就进入村子的腹地。
这是一个人烟越来越稀少的村子,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我家房后有一条河,这让我对乡村的记忆,又在越来越萧条之后,又凭空生出一些乐趣。而因为这些乐趣,又让我在若干年后,因为一条异地的河流,梦回故乡。
故乡的这条河流是东西走向的,每年到了汛期,水库里都会开闸放水,水从大坝上一泻而下,沿着小河向东流去。到我们家房后,就被很多小伙伴拦下,其实拦下的无非是些小鱼小虾,玩够了就被我们扔掉了。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宿命吧,想想小小的我们,那时候竟然能够主宰这些小鱼小虾的宿命,如今也是要惊骇一下。
但是小时候我们找寻的,只有趣味。
到雨季正式到来,河里的水便许久不退,我们摸鱼摸够了就打水漂儿,我们丢一个,它便落下去,再丢一个,它又落下去,我们便缠着大人,看着薄薄的石头在水面跳跃,像跳舞一般,于是也争先恐后地将身子侧弯,模仿着大人的样子丢出去,嗖——嗖——嗖……
最热的就是午后,知了在和河两边的槐树上一个劲儿地叫:热啊——热啊——。
午后,我们去沾知了,因为这个时候的知了叫得最欢,你只需听听声音,就能辨别出哪棵树上的知了多。不一会儿便能粘到好多,洗净了将翅膀摘去,晚上炸了吃。
还有一种方法并不需要听知了的叫声。雨后,泥土地变得松软,知了猴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数年的蛰伏,冲破地表的束缚,爬到树上去。它们一边爬,一边将身上的壳退掉,让翅膀露出来,因为它们要飞了。
知了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有时候飞得更高,我们的竹竿就无能为力了。
够得着的知了也不一定都能被我们粘住,有时候知了很傻,你慢吞吞它也不飞,上手就能粘住,有时候它极聪明,没等粘竿碰到它们,排了一泡水就跑掉了,被知了的水碰到,粘贴物就失去了黏性,很难再粘住它们了。
虽然小时候粘知了也不太行,但是现在完全不行了,眼睛只会瞅电脑和手机了,根本看不到知了翅膀在哪里,找了一会儿,脖子就酸。
夏天的趣味还有很多,多得像河床上曾经铺满的鹅卵石。
可是如今,我只能在夜里守着一条河,守着轰隆隆的盛夏的流水声,回忆曾经的河两岸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4/7/6 8:12:50编辑过]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阿悦的糖果屋
:阿悦的糖果屋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7/4 21:15:5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4 21:15:5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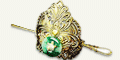

 :落樱
:落樱
 :尘缘
:尘缘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7/7 19:32:2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7 19:32:2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阿悦的糖果屋
:阿悦的糖果屋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7/8 21:29:5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8 21:29:5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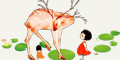

 :娱乐圈顶流嗜睡演员
:娱乐圈顶流嗜睡演员
 :花小獾
:花小獾
 :一片林深时见鹿
:一片林深时见鹿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7/9 16:43:5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9 16:43:5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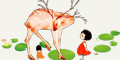

 :娱乐圈顶流嗜睡演员
:娱乐圈顶流嗜睡演员
 :花小獾
:花小獾
 :一片林深时见鹿
:一片林深时见鹿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7/10 10:24: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0 10:24:4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7/10 13:28:1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0 13:28:12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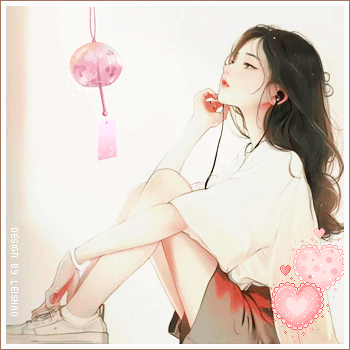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对四
:对四
 :三四相依
:三四相依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661-1 届
:风云661-1 届













































 Post By:2024/7/10 23:25:0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0 23:25:0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7/11 14:36: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7/11 14:36:23 [只看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