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い出は亿千万
“子供の顷やったことあるよ,色褪せた记忆だ……”熟悉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他的专属。
“你到了吗?”电话那面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询问着。
“到了。”我很习惯这样与他对话,毕竟他是我一生的大哥。
“老三啥时候去?”他问道。
“还半个小时吧。”我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你不是也到c城了嘛?你来吗?”
“……”那边沉默了片刻,“不了,免得他见了我烦。而且我还得赶今晚的飞机去佛山,那边工程出了点问题,几位大领导点了名要见我……”
“好,你没事吧。”
“没事的,按流程正常处理就是了。”
“嗯……”我点点头。
那边又是片刻的沉默,而后,他难得地又叫了我一声,“老二。”
“大哥你说。”
“今晚跟老三谈完,不过什么结果,都务必给我发个信息。”
“好,你放心吧。”
果然,他还是最在意着老三,不过我也跟他一样,否则就不会千里迢迢从南国赶来吃这顿饭了。
有人说,高中是交朋友的最后时间,因为走进高校后你所遇到的人都现实了,不会掏心窝子真心对你。然而这句话并不适用于男生,尤其是我们三个长不大的孩子更是如此,一起逃课打魔兽、一起为了卖点卡省钱吃泡面、为兄弟大打出手最后被社会上的混混围在角落里一顿踢打,回想起那段时间,我所想起的却并不是颓废或浪费青春那些词,那段时光于我而显得言单纯而真实,至少相比现在为了糊口而混沌度日要真实得多。
大三时,我们换了一个负责任的辅导员,当她把我们父母都叫到我们寝室参观时,望着三台从网吧用折扣价买下的二手电脑和散落一地的啤酒瓶,我们三个尴尬羞愧地恨不得钻进地缝。
事已至此,我一言不发,自己犯的错就自己担吧,父亲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我,愤怒之中却依然有着一丝怜悯,我心里叹了口气,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然而,不是所有父母和家庭都如对我这般宽和。
老三的父母是质朴的北方小城职工,见辅导员说老三旷课太多可能要以退学处理时他们惊慌了,走投无路的他们竟然当众跪了下去,这是多么耻辱的事情,可老三却只能用颤颤巍巍的手捻着衣角,嘴唇被上牙咬成了黑紫色。
“是我拖着他逃课的,要退学就处理我吧。”老大愤懑地站了出来,可即使这样也没什么用,因为校规就是校规。
“啪!”一个极为响亮的耳光打在他脸上。
老大的父亲是个质朴刚烈的西北汉子,老大是他的骄傲,那个凭着日夜苦读从陕北山坳坳里考出来的家族希望竟然如此叛逆,他实在是不能理解。
“啐!”老大猛地往地下吐了一口,带血的牙齿重重落在宿舍地板上,他摔门而去,而老大的父亲已然瘫倒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男人哭,那种感觉是语言无法描绘的。
老大失联了,他这一闹间接坑了出于关心才协调此事的辅导员,也弄得学校在处理此事上软了起来,事实上,校规也无外乎人情,我跟老三被法外开恩留校观察。利用这个机会,我拼了命地用一年半的时间修完了所有挂掉的科目,后来还继续深造考了研究生,读了博士,最后留在了南国,而老三在挣扎了两年后也拿了毕业证,回到了自己的城市进了一家企业上班。
而我们当中最有出息的还是老大,他靠着一张身份证一路南下,从杭州辗转到福州,又奔波于深圳、广州、佛山等地,靠着同乡的帮衬、实打实的技术本领和极高的情商在建筑行业一路高升,穷尽十年之功成了各地市领导都要亲自接见的xx集团副总,闲暇之余,他顺带又把建筑行业几个最难考的证都考了一遍,也算是对当时自己大学没毕业的一个交代了。
老大这种人是天生的将才,我看他的眼神总是崇拜,唉,如果老三在生活上有他十分之一的拼劲就好了。
“喂,二哥。”一声招呼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是老三,他来了。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没有变,似乎被时间定格了一般,唯一能说出来的变化,或许就是言语间的神情更加不自信了。即使这般熟人的打招呼,他热情的声音中也犹犹豫豫地,带着一丝胆怯。
“老三,坐吧。”我笑着邀请他,然后吩咐服务员点单。
在他的建议下我们点了些地方特色菜,这是他的家乡,他的主场要给他表现得机会,他点餐我买单就是了。
“可以抽烟吗?”点完餐后老三小心翼翼地问了下服务员。
服务员指着吸烟区得牌子点了点头,他刚兴奋地拿出一盒万宝路,闻不得烟味的我下意识咳嗽一声,老三敏感地眨了眨眼,把烟盒又放在了桌子上。
“没事,你抽你抽。”我有些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我等会抽。”老三也有些尴尬,试图转移开话题,“一路行程怎么样,还顺利吗?”
“还好,就是上飞机睡觉嘛。”
“最近因为疫情来c城的航班减少票价都涨了,你还坐飞机啊?”
“没事,正好我要来c城参加个学术会议,来回路费是可以报销的。”我平淡地回应了一句,看老三脸上一副难堪的神情,我意识到自己居然不自觉地“凡尔赛”了,其实我并没有丝毫嘲笑他的意思,可他性格总是懦弱多疑,打从前就这样。
“你怎么样,听说要评副教授了是吗?”
“哪这么容易。”
“你不是都出书了吗?”
“我们学校规定还得有课题,没课题很难评的。”
听我这么说,老三似乎捡回了自信,“是啊是啊,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好,正常上下班,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微笑地看着他,并没有点破,老大跟我说过,老三做的是流水线计件工作,他技术不过硬又常请病假,若不是老大在背后跟他们领导打点,老三早就被开除了,而他的媳妇嘛,唉,一言难尽。
“怎么了?”他被我盯着有点慌。
“你呢?小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不是说了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还能过什么日子,安稳的幸福呗,哈哈哈哈。”
他尴尬地笑着,我也虚假的回应,据我所知,她老婆在外面有情人,还不止一个,孩子刚满一岁就很少回家了,也许是看在孩子的情分上吧,他一直默默忍受着。说实话,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我和老大对此极看不惯,隐约间也觉得他这样做丢了我们三兄弟的人。
“这么说弟妹还挺贤惠的。”我继续试探,想着让他更多地露怯。
“那当然,她烧得一手好菜。”
“哦?那我什么时候可要去尝尝。”
“当然欢迎,不过她最近加班,总是忙,正好赶巧了,唉……”
就知道他会找借口。
“对了。”我喝了口水,进入正题,“听老大说给你找了个他身边的职位,工资不是比你现在高吗?你怎么不去啊?”
“我不想沾他便宜。”
呸,假清高,我心里暗骂一句,劝解说,“我们同班同学好多跟着他的,现在职位都混得不低,这事也没什么沾便宜一说,就算有,以我们兄弟的感情,沾他点便宜怎么了?你总不能在生产线上干一辈子吧。”
“可他的工作要四处跑,而我还要顾着家……”
我以为他说的家是自己的小家,还在秀那虚假的恩爱吗?看着他那以假乱真的演技,我怒了,心想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冷冷地讽刺道,“你知道同学怎么议论你吗?说你找了个破鞋,找了个婊子!”
我也顾不上自己教师的身份,故意说话言语不客气,有意识刺破他的自尊,想让他清醒面对现实。
老三嘴唇颤颤巍巍地颤抖着,嘴里嘟嘟囔囔说着,“二哥,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
“我怎么跟他们一样。”我生气地调高了调门,“我也不信的,来见你之前我为了你特点找她了解了一下,你知道吗?我们本来谈得都是你们家庭的事,可就是你说的那个贤妻良母,居然想当众勾引我,你说这事是不是恶心?”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他垂着头,如泄了气的皮球般负隅顽抗地对待我。
“当然是为了你。”我余怒未消。
“那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你去找她干什么?查案吗?你是大侦探嘛?”终于,他也怒了。
他一连串的问题把我闻懵了,确实,因为老大跟我介绍的那些故事,我潜意识里就把他当成了一个说谎精,而不是兄弟,我把对他的关心看成了一份善事居高临下地施舍,而不是出于那份兄弟之间的爱。
“可你为什么要隐瞒?”
“为什么,还不是怕你担心。”
“怕我担心你就应该听老大的,离了再找一个呗,你离了女人就不行?”
“你们有想过我父母吗?”他的眼神突然果决起来,直勾勾盯着我,把我盯着浑身发冷。
我愣了,确实,我以己度人,没有思考过他的具体情况。
“我是离了女人就不行吗?我的第一个妻子是小倩,你们知道的吧,我们大学同学,你们倒是都说我俩般配,结果呢?结婚两年就离了,她家里托关系找了xxx,三十万彩礼钱一分没给我退,最后给我判了个赠与,呵呵,赠与……”
我沉默了,无言以对,这件事我其实也是知道的。
“这个女人水性杨花我早就知道,可她不要彩礼啊,只要孩子是我的就行了。我爸妈都老了,好不容易有了孙子,我还要折腾什么,离了婚让两位老人再操一次心吗?我为什么不跟老大走,我爸妈都八十了,他们还能活几年?”
我微张着嘴,想要劝解着什么,却被驳斥得无言以对,确实,社会上存在着太多不得已和苟且,我生搬硬套地把自己这个群体的思维逻辑和道德要求强加给别人身上,这是多么不堪,尤其这个对象还是我们曾经一起吃一碗泡面的好兄弟。
他为了父母对付着过生活,他错了吗?或者是我错了吗?
老三走了,手足无措的我拿过他留在桌上的那包烟,颤颤巍巍地点上,猛地嘬了一口,辛辣的烟雾涌进我的喉腔,错碰了下手机,那里正播放着我们读大学时最喜欢的那首同人歌曲——“倏然而逝的景色,亿万千,亿万千,擦身而过的季节,留下伤痕;你给我的勇气,亿万千,亿万千,错身而过的季节,满是戏剧。”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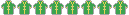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1/20 8:34:3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20 8:34:3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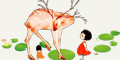
 :最爱风月
:最爱风月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16-5 届
:风云516-5 届










































 Post By:2022/1/28 18:47:1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1/28 18:47:1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聍
:浅聍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2/15 16:41:3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6:41:3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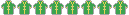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2/15 16:46:2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6:46:2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聍
:浅聍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2/15 16:55:3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6:55:3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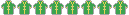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2/15 16:57:5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6:57:5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聍
:浅聍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2/15 16:59: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6:59:0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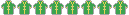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2/15 16:59:1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6:59:1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聍
:浅聍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2/15 16:59: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6:59:2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叶青青
:叶青青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2/15 17:02:4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2/15 17:02:47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