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梦,它陪我度过高中毕业前的每个午休和不眠之夜,发散想象力的过程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并忘记时间的流逝。等我从窗前走开,准备看会儿电视的时候,房间里竟多出一个男孩来,他穿着病服,坐在老人睡过的病床上,双手撑着床沿,正看着我。
“我能看会儿电视吗?”他问我。
“一起看吧,我也正准备看呢。”说着,我打开电视,回到自己床上躺着。
少儿频道暑期档的节目尤其丰富,我们两人看得津津有味,只是中途再没说过话。直到动画电影播完了,他才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我先走了,晚点儿我再来可以吗。”原来他并不住这里,是擅自走进我病房的。
我不想显得那么友好,毕竟我不是经常拥有这样可以肆无忌惮看电视的机会,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我说:“随便。”
“拜拜。”他跳下床,走出房门。
当天晚上,男孩没有来,我独自看着电视,心里竟有些失落。我在乡下长大,男孩八成是城里人,他和我还有我见惯的乡下孩子不一样。他细皮嫩肉的,长得也好看,给人一种学习成绩很好的斯文感。十二岁的孩子词汇量并不多,我只是觉得自己想和他交朋友愿意让他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做个“男二号”。
第二天下午,男孩才再次出现,他先推开门,试探着往屋里看了看,发现我已经看见他了,才开口:“我能进来看会儿电视吗?”
我点点头,说:“可以。”
我们依旧像昨天那样前后错开坐着。动画片中间播广告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几眼,主动问我道:“你多大了?”
“十二岁,你呢?”
“一样。那你明年读初中了是吧。”
“是啊。”
“你小学哪的?我实验小学的。”
“我在乡下读的小学,在一个村子里。”
“哦,那我应该不知道。”
“你在实验小学,那你认识王瀚杰吗?”他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同学,后来转去了县城的实验小学。
男孩摇摇头:“不认识。”
“你们一个年级是不是有很多班?”
“对,我们有五个班。现在的一年级更多,有八个班。”
不知不觉间,这场对话成了问答,我接着问他:“你为什么住院?”
他耸耸肩说:“我被车撞了。”
“真的吗,我也被车撞了,被一辆摩托车!你呢?”
男孩短暂地思考了半分钟,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然后描述道:“我们的车被一辆卡车撞了,当时我坐在副驾驶,我爸开的车,我妈坐在后面。我就看见那车冲我们撞来,后面的事我就记不清了。”
我仔细打量着男孩,他看上去很健康,我想或许他跟我一样只是受了轻伤,正在住院观察。动画片正巧开始了,我们继续看电视。
快到饭点的时候,男孩走了。我问他晚上还来不,他说不知道,因为他住在别的地方,走过来还挺费劲的。
第三天同一时间,男孩来了,这次他靠坐在隔壁床上,和我平齐。我拿出亲戚们带来的零食叫他一起吃,他看着那堆我视为美味的东西,摇摇头,表示自己已经吃腻了。
从中午开始,窗外就不见阳光,乌云低垂,像一床细碎的棉被,笼盖我能看见的整个天空。男孩进来后不久,乌云变得越来越厚,房间里变得愈发暗淡,最后只剩电视屏幕透出的打在我们脸上。男孩扭头看了看窗外,兴奋地翻身下床,跑到窗台前,说:“要下雨了吧!”
“是吧。”我正关注着电视中的剧情,并不关心窗外发生了什么。
“你看那里还有座房子,跟个岛似的。”他指的大概是那间瓦屋。
“那是‘破铜烂铁’住的房子。”
“我看到了,他正在院子里卸货呢。他还有条狗。”
“是条狼狗。”
“应该是黑背牧羊犬。”
我是听到过“牧羊犬”这个词的,但当时我并不认识牧羊犬,加个“黑背”就更令我迷惑了。那时候的男孩子们,会刻意记住那些当时并不常见的汽车的标志,然后会在与同伴们逛街并碰巧看见那类车子的时候,仿佛他们家有一辆那样的轿车似的,轻描淡写地喊出它们的名字,以此来满足虚荣心。而男孩喊出的“黑背牧羊犬”,在我听来,比脱口而出某个豪车品牌还让人羡慕。
城里孩子了解的东西就是要比乡下孩子要先进,我们还在背汽车标志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研究狗的品种了!我这样想着,也走到窗前,和男孩肩并肩站着。我远远的看着那条狗,默默地记住它的模样,以至于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看到类似的狗,就装模作样地喊它们“黑背牧羊犬”。
轰隆隆,天上打雷了,但声音不大,闷闷的,被乌云捂着。
“马上下雨啦,他要被淋成落汤鸡咯。”说着,我们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正笑着,弹珠大小地雨滴就开始劈里啪啦地落下来,田野间顿时弥漫着茫茫雨幕。淋雨的人手忙脚乱起来,他跳上拖拉机,先把上面堆着的纸板箱丢到屋檐下淋不到雨的地方,然后开始往地上丢一个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大概是他太用力,有个袋子被撕破了,里面的塑料瓶子全撒了出来,五颜六色的,像广告里地彩虹糖似的,散在院子里。我们又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车斗上那最后一个白色大蛇皮袋似乎很重,男人没有将它提起来,而是将它拖到车斗边上,然后他便跳下车,消失在了屋檐下。
“那是什么东西?看上去挺重的。”我问了句。
“不知道。”男孩当然不知道。
“你看之前那些袋子里装的应该都是瓶子,挺轻的,他轻轻松松就提起来了。这个袋子怎么就这么重,是废铁吗?”
“我看不像,废铁干嘛还装个袋子呀,直接丢车里不就行了。”
“不是有那种小的铁嘛”
“也是。”
我们正聊着,男人又出现了,他跳上车,弯下腰把袋子往外推。这时,屋檐下又走出一个扎马尾辫的女人来,大概是他老婆。女人张着双手,要去接那个袋子。最后,两人合力把袋子从车上弄下来,一前一后抬着它,走进屋檐下。
我正好奇那袋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男孩冷不丁地问了一句话,听得我汗毛倒竖,既兴奋又害怕。他说:“你看那袋子里装的像不像一个人?”
雨一直下到深夜。我本该很快睡着,可一闭上眼睛,夫妻两搬进屋子里的那袋子就越来越像人形,迷迷糊糊间,它甚至会挣扎起来。我不止一次起床去窗边,盯着远处那瓦房看。房子里始终亮着灯,昏黄的灯光透过屋顶瓦片间的几处缝隙露出来,吸引我去想象里面正在发生的事。回想起下午看到种种,我很容易就把那些关于小偷和人贩子的传说,套在了那对夫妻身上。幻想或许正在照进现实,兴奋得我浑身颤抖。
我最后一次起身去看那间房子,灯突然灭了,黑漆漆的雨夜,窗外再也看不见什么。
“去那里探个究竟吧。”身后突然传来男孩的声音,吓得我一激灵。我回头,看见他正站在空病床的床尾,脸上带着小孩子熬夜时的兴奋劲。
“你怎么也没睡觉?”我问他。
“一想到袋子里是个人,我就睡不着。”
“我也是。”我坦诚道。
“那我们去看看吧,如果里面真是个人,我们就报警。”男孩小跑到我跟前,拉起我的手要往外走。
“现在就去吗?”
“对啊。”
男孩力气很大,我来不及犹豫就已被拉到走廊上。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止
:浅止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3/4/12 8:43:2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2 8:43:27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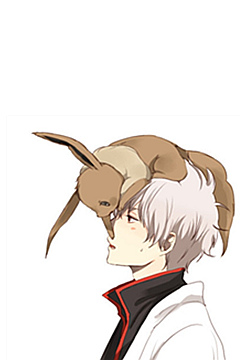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止
:浅止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3/4/12 8:45:0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2 8:45:05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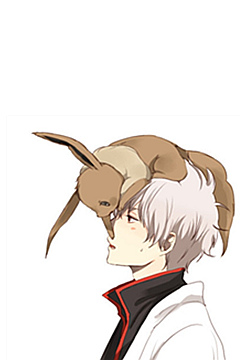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止
:浅止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3/4/12 8:45:4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2 8:45:4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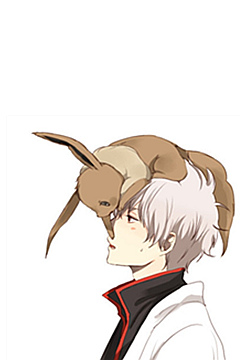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浅止
:浅止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3/4/12 8:47:0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2 8:47:02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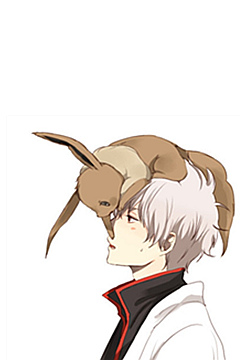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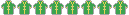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3/4/12 9:27:2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2 9:27:2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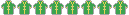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3/4/12 10:04:3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4/12 10:04:3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3 16:29:3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3 16:29:3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3 16:37:5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3 16:37:57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归墟演梦
:归墟演梦
 :鹏
:鹏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3 16:40:0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3 16:40:0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3/5/3 16:42:2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3/5/3 16:42:27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