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由信六岁的时候,第一次戴上皇子的冠冕。
那是一顶奇异的帽子,当它被托在服侍更衣太监的手里时,仿佛整间屋子的光线都被集中到了帽檐的垂珠上。
朱由信完全被这些琉璃彩珠吸引,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看。于是那太监的腰弯得更低了,脸上的笑容也更显慈祥。
其实朱由信只是想数清楚珠子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可是珠子一直晃啊晃,明明房间里没有风,那些珠子却一直摇摆着,就像有一只奇异的手在操纵,不时碰撞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朱由信心里默念的数字便又被打乱了。
可他是一个执着的孩子,每次被打断,他就从头开始数。直到帽子被戴在他头上,珠子的晃动也没有停止。于是,连眼前的世界都变得光怪陆离起来。飞檐下探出的龙首慵懒地扭动着,似在回望,柱子上盘踞着的龙身漫不经心地盘动起来,整座宫殿仿佛被唤醒了,随着他的脚步变得生机勃勃。前所未有的体验让他目眩神迷,却又很快痴迷在这新奇的冒险中。
穿戴冕服是一项漫长而枯燥的工作,所以,当朱由信终于完成这项工作时,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奖赏。可是这一天,宫内格外忙碌,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开始的天地祭礼做准备,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跑来跑去,没有人注意到朱由信的小小冒险。
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小小院落,失陷在一片更为广袤的宫殿中,像一尾被扔到浅滩的小鱼。他觉得很渴,于是大口喘息起来。他开始奔跑,额前的垂珠跟着跳跃,整个世界摇摇欲坠。不记得经过多少扇一模一样的门,最后他在回廊的尽头,折进其中一扇。
屋子里很黑,从门口透进来的天光隐约照亮了几排高大的书架,有金色的尘埃在袅袅升腾,空气在这里变得粘稠,充斥鼻端的是已经干燥的潮湿味,与母妃房间里的味道一样。于是朱由信安下心来,在其中一排书架前坐下,倚着橱框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一抹明艳地阳光正从半掩的门中斜射进来,一半打在他的脸上,另一半落在屋子角落一面巨大的铜镜上。朱由信从未见过这样大的镜子,落在上面的阳光化开,融成瑰丽的颜色,迷离得像一场梦境。所以,当一个和自己戴着同样帽子的孩子,手捧书本,从镜子背后钻出来时,朱由信分不清这到底是另一个孩子,还是自己的影子从镜子里走出来了。甚至直到很多年后,朱由信回忆这一天时,依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真的,还只是童年无数古怪梦境中的一场。
朱由信伸出手,想去摸一摸那孩子的脸,终究还是觉得太失礼,又生生停了下来,只是捧起孩子帽子上的旒珠。这一次,他终于数清楚了,一共有五种颜色。
之后的记忆变得很慌乱,两个孩子开始争论他们到底有没有错过祭礼。朱由信感到很害怕,他知道母妃有多么重视这场祭礼。母妃是一个压抑而寡淡的人,可当祭礼的日期一天天接近,她干枯的眼波却一点点变得丰盈起来,对这场祭礼的期待成了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的亮色,所以朱由信不敢去想缺席的后果。
朱由信不知道祭礼到底什么时间举行,落在地上的阳光被拉得窄长,似乎已经是黄昏时分,他疑心自己已经错过了,便往阴影里退缩了一步,黑暗可以给他安全感,让他觉得闭上眼睛再醒过来时,或许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梦。
可是那孩子却说:“不出去看看怎么知道?”不由分说地拉他跑了出去。他们一起在宫殿里乱撞,然后被一群同样慌乱的内侍找到,不由分说地将他们扛起来。终于在祭礼开始前,把他们送到了一身袞冕的父皇身边。
之后便是庄严的鼓乐奏响,父皇手捧礼器,一步步登上高台。而朱由信和那个孩子一起走在父皇身后,亦步亦趋。登台的仪态是反复练习过的,每一步都必须走得端方,这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那条路深得仿佛走不到尽头。
他一直盯着天边的落日,想着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落下,可是落日纹丝不动,像被画在空中一般,真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落日。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大,有几次他以为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可是那个孩子还跟在父皇身后,影子一般,他只能咬着牙,拖着灌了铅的双腿继续走。
终于,他们登上了高台,广场上的人群开始舞蹈,他们夸张的动作与肃穆的表情重叠在一起,混合成奇异的舞姿。他们的嘴唇翕动着,歌声却混合进鼓乐声中,什么也听不见。
朱由信此时才发现,原来头上的冠冕如此沉重,丝绦在下巴上系成一个死结,狠狠勒进肉里,被汗水浸渍得生痛。
可奇异的是,他没有想过去摘,反而福至心灵一般,似懂非懂地意识到那顶冠冕意味着什么。落日稳稳地压在冠冕边缘,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可他努力挺起胸,站得更直了。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江山的重量。
二、
朱由信是个安静的孩子。从他记事起,母妃对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安静”。母妃说话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但她的声音却那样疲倦。朱由信便踮起脚尖,努力将脚步声放得轻一些,再轻一些。
他的母妃本是太后的宫女,即便在生下她之后,母妃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本分。这是属于她的生存智慧,像紧紧依附在壁角的青苔,拼命降低着存在感,只为在阴影里偷生。
他跟着母妃寄住在慈宁宫,太后上了年纪,老人家总是爱清静的。慈宁宫里永远都是沉闷的,紧闭的门窗连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因为风吹过帘幕的摩擦音会惊扰到太后。朱由信以孩子天生的敏锐察觉到,这安静里似乎潜藏着什么。
朱由信是父皇的第七个孩子,他曾有过六个哥哥,却没有一个能活过一岁。在这阴沉的宫殿里,孩子的到来像一个诅咒。那些口耳相传的秘密面貌狰狞,似乎随时都会张开血盆大口。朱由信总是做一个梦,梦见看不清样貌的怪物在死寂的宫殿中逡巡,母妃带着他躲在一根巨大的柱子后面,死死捂住他的嘴——不能出声,不能被发现。
梦境的结局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在那些反反复复告诫自己安静的梦境中,成了宫中第一个活到六岁的皇子。
直到遇到朱由孝他才知道,原来这座宫殿中,有的孩子不需要安静也可以活下去。
那天从镜子后面钻出来的孩子叫朱由孝,是他的八皇弟,只比他小一个月。他沉浸在初遇同龄玩伴的喜悦中,没有意识到这一个月意味着什么。就像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他明明完美地完成了祭礼,母妃却变得更加忧心忡忡。
那间装满书的房间成为两个孩子秘密据点——在此之前,那是朱由孝一个人的据点。他的母妃给他安排了满满的功课,而他总是逃课,一个人躲在这里睡觉。而即使这样,他的母妃也从不会责罚他。听到这些时,朱由信惊讶地瞪大眼睛,心里满是羡慕。即便后来他知道八皇弟的母妃正是父皇最宠爱的郑贵妃,是那些染血秘谋的制造者,他心里也提不起恨意。他想,如果他是父皇,一定也更喜欢八皇弟的母妃。
八弟是个心胸宽广的孩子,他慷慨地将自己的地盘分给了哥哥,从此两个孩子便在这间巨大的书房中各自相安。
成祖年间曾编纂过一部叫《永乐大典》的巨著,这间房间里存放的,便是其中一部分,或许只是十分之一,或许更少。可即便如此,朱由信也时常觉得,这里的书他一辈子也看不完。
本来以他的年龄,是该有一位老师了。可他像被遗忘了一般,只是一个人在这幽暗的宫殿里小心翼翼地生长。
他读书时的坐姿很好看,即便是席地而坐,都坐得端端正正。看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用余光偷偷打量自己的八弟,一旦被发现,便会心虚地低下头。相比之下,朱由孝对哥哥的好奇则表现得更加主动和放肆,他会凑到哥哥身边,探头去看哥哥在看什么,然后又兴趣缺缺地跑开。经过最初的互相试探,两个孩子很快熟识起来。奇妙的是,安静的朱由信,却成了更爱说话的那个。
朱由信最爱看的书是帝王本纪,一知半解却乐此不疲。他活得怯懦而卑微,他的母妃也从未对他提及过储君的话题,他却无师自通地意识到自己本来的身份,以及未来的可能性。他崇拜地读着那些贤明君主的传记,想像自己有一天坐上那个位置时,会怎样做。他模仿着那些史书的语气指点江山,评价他的臣子们。尽管他根本不清楚大夏的疆域到底有多广大,也不知道朝堂里都有哪些臣子。
在那些汗牛充栋的书史中,好与坏通常都是很容易分辨的,而君王的失败往往并非由于能力不足,而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所以那时的朱由信天真的相信,即便他做不了最好的那类,至少不是最坏的。他想他一定不会宠爱妖孽,贪图享乐,更不会嫉贤妒能,残害忠良,他要爱护他的臣民,轻徭薄赋,对不懂的事情,他会虚心请教,听那些更有学识的臣子的意见。
无人打扰的书库是属于他的地盘,这样的认识给了他安全感,让他越来越有勇气去释放他被压抑已久的天性,而弟弟是他唯一的听众。
弟弟并非一个好听众。他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偶尔读书,读的也都是千奇百怪的书目。所以他并不能理解哥哥的宏图壮志。但朱由信也并不需要来自弟弟的意见,相反,弟弟的不学无术给了他某种程度的优越感,让他更加自信满满地指点江山。他甚至对弟弟有了某种程度的爱怜,他想,既然弟弟并不需要去肩负治国的重任,又是这样闲散的性格,那么,他以后一定不会像史书里写的那样,对兄弟赶尽杀绝。相反,他要保护弟弟,让他可以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弟弟最爱的书是一本描写西域各国的游记,他喜欢卷着舌头去念书里那些古怪的人名和地名,然后自己大笑起来。
另一本他最爱的书叫《一生所爱》,这本书装帧潦草,和书库里的其他书笔迹也有明显不同,它被摆放在书架的最上层,夹在两本厚厚的史书中间,书脊露出一小半来,像是后来才被塞进去的。
这本书引起了弟弟非同寻常的兴趣,书架很高,最上层并非他们可以够到的,于是弟弟理直气壮地指挥哥哥抱着他去够。这本独特的书同样引起了朱由信的兴趣,于是他不介意当一回人梯,用尽力气把弟弟举起来去够那本书。可当弟弟刚攀住书架的最上层时,朱由信却重心不稳摔倒了,年久腐朽的书架没有支撑住弟弟的重量,轰然倒塌了。两位皇子被堆成小山一般的书埋在下面。
朱由信艰难地从一堆经史子集中爬出来,他想,想不到这些看起来轻薄的书堆积起来的时候这般沉重,很多年后他才明白,沉重的不是书,是书写在书中那些真假难辨的历史。
三、
《一生所爱》引发了兄弟之间的第一次分歧。
这本书里所载的是本朝一位名为朱寿的大将军的丰功伟绩,它用夸张的笔法描写了朱寿对瓦剌人作战的种种事迹。曾让本朝深受困扰的瓦剌,在这位大将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他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即便只有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也能以勇武和奇谋取胜。他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肃清了边境,令瓦剌在这位将军活着的年代不敢再来寇边。
此外这本书不同于那些一本正经的史书,其中穿插了若干香艳事迹。这位朱寿将军的猎艳范围无比广博,比起自己府中的王妃,他更热衷于与民女、妓女、甚至孕妇厮混。更为逾矩的是,他春风一度的对象甚至包括男人,俊秀的书生和英武的将军都尽入他彀中。这本书以极尽渲染的笔法描写朱寿与他的男宠们的绵绵情意,细腻程度甚至超过战场上克敌的部分。
当朱由信和弟弟并肩坐着一起翻阅这本书时,都不可避免地感觉口干舌燥。这一年他们已经十三岁了,已经到可以选妃的年龄了。只是以父皇对朱由信的忽视程度,自然不愿提及这件事。而朝堂上忠心耿耿的臣子们,正在拼命阻止弟弟在哥哥之前选妃。也正是因此,这两位可以算作少年的皇子,才显得如此没见过世面。
朱由信很快强迫自己移开目光,努力平静呼吸和心跳,他非常肯定的指出,这一定不是正经史书,只是一本伪造成史书的坊间传奇。他以训诫的口吻告诉弟弟,作为一位正经的皇子,是不应该看这类毫无根据的话本的,只会被带偏了心性。
但是弟弟对他置之不理,和孙武、霍去病等前朝名将比,这位本朝的将军无疑更能吸引朱由孝,令他如痴如醉。朱由信才悲哀的发现,尽管史书上说,弟弟对兄长应该是尊敬且服从的,可这个比他小一个月的皇弟并不爱读书,所以也丝毫不具备这样的品质。
于是他准备用另一种办法说服弟弟。他通过多方考证,向弟弟证明这位大将军朱寿并不存在。这只是一个化名,他的真实的身份是本朝的一位皇帝,庙号“武宗”的那位。这位皇帝终其一生都梦想着御驾亲征,以至于做出自己封自己为将军这样的荒唐事。他出征的战绩并未见载于正史,想来并不如这本书所写那般彪炳。
可这个发现只让他的弟弟更加跃跃欲试,甚至眼睛都亮了起来,他对哥哥说:“原来当皇帝还可以这样,这才对啊。要是当皇帝都像你之前说的那样麻烦,那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又何必大家都去抢着做呢?我要当就要当这样的皇帝,到时候,我也要封自己当大将军。”
这句话给朱由信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直到此时他才清晰地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皇位,并不理所当然属于自己。他的弟弟,其实和他有一样的目标。
这领悟显然来得太迟。事实上,从那场有两位皇子同时陪祭的祭礼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储君之争就已经拉开了帷幕,并席卷了整个朝堂。他们的父皇,此时正忙于和一帮忠心耿耿或者说食古不化的臣子们对峙。他固执地打压着自己不喜的七皇子,甚至为此不惜委屈自己真正宠爱的孩子。结果就是,两位皇子都既没有读书,也没有选妃,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波里,最无所事事的人。
如果他们相遇的时候更年长一些,或许从最初就会成为不死不休的仇敌。可是当时他们太年幼了,等他们成熟到可以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彼此又已经太够熟悉了,熟悉到谁也不愿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如今这层纸终于被捅破了,似乎也没有掀起想象中的波澜,因为朱由孝轻描淡写地对他的皇兄说:“皇兄,我们又何必为这个问题苦恼呢?最后谁坐上那个位子,难道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吗?”
这句话真正把朱由信从幻梦中拉了回来。他悲哀的发现,弟弟才是对的。他此前一直相信,只要他够努力,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好。
可事实上,支持他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更具有君主的品质,只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名为“礼”的东西。“礼”在看不见的地方编制出纵横交错的网,不动声色地将所有人都束缚在里面。而他的父皇,也未必是多么宠爱弟弟,只是想从这张网中挣脱。
于是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弟弟,弟弟一边看着书,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想那么多有什么用,我只知道,如果最后是我坐上那个位置,他们谁也别想指挥我。”之后他又想起什么一般拍了拍哥哥,承诺道:“别怕,总之到时候我不为难你就是了。”
朱由信没有回答,因为他没有弟弟那样的自信。他和弟弟,不过是两个被推到台前的傀儡,手足都被丝线牵着,丝线被扯动的时候,便由不得他们自己。
四、
储君之争的结束和它的开始一样魔幻。
当那位手持木棒的大汉一路打向朱由信居住的宫殿时,竟然没碰到任何阻挡。话本上说写的那些大内高手、锦衣卫、影卫们,那个时候统统失踪了。朱由信像回到了童年的梦魇中,被恐怖支配的感觉再一次攫取了他,于是他忘记了逃跑和喊叫,只是下意识告诫自己:不要出声,不能被发现。
可与那些梦境不同的是,尽管朱由信确信自己把所有的惊呼都狠狠咽了回去。那头怪物还是发现了他,径直向他扑过来。梦境里从未看清的样貌瞬间清晰起来,怪兽的眼睛布满血丝,向外突出,堆积着黄色牙垢的牙齿参差不齐,门牙的位置缺了一块,这使得他嘴里唱着的怪异歌谣格外含混起来。他扑向朱由信的时候,露出一个狡黠的笑。之后这个笑便倒映在朱由信眼中,无限放大。
那一刻朱由信想起了《一生所爱》里的描写,“神挡杀神,佛当杀佛,万军辟易,直捣黄龙”,他觉得用这样溢美的词句去形容一个怪物显然不合适,于是他又想起了“千军万马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可这句同样不合适。
此时木棒带起的风已经打在朱由信脸上,怪物那狞笑着裂开的嘴里喷出中人欲呕的臭气,朱由信却还在想他的形容词。他看着那支高高扬起的木棒,觉得它的形状像一支船桨,于是他又想起了“中流击楫而誓曰,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这句似乎仍旧不合适,但它至少出自一本正经的史书,这让朱由信稍稍松了一口气,像完成了一项任务。于是他看着那支船桨向自己头上砸下来时,竟然感到一刹那的轻松。阳光照在船桨的边缘,幻出一道七彩的光,像船桨上被甩开来的水珠。
朱由信就这样沉湎在自己的幻想中,以至于当那个妆容寡淡的妇人忽然撞出来,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将怪物撞倒在地时,朱由信甚至呆愣了半晌才认出这是自己的母妃。母妃的打扮依然像个宫女,她从两年前就因为眼疾幽居深宫,连朱由信都很少见到她了。
她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血色,身体轻薄得像一页纸,谁也想象不到她是怎样把一位壮汉撞倒在地的,就像大家无法理解一个已经近乎失明的人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母妃倒地的动作把朱由信从幻想中惊醒,他最后想到的画面是一只老母鸡奋力飞上了树。
后来这件事成为支持朱由信那些臣子的重要论据,他们一部分在歌颂母亲的爱,另一部分将这归功于上天护佑,无论哪一种,都能成为一项不错的政治资本。
但此时朱由信只是茫然的看着他的母妃,他一直不知道母妃是不是爱自己,在此前的十八年,来自母妃的爱像死死捂住他嘴的那只手,在巨大的恐惧感中,让人无暇去感受那手上的温度。母妃软弱了一辈子,竟然会有如此勇敢的时刻,这让朱由信又震惊又迷茫。
他想自己应该感动的,可是那一刻他只有迷茫。母妃并不是因为受伤,而是沉疴之人熬干最后一滴灯油。朱由信没有从她最后的眼神里感觉到任何爱意,只有轻松。那是终于完成任务的无牵无挂,大约她如履薄冰的一生,唯有此刻是轻松的。
这次事件理所当然引起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那个行凶的人到底是不是疯子,朱由信清楚的知道他不是,因为那个狡黠的笑容太过意味深长。何况,无论是不是疯子,都需要查清他是如何出现在宫中的。
可父皇态度强硬地拒绝查下去,这态度更让群臣们确定陛下是在有意维护幕后的主谋,民意汹汹之下,父皇只得答应了另一项决议,七皇子立储与八皇子就藩。这些恪守礼法的臣子们前仆后继,终于又战胜了一次人君的私欲,这让他们欢欣鼓舞。
而朱由信在为亡母守孝,他纯孝的行为得到了又一波赞誉。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悲伤是真实的,却不止是因为母妃。史官对母妃的记载只有不足一页纸,而她临终前的英勇表现占了三分之二篇幅。这薄薄的一页纸,便是她留下的全部重量。她最后的谥号是一个“恭”字,一个字便道尽了她的一生。
八皇子朱由孝就藩的那天,出行的车驾从宫城一直延伸到官道尽头。无论是已经开始修造的府邸,还是赏赐的婚费,都十倍于寻常皇子规制,处处彰显天子对八皇子的宠爱。
朱由信跟在父皇身后,看着弟弟打马走远,大约行出百米,又别过马头,原地绕了三圈,向宫城的方向遥遥行了个礼。那一瞬间,兄弟两的视线相交,默默无言。
弟弟的就藩标志着朱由信的全面胜利,可他感受不到丝毫胜利的喜悦。那是一个秋日,秋风肃杀,天空显得格外高远。一夜之间,两个最血脉相连的人,便同时离开了自己。
朱由孝在宫城前伫立的良久,终于拨转马头,去追赶前面的车驾。他转身的动作像鱼尾划过一条漂亮的弧线,从此回归江海,无拘无束。
朱由信目送着车队渐行渐远,忽然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五、宫墙外的天地或许真的是属于朱由孝的大海。
在就藩之前,咸阳王朱由孝在所有人眼里,都只是一位轻慢骄纵且不学无术的皇子。即便是宠爱他的先皇,都并未对他的才干抱有过高期待。可就藩之后,他却如鱼得水,在短短几年内厉兵秣马,连战连捷——至少他呈上来的奏报是这么说的。
朱由信严重怀疑这些奏报的真实性,他想起少年时和弟弟一起读过的《一生所爱》,弟弟呈上来的奏报,情节和那本书多有雷同,连遣词造句的风格都极为相似。弟弟招至麾下的几员猛将叫做黑木、玛莎和古丽,这些古怪的名字也与弟弟用滑稽的腔调诵读过的那本《西域游记》如出一辙。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一封奏报提到了与罗刹国的骑兵交锋并取胜。可事实上罗刹国离弟弟的封地还很遥远,很难想像他们的骑兵可以穿过茫茫雪原和戈壁与弟弟的军队相遇。
更让他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朝中百官早已习惯了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满朝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些战报的真实性,反而有人提议应该一鼓作气,反攻罗刹国,这个提议甚至得到不少臣子的支持。朱由信惩治了那些狂妄的臣子,于是另一些臣子提议应该和谈,与罗刹国结盟对抗努尔哈赤的骑兵。
朱由信只得自己派遣密使去求证这些奏报的真实性,但是密使明确的汇报他,虽然奏报中提到的敌人并不存在,修辞也过分夸张,但咸阳王立下的战功是实实在在的。
咸阳王的封地附近的确没有南疆苗人或哥萨克骑兵,却有此起彼伏的流民之乱。此前派去剿抚的总兵们疲于奔命,徒劳无功。而咸阳王未费朝廷一兵一粟,就几乎肃清了整个西北境内的流民。
咸阳王的功绩让朝野上下一片欢腾,这甚至比之前的奏报更鼓舞人心。和遥远的罗刹国比,流民的威胁显然更为紧迫。而风雨飘摇的大夏江山,真的太需要一位英雄了。咸阳王的故事满足了百姓对英雄的所有期待,很快便被十倍百倍地夸大,在各个茶楼酒肆间口耳相传。他甚至被民间奉为战神,名字和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同列。
朱由信对这些花团锦簇的捷报依然持怀疑态度,何况他清楚地记得,本朝的藩王自成祖之后,并不具备募兵的权利。咸阳王所为无疑是逾矩的。但在一片赞誉声中,提出质疑显得不合时宜,且难免会让人误会他嫉贤妒能,容不下兄弟。
更让朱由信感到悲哀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在嫉妒弟弟。
在弟弟夺走他的全部宠爱,甚至逼迫得他们母子无处容身的时候,他表现出了相当的大度,然而那是建立在他自诩比弟弟强的前提下。那些支持他继位的奏折上,把他形容成千古难遇的贤明皇子,仿佛只要他继位,立刻便能重振朝纲,中兴大夏。溢美之词听多了,连他自己都信了,强者总是很容易宽容。
可登基以来,他的自信心正不断的遭遇挫折。他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听到的话,都是臣子们希望他听到的话,却并不接近真相。他想要亲贤远佞,可人之忠奸贤愚远不如史书上所写的那般易于分辨。免除一位不称职的官员很容易,可要找到更好的接替者却难得多。弟弟的成功更像是一种讽刺,让他醒悟自己其实并不具备识人的眼光,既然连自己最熟悉的人都无法看清,又如何去发现其他人的才华呢?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发现自己表现得越平庸,朝中那些赞美弟弟的声音就越大,曾经颂扬自己的溢美之词被用在弟弟身上,而这些官员和此前颂扬自己的,根本是同一批人。这无疑是一种委婉的抗议,他的臣子们在表达,当初选择他其实是一个错误。这让朱由信觉得自己成了彻底的失败者。
承认一个人比自己强真的很难,尤其当这个人一向被认为不如自己的时候。当朱由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嫉妒之心时,又对自己的狭隘感到失望。
嫉妒心最强烈的时候,他开始由衷地期待弟弟吃败仗,这样他可以宽宏大量地赦免弟弟,并收拾残局,来证明自己不比弟弟差。
六、
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却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到那个时候,局面早已崩坏到无可收拾的地步了。
那是十四年春,咸阳王朱由孝就藩后首次入京述职,那是他们暌违十五年后第一次重逢,带来的却是石破天惊的消息。咸阳王的封地咸阳城已经被流民攻破,整个西北都落入了流民的掌握中。比这个消息更令人心惊的是,在此之前,朱由信竟没接到任何相关的战报。
西北的确许久没有消息传来,但大家沉浸在对咸阳王武力的盲目信任中,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危机。咸阳王也曾发出不少求援的书函,却没有一封被天子收到,不知是全部被拦截还是有人刻意隐瞒。无论是哪一种,都标致着大夏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朱由信感觉所有的臣子都背叛了他,在局面已如此糜烂时,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真话。这样看来,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告诉他真相的弟弟,便格外亲切起来。
弟弟的脸上仍是当年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似乎真的把这次逃亡当做一次述职。对他而言,成功或失败,都并非大不了的事。他只是享受了一把当大将军的乐趣,玩够了,便又回来了。他甚至略带兴奋地对哥哥描述他是怎样从义军的十面埋伏下杀出重围的,他的属下黑木、古丽、玛莎又是如何奋不顾身营救他,巧妙的掩护他逃跑。总之,这次逃亡被他描述成一次英勇的突围,他对突围成功颇感自得。
弟弟九死一生的遭遇激起了朱由信由衷的爱怜之情,所以,他几乎立刻就原谅了弟弟弃藩而逃的行为,甚至自责自己没能及时接到消息去救援弟弟,让弟弟孤军奋战以至于山穷水尽。在弟弟成功的时候,他是那样嫉妒着弟弟,甚至恨不得他死。可当弟弟失败的时候,他心中反而又生出兄长般的柔情,想要保护犯了错的弟弟。
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这样充满责任感的人。只有在他能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面对如今的局面,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并非权力或者地位的丧失,而在于他的价值得不到认可。他的子民宁可去当流民也不需要他,这个现实一度让他灰心丧气。现在,终于又有一个人需要他了,这让他勉强打起一点精神。
一位藩王弃封地而逃实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为了维护弟弟的名誉,他制造了一场假死,宣布咸阳王在英勇抵抗,寡不敌众之后,又九死一生回到京城只为传递消息。在消息传出后,他便因愧对自己的职责自杀谢罪了。
这个事件将咸阳王朱由孝的声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人们普遍有死者为尊的理念。若是朱由孝不死,丢失了封地还好好活着的他,势必会受到各种口诛笔伐。但一旦他选择了以死谢罪,人们又纷纷开始同情他。明明非战之罪还以身殉国,这无疑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咸阳王从此成为悲剧英雄的代名词,成为大夏的最后一个传奇。
朱由孝从不在意自己的名誉,但是对哥哥做的这一系列事情,他也并没有表示反对。相反还饶有兴趣地参与其中,并自己为自己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因为他所崇拜着的大将军朱寿是溺亡,所以他也选择了在澡盆中溺亡,这是一种致敬。
从此,咸阳王朱由孝便在野史传奇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形象如此光辉,让身为天子的朱由信艳羡不已。
七
大夏王朝的最后两年,时间过得忽快忽慢。
当朱由信上朝理政的时候,时光倏忽而逝,他麻木地批阅着几乎一样的奏折,面对同一批臣子——他们甚至连表情都缺少变化。因为臣子们习惯从陈年的案牍中寻找奏折的范本,他收到的奏折甚至经常写错年号。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朱由信终于放弃了挑剔臣子的舛错,于是他收到的写错年号的奏折越来越多,让他时常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
朝堂上的气氛甚至可以称得上和谐,对臣子来说,一个吹毛求疵动辄问罪的君主显然比内忧外患更加难以忍受,所以,当朱由信终于变得宽容,朝廷上下变得一片和谐。
当朱由信和弟弟呆在一起的时候,时光又变得无比缓慢起来,像缓缓翻动的书页,能清晰看到里面的每一个字。
已经从历史中消失的朱由孝索性搬回了宫中,因为他的存在不可告人,他的皇帝哥哥将他藏匿在后宫中。兄弟两一起在少年时代的书库里,消磨掉了最后的时光。
朱由孝只比哥哥小一个月,但如今他看起来远比哥哥年轻。似乎在从历史中消失的同时,他也抹去了自己身上的历史,从此不受岁月侵扰。
朱由信和弟弟呆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渐渐便有了神秘妃子专宠后宫的传闻。于是史官感叹“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作为一个亡国的君主,朱由信的私德并没有太多可指摘的地方,这令后世修史的史官苦恼不已。这位神秘的妃子总算为他们找到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
在朱由信看来,与弟弟相关联的一切,都蒙着一层迷离的色彩,让朱由信时常有自己也置身于梦中的感慨。
时光像回到了最初,他们一起躲在黑暗的书库里,讨论是否错过了祭礼。
朱由信想,或许当初的自己从来没有走出去,而是选择了退回黑暗中闭上眼睛,之后便陷入一个长梦,至今也无法醒过来。
又或许,从来就没有过朱由孝的存在,当他看见朱由孝从镜子后面爬出来时,其实便已经置身梦境中了。
只是这梦境实在是太过漫长,长到已经忘了怎样才能醒来。
八
义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朱由信最后一次去见自己的弟弟,却意外地看到弟弟穿着一身新妇的吉服,凤冠霞披,风姿卓绝。他以为弟弟是想扮做女装逃亡,心里难免涌起离愁别绪。
其实他本来就是想劝弟弟逃走的,作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想混出城并非难事。可是当他看到弟弟已经做好离去的准备时,他又不免伤感起来,想着连最后一个未曾背叛他的人,也终于要离自己而去了。
可是弟弟妩媚一笑,“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试过了,唯独还没试过男人,等试过了,我就死而无憾了。”
这时朱由信才惊讶的发现,整个房间里的布置都变化了,一支又一支的红烛亮起来,光线变得暧昧而柔软,婚床出现在房间的正**,挂着正红的纱幔,喜被上绣着龙凤的图案。朱由孝便坐在床的一侧,目光灼灼地看他。唯有角落里那面巨大的铜镜没有变化,依然安静地立在那里,影影绰绰倒映着烛光。
震惊让朱由信从麻木中清醒了过来,他当然不可能允许此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发生。可是朱由孝的打扮实在太容易让人卸下防备,而且他看自己的眼神也太过温柔,竟让朱由信心软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发现自己已经想不起新娘的容貌。他从不敢沉湎于女色,以至于那些为他生男育女的女子们,他几乎不记得她们的长相。于是,新娘的面容便幻化成了弟弟的样子。
他迷迷糊糊地想,或许他安排弟弟假死,从一开始就是想把弟弟留在身边,他这一辈子几乎没享受过一点乐趣,也没有信任过什么人。他实在是太孤单了。
再后来,他便生出了一股自暴自弃的念头,他这辈子,从未做过任何逾矩的事,却依然走到了今天。结局左右也不可能更坏了,便逾矩一次,又如何呢?
这世间,堕落总是比克制来得容易。
最后,朱由孝问:“哥,你这一辈子,就是活得太要脸了,值吗?”
朱由信无言以对。
朱由孝便大笑着说:“反正我是值了,死而无憾。”
崇明天子朱由信登上煤山,山脚下的宫殿正在熊熊燃烧。从山上俯瞰,宫殿显得如此小,像一座小小的戏台,如今,戏台上的粉墨油彩正被火焰缓缓融化,一点点坍塌下去。
他最后看了一眼他生活了一生的地方,大概是因为从未从这个角度看过,坍塌中的宫殿变得无比陌生,似乎和他再没有一点联系。
于是他终于读懂了母妃最后的眼神,也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用死亡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尾声
崇明天子朱由信,庙号为“思”: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谋虑不衍曰思。常用于亡国之君,取追思哀悼之意。
至于咸阳王朱由孝,他的记载未见于任何一本正史,却活跃在各类野史传奇中。对于这个人物是否存在,看法历来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他如李元霸一样,是一个脱胎于正史又被演艺神话的人物,他的原型有可能是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
也有人认为,这个人物与朱寿一样,只是一个化名,而使用这个化名的,正是思宗朱由信本人。
发生或未发生过的一切,都被埋在厚厚的书简中,再无余音。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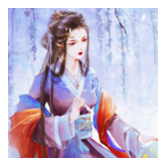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25 20:33:0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5 20:33:08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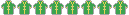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26 6:10:3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6 6:10:3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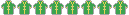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26 6:18:4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6 6:18:4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妙僧---
:---妙僧---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4/26 6:20:2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6 6:20:2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妙僧---
:---妙僧---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2/4/26 6:2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6 6:22:0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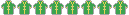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26 6:26:0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6 6:26:06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槛外清风
:槛外清风
 :指间三寸雪
:指间三寸雪
 :青青子衿
:青青子衿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2 届
:风云0-2 届





 Post By:2022/4/26 11:00:2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6 11:00:2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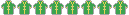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27 11:25:0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7 11:25:0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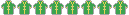


 :林寻
:林寻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27 11:31:4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7 11:31:4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1 届
:风云0-1 届







 Post By:2022/4/27 12:46:1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2/4/27 12:46:15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