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殇
楔子
城门早已被烧成黑炭,随着雨点落下“嗤嗤”地发出响声。
一个炸雷过后,聚在一起的乌鸦惊起,叼着或断指或断肠四散。
马蹄声后,一个人影从尸堆里爬起,手里拎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摇摇晃晃地找了块烂门板,拿着手里的东西啃起来。
一
众目睽睽之下,许太医竟失踪了。
赵始景杀到第七个人,才堪堪被祁总管拦下来。扔了刀,将身上的袍子脱下随手扔在大殿里。
他仍怒气未消:“历来是许太医为圣上诊病,如今却突然消失了,若是圣上病情复发,你们哪个有举荐?”
不仅一旁的御医,地上跪着的几个大臣也不敢说话。
祁总管低声报:“这段时间皇城内外都查得紧,带一个人出去很难,莫不是北域或东疆的人?”
赵始景看了眼京畿戍卫郎官,后者忙报:“来往城内外已一律盘查!剩余十七辆运尸车除棺材也都……”
赵始景挑着眉:“除?许太医可是救过我的命!滚下去,城内再查一遍,尤其是那群外史客馆!”
郎官忙不迭出去了。
与他擦身进来的殿检顾锦川进来,赵始景的眼睛立刻盯在他身上。
随着顾锦川轻微摇头,赵始景直接离了殿,祁总管跟在身后,看了眼顾锦川。
赵始景到了后园,见隆庆帝与柳贵妃坐在小船上说笑着,脸上一阵阴晴不定。
转身道:“让顾锦川来见我。”
祁总管朝远处的顾锦川招手,自己则退下去。
没等赵始景问,顾锦川先开口:“搜了几日,他不在城内,容予楼打探到从南门走了。”
赵始景疑惑:“南门?”
“应是躲在棺材里混出去了”顾锦川答。
赵始景恨道:“这帮饭桶!”
“秦王……”顾锦川刚说出口,赵始景已经拦住他:“找到许太医,其他的不要管。”
柳贵妃懒散地卧在榻上,看着赵始景批阅奏文:“前几日游湖,圣上还夸你来着!”
赵始景没抬头嘴里“哦”了一声。
“就不想知道他说了什么?”
赵始景将笔放下,来到榻前:“说了什么?”
“监国任重,让我多照顾你”
“没了?”
“没了!”
“那我明天要好好回禀一声,你到底有多照顾!”
祁总管在窗外轻咳时,已过了一个时辰。
赵始景起身:“知道了。”
随手将柳贵妃露在外面的肩盖上,柳贵妃嬉笑着一把把他拉回榻上,赵始暄挣开:“还有事。”
开了门,见祁总管搓着手:“这天怎么这么冷!少爷您得多加件袍子!”
二
雷誉等人被围在客馆。
自太子被刺后他们一直在这,外面守卫森严,有几次他溜出去时差点被发现。
赵始景帅军出城后,外面才看守得稍松了些。
宫里的隆庆帝是雷誉费了极大代价才从苗疆找来的。
赵始景养了四年,才将父亲所有的生活习惯学会,一点一滴,甚至连如厕的习惯都学了。
四年间,赵始景将北界关驻守的士兵轮换,又派人盯着赵始暄和赵始初的一举一动,直到春猎时才敢派人将太子袭杀。
雷誉带回北域和东疆出兵的条件:两国称臣,赵始景拿出两个州,做为共管。
赵始景暂定截铁地拒绝了,北域和东疆人不要妄想得到大奉的一寸土地!
北域和东疆人也不在意:“那就重开榷场,并把谢家人交出来!”
赵始景点头。
即便谢靖在北界关镇守,自己得了国后也未必派不出能够替换他的人,泱泱大国,最不缺的就是人。
三
赵始暄起兵前,檄文已到各个州府。
三十五个州府中,呼应的不过七个,但得知赵始暄带着北界关的士兵时,这个数字变成了十三个,而得知这些士兵不过是四年前换防过去的,这个数字又变成了四个。
甚至,在奇狼隘,赵始暄见到了六七种颜色的帅旗。
这些人只是在隘里躲着,见人来了就放箭,人走了又不追。
赵始暄看着两侧的峭壁和四丈厚的城墙,有些着急。
十二天后,林阿三赶回来,黝黑的脸上蒙上厚厚一层灰。
赵始暄跑到营门口,急切地看着他,林阿三递出一根木简后从马上栽下来,赵始暄伸手扶着,大声吼着“让开”,把他放在大帐里,随后才拿出木简。
第二天,奇狼隘的守将很是郁闷,对面的人像疯了一样,冒着箭雨冲过来,即便手里的藤盾已经被扎得像刺猬,盾后那些头上绑着白布的人还是不知死活一般冲上来。
不得不将后备守军派上来,准备了桐油后一支支火箭在天空划过一道曲线,留下地面上那些嚎叫声。
赵始暄亲自来到战鼓旁边,夺过鼓槌,一下下敲起来。
往前冲的士兵中间,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回头见赵始暄脱了上衣,用力敲着战鼓,嗷嗷叫着迎上去。
战鼓旁,一个将军一刻一刻将时间传到赵始暄耳朵里。
终于,他听到了自己想听的。
于是,正冲的上瘾的士兵突然听到了金铙声,一下快过一下。
撤?众人疑惑,然后从最后排开始,将盾放在地上,为撤下来的士兵抵挡箭雨。
奇狼隘上,俯身张望的将军们盯着下面不住地摇头:“这简直是送死,难道他们不知道?”
奇怪间,一个斥候突然跑过来:“不知从哪冒出一只队伍,把粮仓烧了,正往奇狼隘来。”
一众人立刻乱起来,甚至把军旗都倒了几根。
赵始暄站在鼓架上,仍然赤着上身,见几个将军浑身是血,怒气冲冲过来:“这么多兄弟扔在这?”
赵始暄指着隘上倒下的几杆大旗。
众人疑惑间,林阿三已经跑过来,仍旧喘着粗气:“未时,三刻!”
赵始暄点头,朝着下面一群杀红眼的将军:“等。”
奇狼隘南门。
众人望着远处滚滚黑烟,还未来得及骂娘,一阵战鼓声传来。依旧是头上扎着白布的骑兵袭来,后面huang色烟尘越来越浓,烟尘里偶尔露出几杆绣着龙的大旗。
这边还未消停,已经有人喊着北门开了。
众人反应过来时,一队扎着白布的人已经站在空荡荡的门口,背后的大门敞开着。
未进隘口,赵始暄的军令已经下来:“不得杀降、不得放火!”
将隘口守将抽了三十鞭,随后把许太医请来。
许太医断了一只胳膊,花白的胡须上汗珠滴滴哒哒往下流。
赵始暄有些不忍,但老头子执拗得很,劝了几句见他竟发起脾气来,只好作罢了。
奇狼隘里很多士兵并未散开,大部分去了大营里,小部分依旧站在隘口上,望着北方冲天的狼烟,握紧手里的家伙。
只是,头上都裹了白巾。
四
谢无极的马很快,林阿三捧着秦王赵始暄的令找到她时,她正缓缓地擦着枪尖上的血迹。
不过五十余骑,牢牢拖住北域人两个昼夜,最终堪堪斩了敌将。又看了木简,绕过了奇狼隘,在那群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奉军背后少了粮仓,赵始暄才得以进了隘口。
赵始暄留给她的是快骑,这支被北域人称为幽灵骑的快骑是北界关老帅谢靖花了十几年才凑齐的,以至于兀御魂被他们追了三百五十里后,硬是自己躲在一个羊粪坑里,让老婆和儿子乌善治引开五十里外才敢爬出来。
乌善治自此发誓,只要兀御魂活着一天,自己便不再回北域。
用他的话说,这个抛弃妻儿的男人,不配做为北域的统帅。
赵始暄看着满是风尘的谢无极,刚要说话,谢无极已经转身哼了声出去了。
赵始暄叹了口气,跟在后面上了隘口。
谢无极认真地望着北方。
赵始暄把自己的大氅批在她身上,看着她白皙的脖颈和乌漆墨黑的脸颊,突然笑了。
谢无极转头,白了他一眼,随机眼中露出哀伤:“你说,北域人到哪了?”
赵始暄知道她在担心谢靖,只能轻声说:“斥候还没回来,有消息我马上和你说。”
谢无极摇头:“他那么大年纪了,上次去收拢流民时还受了伤……”
赵始暄拉起她的手:“我还是派些人回去吧?”
谢无极摇头,她看着赵始暄:“其实,在北域这么多年,你也习惯了吧?”
赵始暄点头,随后又摇头:“也习惯,也不习惯。”
谢无极有些急:“其实,呆在北域也挺好的,远离那些弄权的小人……”
赵始暄叹了口气:“我哥也这么说,就藩这么多年,我也以为我已经习惯了。但北界关换防开始,已知道他们还是不放心,也不会让我活着。”
谢无极皱眉道:“那我就陪你出关,我们找个地方放羊,再也不回来!”
赵始暄笑着:“要不要再生一窝娃娃?”
谢无极认真道:“也好啊,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怎么都好。”
她的话让赵始暄有些不知所措,原本是想逗一下,但平日里聊这个事时谢无极每次都会红着脸啐他,此刻却无比认真地在等他的答案。
赵始暄无法回答。
就藩以来,他本就与谢靖直接有些隔阂,谢靖以为他是隆庆帝派来监视自己的,赵始暄则以为把他放在北界关,突然被北域刺客杀掉,也算是个不错的借口。
两人互相戒备着,又不能公开撕破脸,甚是尴尬。
但赵始暄在北域人手里拼死救出谢无极后,这种尴尬已经消失了,谢靖看着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皇子将自己的封地租给佃户,自己则每年除夕方才吃上点荤腥后,特地把从北域人那里夺来的羊肉送过去。
那时起,被北域人称为“公羊恶魔”的一小股骑兵穿梭在北域辽阔的草原上。
兀御魂就是迷迷糊糊被他们遇到后差点杀掉。
赵始暄并不知道他就是兀御魂,只知道这人家资甚重,抢了这么多次,终于遇到了肥羊的主人“肥羊”。
他和谢无极打着马放肆地追逐着。
但兀御魂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目标是羊,而不是人。
若是知道他只要乖乖地把羊交出去,满嘴的羊粪刑可以免去,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想法。
谢无极见他不回答,脸上的期盼变得黯然。
但她知道赵始暄要的不是天下,而是天下太平。
赵始暄出神,低声道:“那时我还未出生,但这里有我六位皇叔的血。”
他喃喃自语:“史书上会怎么写呢?为国捐躯?还是染病去世?”
回过神时,谢无极已经走了。
五
顾锦川已经追了几天,依旧不见许太医的踪迹。
他有些急躁,但更多的是无奈。
赵始暄的原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费了很大气力,顾锦川得到消息,有人在赵始暄的军营里见过一个独臂老人为伤患医兵,甚至将苗疆混进去的疫病都医好了。
那只手就是顾锦川伤的,但当时许太医的尸体被人抢了去。
许太医身边有人护着,顾锦川却看不出那人的招式,仅几个照面不仅带走了许太医,连顾锦川都根本无法近身。
许太医名不虚传,想不到不仅没死,竟还能到北界关。
至于为什么去北界关,自然是赵始暄或赵始初。
这事赵始景迟早要知道的,顾锦川不能不报。但想想赵始景知道这消息的后果,顾锦川有些头疼。
或许,民间传说的隆庆帝被人替换是真的?顾锦川不敢再想下去,也不想回皇城。
好在,他正在办另外一件事,隆庆帝的密旨——找一个人。
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先做,哪些事后做,顾锦川还是拎得清的。
如今盗匪四起,顾锦川杀了几伙劫财的人后,也换了行头一路沿着官道往北。
刀兵起时,南迁的人越来越多,破衣烂衫的孤儿寡妇随处可见。
偶尔能见到败下来的逃兵,拿着刀和匕首之类的抢些吃食,但毫无意外都被流民一窝蜂围起来丢了性命,身上的衣服也被拔下来。
运气好的被人丢在路边的深沟里,运气不好只能留在路上,甚至变成这群流民嘴里的吃食。
顾锦川背了一个竹筒,和流民们的方向相反,被几队官兵盘问了几次,只能扯了个谎胡乱回了。
人群中,有人和他擦肩,在他耳边说了句话,顾锦川便下了官道。
走了半日,一个驿棚里,顾锦川遇见了熟人。
那人正在喂牲口,一边的凉席上躺着一个人,另一个少年正一勺一勺喂药。
顾锦川初以为那牲口是匹马,但走近了才发现是驴,一匹差不多和马一样大的驴。
喂牲口的人抬起头,一柄长剑出现在顾锦川手中。
那人笑:“我真有些好奇,所有的黑鹰卫手里都是这么长的剑么?恐怕袭杀时候相当不便吧?那就是,各有所长?”
顾锦川冷冷道:“沈长河,你想知道?不如你和我回去,到时让你一件一件的试试!”
沈长河笑道:“这倒是不必了,我身子骨弱,经不起折腾!”
顾锦川如同一只大鸟般飞起来,催着内力在虚空中踩了几步,手里的剑劈直直地落下,但目标不是沈长河,而是席子上的人。
见他扑过来,喂药的年轻人抬手,破空声传来,顾锦川劈下的剑不得不收回来,人也硬生生在空中顿了下,翻身落在车前。
看着掉在驴粪上的药杵。
年轻人想要往前,衣襟却被人抓住:“秦南月,以后若是让我再见到那根药杵,我就杀了你!”
顾锦川又要往前的身子突然停下,朝席子上的人望去:“大……大皇子?”
秦南月将自己的衣襟抢过来,拿了根棍子将搅在驴粪里的药杵挑出来,指着药杵:“这是给你救命的!”
席子上的人显然外伤不轻,颤抖着指着秦南月,眼睛看着顾锦川:“你杀了他,我给你官升一级!割了他的舌头,官升san级!”
“赵始初,没你这样的,你救我一命,我救你一回,凭什么你又要人来杀我?江湖义气还要不要?大皇子的身份还要不要?脸还要不要?”秦南月有些激动。
沈长河始终没动,也不说话。
顾锦川又要说话时,小路上脚步声传来,一伙人已经到了。
秦南月已经回到赵始初身边,手里的棍子也换成了一把窄刃剑,嘴里嘟囔着:“沈老大,我就说把他扔下去,你这驴根本就不像能日行千里的样子,这回好了,终于被追上了!”
沈长河不说话,吃草料的驴突然回过头,鼻子喷着粗气,露出一口白皙的大牙,白了秦南月一眼。
秦南月看着驴,气势矮了几分:“特特特,我知道你是龙种,叫特。但是你也不能看着我们被人欺负吧?尤其是这里还躺了个龙种……你俩到底谁是真的?”
一人一驴互相看着,秦南月骂驴,驴则裂开嘴竟似在笑。
顾锦川等人愣在原地。
传说中的特?但他只想问问秦南月,和一头驴骂起来是什么感觉。
沈长河无奈地缓步走到赵始初身边:“别装死了,等下我一个人打不过的话,少不得要把剑架在你脖子上,若是一不小心抹了你的脖子,再想救活就难了。”
赵始初坐起身笑道:“难得让他伺候伺候。”
秦南月,骂声更大了。
顾锦川又要说话,沈长河一拍脑袋:“差点忘记,今日等你,有其他事。”
赵始初走过来:“你速回去,皇城客馆里有细作,这事需得你亲自办,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顾锦川愣住:“不放心?”
赵始初道:“许太医曾和我说过,你若是再偏一点,只怕掉的不是胳膊而是他的头了。”
顾锦川挥了挥手,身后几人离去。
见他没动,赵始初苦笑:“沈长河,你失算了。看看如今黑鹰卫见了皇子都不知道上前请安了,遑论他去救国?这世道真是乱了!”
沈长河不置可否。
顾锦川身后人却犹豫着,最终看看顾锦川丝毫没有要拜的意思,手里的家伙握得更紧了。
赵始初摇头:“看来,我还是躺下吧?免得动起手来碍事。”
沈长河看着顾锦川皱眉道:“人你找到了,但东西没在我身上。”
顾锦川摆手笑:“什么人?上次许太医被你救走了,这次挟持皇子,罪名更大了。江湖传闻沈长河从无败绩,我领教一下吧!”
沈长河走两步:“你确定?”
顾锦川双手握了长剑横着切出,沈长河身子矮下去,手指在长剑上轻弹,顾锦川的剑便斜着划出去,收剑后身子向前一剑劈下来,沈长河则往前蹿了几步,从黑鹰卫腰间拔出一支短剑,回身迎着顾锦川的长剑奔过来。
顾锦川暗自高兴,但不知沈长河用了什么步法,眼见得他只迈了一步,匕首却已到胸前,只觉得剑尖已经刺破了外衫,身上汗毛直立,脚下已经停不了了。半晌脚已经踏在地上,短剑却未曾再进一分。
沈长河收起短剑,在手里耍了个剑花:“剑不错”话音未落,被夺短剑的黑鹰卫腰间一沉,短剑已经归鞘。
顾锦川无奈,扔了长剑。
他越发确认,救走许太医的就是沈长河。
沈长河将长剑拾起,递给他:“可惜君子剑,落在屠夫手!”
顾锦川冷哼:“若是江湖人知道规矩,还需要我们?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朝廷与你们的恩怨已不是一两日之事了。”
沈长河撇嘴道:“有道理!不过,黑鹰卫的初衷,只是拱卫皇家,而不是变成他们手里杀人的武qi……当年大奉立国时,山河令主与大奉国君有过君子之约,所以才出手相救,也才有了大奉。”
顾锦川笑道:“既如此,你杀了我们就是了,然后再回你的江湖。”
沈长河摇头:“不杀你,是因为敬重你是忠臣,虽是愚忠……而且,不瞒你说,你算是黑鹰卫统领里,功夫最差的……。”
顾锦川:“……”
转头看着赵始初,躬身拜道:“大皇子……身不由己。”
赵始初叹:“只希望你的身不由己,是对的!”
六
乌云蔽日。
北域人已经第五次被杀退。
北界关城墙一片漆黑,显然是用桐油烧了几次。
兀御魂骑在马上望着高耸的城墙和城下已经填平了护城河的尸体。
谢靖到底留了多少人在城里?兀御魂始终未摸清楚。开战第二天开始,城里的探子尸体被陆续挂在城墙上。
有几个已经在将军府伺候了两三年,但却是被先挂出来的。
但兀御魂不着急,帐外的笼子里,还锁着一张底牌。
与兀御魂的从容相比,北界关内是另一个极端。
府里下人跑进跑出,但没人发出声音,乱中有序地完成自己手里的活。
王麻子等人不住地接到军报,但谁都没说话。
谢靖两眼满是血丝,满头白发有些凌乱,就着咸菜吃了一碗粥,边吃边低声问:“还没找到么?”
王麻子等人仍不说话。
“哑了?到底找到没有?”谢靖将碗重重按在桌上。
但回答他的依旧是沉默。
身边的谢长安忍不住:“还没找到!”
谢靖扔下筷子,起身到地图旁:“秦王到哪了?”
王麻子快步走过来:“过了奇狼隘,此刻应该到孟州了。只怕越往后越慢了,据说二十多个州举旗勤王。”
“好好好,那就等!我倒要看看兀御魂怎么破北界关!”谢靖打量着地图笑道。
王麻子等人欲言又止,谢长安快步走来:“军粮已经不够了。”
谢靖笑道:“放心,马上会有人来送粮,你们只管御敌!大丈夫当马革裹尸!”
听这话,王麻子等人只是低头,无人搭话。
待王麻子等人走了,谢靖脸上的笑消失,看着桌上的咸菜和粥,长叹一声。随即看着谢长安:“长生就是这个性子,不够沉稳,顺境时是好事,逆境时是缺点。”
谢长安跪倒,流泪道:“瞒不过您。”
“笑话,北域这么多年,除了你大姐,本帅怕过谁?”谢靖笑着,摸着谢长安的头,两眼有点模糊。谢长安的头顶温热湿润,随即被拉起来,谢靖拍拍他的肩膀:“你是沉稳得有些过了,若是和你大姐和大哥的性子综合一下,只怕我们还能守关五十年。”
谢长安抬起头,抹了把眼泪:“老帅放心,北界关姓谢,是大奉的!”
一夜。
北界关居然下起了雪!
早上谢长安跑过来时,谢靖等人已经在城墙上。
天地白茫茫一片,雪花大片大片地落下,随着风四散。
谢靖眉头紧锁,似乎要透过大雪看清北域人的动向。
片刻后,一匹马跑过来,马上伏的人大吼:“敌袭!”
七
越是往南,速度越慢。
过了奇狼隘,赵始暄最头疼的事终于发生了。
檄文发出后,赵始暄就已知道,十几年北界关的生活,终究抵不过赵始景在各州的威望和门徒。
甚至有几个北界关调回来的守将他都见到了。
只是过来请安后,便将将旗砍了匆匆回去。
大家都在观望,赵始景手里有隆庆帝,赵始暄手里有檄文。
真假无法分辨时,观望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都在待价而沽。
但赵始暄明白,即便看上去孟州之前有所阻碍,但过了孟州的千里沃野,才是赵始景最后的依仗。
他需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皇城,因为身后的北界关。
谢靖和他都知道,北界关是最薄弱的点。
两人为此争执过多次,为了比他南下,谢靖让谢长生出关袭扰北域,为他和北界关争取更多的时间。
去年这时候,谢长生还被谢无极扯着耳朵喊饶命吧?
北域的路谢长生极熟悉,即便有惊险,他应该也能全身而退,然后整装再出关。
谢家三代守着北界关,守着大奉。
正要去看看谢无极时,她已走进来了,坐在赵始暄对面。
赵始暄帮她理了发鬓,拿出个簪子:“上次长安弄丢了,我托人带了一只回来,一只没机会给你。”
谢无极没接,赵始暄只好放在桌面上。
“你若是走,我绝不怪你”赵始暄看着她。
谢无极摇头:“没事,只是有些心神不宁。”说罢,转身出了门。
赵始暄见她走了,刚要把簪子收起来,谢无极已经一阵风似的回来,随手在桌子上捞起簪子又出去了。
八
云梯已经搭在城墙上。
梯子尽头的钩锁直接钩在城墙上。
不过数息,王麻子探身出去时,一把刀已经劈过来,躲闪不及时被一刀划在脸上。
嘴里骂了声,将人劈下去后,转身吼道:“不对劲,这些人不像是北域人!”
谢长安等人疑惑了下,随后从梯子上拽下一人,一刀劈下去,猛然见了那双光着的脚,随后喝道:“东胡人!”
东胡人世代住在山里,跋山涉水和上树的功夫了得,尤其十五岁以后,反复用松香将脚裹了,再放在沙里打磨,便于攀登。很多富人专门雇佣他们采摘云际果为朝廷纳贡。
大奉建国时,虎贲营整整一万三千多人在东胡被灭,最后放火烧了近两百里,才堪堪将东胡打服。
越来越多的东胡人已经上了墙,顾不得掀梯子,王麻子等人只能先对他们动手。
谢靖弃了剑,抄起斩马刀便冲上去。谢长安没拉住,被他带得往前踉跄了几步,堪堪躲过一刀,已将自己的长匕首拿起来,三棱的匕首直直捅进那人心窝里,喷了他满脸的血。
很快,这次突袭便被击退了。
谢靖找到谢长安时,他正骑在一个东胡人身上,手中的匕首将那人扎得满是窟窿,刃间在他身下“当当”地凿击着地面。
谢靖抓着他的肩膀用力按着,谢长安红着眼睛,谢靖竟搬不动他。
良久,王麻子等人合力将谢长安制住,浑身上下摸索着是否有受伤。
谢长安才扔了匕首,倚在垛口大口喘着粗气。
众人清理了城墙上的尸体,大雪依旧在下,没有停下的迹象。
大奉贤安十五年,东胡人勾连北域,是时九月,大雪。
足足一天一夜后,雪终于停了。
北界关里,士卒们穿着几个月前刚到的寒衣,冻得只打寒颤。
王麻子抓了一把,愤恨道:“赵始景这个王八蛋,都是芦絮!”
谢长安用刀划开,白花花的芦絮间还杂着芦梗。
都在大骂时,谢靖突然起身,连大氅和靴子都未来得及披上,推开门跑出去。
九
军营里甚是热闹,到处都是埋锅造饭的热气。
赵始暄小心翼翼地将地图折起来,放在自己的军印下面。
赵始初拿着一根木简,呆呆地出神。
赵始暄见他皱眉:“过了孟州便到皇城了,应该高兴才是。”
赵始初道:“北界关……下雪了。”
赵始暄一愣:“九月,这么早?”
但他突然站起:“下雪?消息可靠?”
“信鸽三天前收到的消息,林阿三刚到,是真的。”
赵始初思立即起身大喝:“传令,全军带三天的干粮,火速开拔!督粮官跟上,迟了时辰,当斩不赦!”
随即对赵始暄道:“秦南月和沈长河带人过去了,但愿……不晚。”
赵始暄脸色惨白:“临行时,谢老帅说过,北界关可守五个月,除非……”
“除非下雪,历次北域人攻城,都是雪天,若不是谢老帅帅军抵挡,只怕奇狼隘以北,都是北域的了。”
赵始初继续急道:“无极也回去了,若是北界关和她有事,你……。”
赵始暄边收拾边道:“带兵最忌将帅犹豫,眼下能救他们的只有我们!”
皇城近在咫尺,即便攻不下孟州,也可以绕过去。风头正盛时,各州府也都在观望,此时若是驰援北界关,这些摇摆之人定会倒向赵始景。
历代建国均是从南往北,由北往南者均未建功。
即便是退回去守住了北界关,赵始景登位后必然会出兵。
扼住奇狼隘,划地而治?这个念头刚升起,马上被他按下去。
但让他舍弃谢家和谢无极,他也无法做到。
谢老帅一辈子经营北界关,若不是他支持,只怕自己在奇狼隘便已再难进寸步。
谢无极等他答复的样子,是他从未见过的。
这个让北域人都头疼的女人,便是除夕和自己谈心都穿着一身戎装,甚至卧榻旁都准备了一副铠甲和一根枪。
她只会在战场上用枪把敌人的脑袋砸开花。
如果这也算绣花的话。
唯一能证明她是女人的,除了像她娘一样漂亮的脸以外,仅有一根簪子。
那是赵始暄刚认识她时送的。
做为还礼,她把他摔了个七荤八素。
然后红着脸道歉。
若是没有太子的事,他宁愿舍弃王爵也会带走谢无极,但此刻?
赵始初仍在犹豫,他看着赵始暄,想到一个办法。
赵始暄皱眉:“你想都别想!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州与我们遥相呼应,当断则断!我拍拍屁股走了,北界关能跑得了?老帅能跑得了?”
“那就分兵,你先去北界关,我退回奇狼隘守着!”赵始初认真道。
赵始暄摇头:“来不及,我已经安排好了。若是她要交代,我便给她交代。”
赵始初咬牙道:“开拔!”
两人出了帐,卫士跑过来大声道:“大皇子……那驴……那驴……”
赵始初疑惑,只见一头比马稍小些的驴溜溜达达走过来,嘴里叼根萝卜,眯起眼看着他。
赵始初摊手:“我……没骗你吧,这里的确有萝卜吃……”
十
北界关的城墙上,满是冰。
东胡人便是脚上长了刺,只怕也爬不上来。
本是应该开心的事,此刻谢靖却高兴不起来。
王麻子等人不解,跑过见谢靖满面愁容,不禁问:“老帅为何闷闷不乐?”
谢靖起身,竟似老了十岁,看着王麻子:“今晚你们收拾一下,去找秦王吧。”
王麻子疑惑:“在这挺好的,为何要去找秦王?据说他们马上要过孟州了,若是顺利,再有十天即可到达皇城。”
谢靖叹道:“只怕,北界关坚持不了十天!”
王麻子急得乱转:“怎么回事?难道大帅要降?”
谢靖怒道:“你放肆!让你去你就去,哪里还干啰嗦?”
王麻子坐到地上:“不走!大帅不把话说清楚,我哪都不去!砍了我我也长在这地上!”
半晌,谢靖突然笑了:“好样儿的,小子!”
北界关原本城墙原本只有三丈宽,如今已达十丈有余,原本城墙是用烧透的砖砌成,但谢靖到后发现只要每次雪尽时,城墙冻了又受暖,竟出了裂痕。
不得已,在原来的墙外和墙内又加厚,一层裹一层,里里外外已经有七八层厚。
前几天用桐油浇后,突然降雪,为了防东胡人又泼了水结冰,若是天突然转热,只怕城墙要一层层揭下来。
没有城墙的北界关,在北域战马的铁蹄下,简直是如履平地。
王麻子不再说话。
谢靖平淡道:“你若改了主意,今晚还可以走。”
王麻子嘿嘿笑道:“北界关是谢家的,也是大奉的!”
第二日,天气果然热的厉害。
王麻子咒骂着,登上城墙。
关外不远处,一座铁笼,笼子里坐着一个人。
城门开了个侧角,一骑疾驰而出,到了笼子附近看清了里面的人,急急回头,马鞭刚落下,连人带马已被人放了一箭,跌下马来。
那人爬起来往回跑:“是……少爷!”
北界关的少爷,除了在府里的谢长安,便是谢长生了。
谢靖跑上来,望着关外的笼子。
王麻子派人出去接时,谢靖却摆手:“任何人,不得开城门!”
“老帅,那是……”
“一个俘虏而已,我知道”说罢,他自下城去了。
王麻子跟在后面,谢长安也跟在后面。
谢靖进了府,握紧了拳锤在桌子上。
血从指间流出,竟是他的指甲嵌在肉里。
王麻子跪倒:“放我出去,不必开城门。”
谢靖不说话。
谢长安则拉起王麻子:“不必了,这是他的选择。”
王麻子愣住:“难道你们见死不救?”
“若是开了门,北界关就废掉了,大奉再无屏障。”
王麻子瘫倒在地,捶地痛哭起来。
谢靖摘了墙上的弓,谢长安欲拦,但手抬起一半又落下去。
十一
赵始景看着战报。
“到孟州了?这哥俩还算有本事。”
几个大臣笑道:“三十一府州已有二十七州在勤王路上,想必他们到孟州前即可到达。”
“另外,圣上已下达旨意,头功者,封侯!”
赵始景点头:“圣上平定天下,虽是近年来不再带兵,但深谙其中道理,即是有重赏,各位当争头筹,为国分忧,也开宗立府。”
众人谢恩,正要议论时,赵始景瞥见门角处露出一抹绿裙。
柳贵妃知道他有事,若不是有急事一般不会到前厅来。当下起身:“您怎么过来了?有事打发人来就是了。”
柳贵妃隔着面纱轻笑:“方才游湖,钓了几尾赤鲈,圣上让我送过来,给别人他不放心。”
赵始景忙接过来,躬身:“近日风冷了,请圣上和贵妃保重。”
柳贵妃点头:“皇子忠孝仁义,方才圣上还在和客馆各位”
“客馆的人?”赵始景皱眉。
“好了,送到了我也该回去了”柳贵妃笑着。
“把前几日新做的糖糕呈给父亲和贵妃”赵始景回身朝祁总管道。
客馆的人赵始景都见过,但除了雷誉外,“隆庆帝”是没见过其他人的。
赵始景有些不安,但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不过第二日早上,当着众朝臣的面,隆庆帝因怠慢他国使节严厉斥责了他。
赵始景不敢争辩,只能请罪。
隆庆帝黑着脸:“两个逆子未除,你却忙着笼络那些州府?”
这句话,让跪在地上的大臣们皆是惊到了。
赵始景眯着眼盯着隆庆帝,后者也盯着他,俩人互不相让。
好一会儿,赵始景才跪倒:“臣愿领兵,讨逆!”
隆庆帝起身拂袖,冷哼道:“难堪大用!”
祁总管看了赵始景一眼,低头跟着过去了。
顾锦川回到皇城,径直被隆庆帝喊了过去。
这个杀戮一生的帝王正在衰老,样子比顾锦川上次见到时更憔悴几分。
跪拜后,隆庆帝只留了他和祁总管。
对他的要求是,客馆内的使节,一个不留。
顾锦川有些意外,前几日才听说为了他们隆庆帝才责骂了赵始景,如今却要全部杀掉?
“若是全灭了,只怕北域和东疆……”
“另外,派人去找秦王,说我回来了。”隆庆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传到他耳朵里。
顾锦川忍不住抬头,看着虽然衰老但眼神里迸发着愤怒。
十二
孟州城已被团团围住。
赵始景坐在城里,一只只飞鸽放出去,却无一只飞回来。
开城逃跑的将领也越来越多。
身边只剩下六七人兵丁两三千时,他再也忍不住了。
索性把城门开了,自己戎装骑了马。
赵始初和赵始暄站在对面,几人不过十丈左右距离。
“大皇子背着谋弑储君的罪名,竟还能打着勤王的旗号,当真是好笑!来来来,诸位看看,这个骑驴的家伙就是鼎鼎大名的大皇子了!”赵始景指着赵始初。
“如今是你监国,只是不知道你身后的人是否知晓,宫里的圣上,已是被你换掉了!此,第一罪!”赵始初大喝。
“败坏人伦之礼,与柳贵妃沆瀣一气,不忠不孝!此,第二罪!”
“勾结苗疆人,猎场刺太子!此,第三罪!”
赵始景大笑:“圣上如今正与柳贵妃泛舟皇园,颁圣旨赐我监国,想必是你二人趁此机会起兵造反,这种借口真是可笑!”
“猎场刺太子?天下人皆知,太子薨后,你逃亡北域,我出城寻药,圣上才转危为安,赵始初,太庙你已被除名,如今只是戴罪的庶人!”
“你不知道吧?那药方,本就是许太医传下来的,那其实不是治病的药,而是让人假死的!”
赵始景又待说话时,赵始初的卫队中走出一位老人。
赵始景皱眉,指着老人笑道:“赵始初,你刚刚说什么?我换掉了隆庆帝?那你这位又是何人?”
祁总管过来搀扶着老人,老人向前走两步,轻声道:“飞熊,是我。”
十三
军报。
北界关一片废墟,出关不远,一个笼子被北域人派人守着,谢靖和谢长安两人站在左右将笼子护着。
笼子里的人身上一根箭,穿透了左胸,但那人脸上竟在笑。
笼子的旁边,是一块牌子,立牌人是兀御魂。
尾
赵始暄登位,但不过四天后,便称病。
谢无极看着眼前人,任凭他苦苦哀求,只是拨转马头,一人一枪缓缓北去。
她说,北界关是谢家的,也是大奉的。谢无极是谢家的,但不是皇帝的。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山河令
:山河令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33-1 届
:风云33-1 届
 Post By:2024/4/16 20:08:45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16 20:08:45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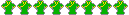


 :大叔
:大叔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5 届
:风云0-5 届











 Post By:2024/4/17 11:40:2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17 11:40:2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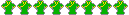


 :古灵精怪小天使
:古灵精怪小天使
 :如意聚宝盆
:如意聚宝盆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3 届
:风云0-3 届





 Post By:2024/4/17 16:21:5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17 16:21:59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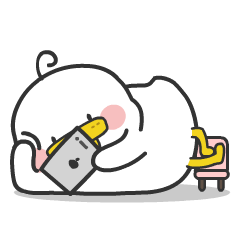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525-0 届
:风云525-0 届













 Post By:2024/4/17 23:33:5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4/17 23:33:52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