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情不知所起,一住而深--赠花慢儿
◆陌上尘◆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梅边雪正在皇成北街的一个小院子里看院。牙子满眼期盼,这买卖结束后,老婆孩子的月钱就有着落了。刚入夏的院子,不算轩敞,却彼为整洁,长条青石铺地,犹如皇城的坊市,鳞次栉比中,带着赏心悦目之美。院中有一棵桂花树,绿油油的枝叶错落有致,伸展至墙外,想来,秋天必是一番茂盛之象。
彼时,庐陵王曾说,当桂花开时,他在院中的竹椅上铺一条薄毯,角上用诗书压着,梅边雪从厨房端来热气腾腾的米糕,在这个雅致的小院中,吹风赏景吃米糕,真是惬意。当时他这样说话的时候,嘴角翘的弧度连他自己都不知自。
梅边雪伸手给了牙子几文赏钱,她关上院门的那一刻,仿佛想把所有的前尘都关在院中,任由它在这个潮湿的院中发霉腐烂,直至被这个尘世遗忘。
她只是十二宫的一枚棋子,入宫三年,苦练舞艺,琴棋书画渡着春秋。如今山河破碎 ,家国兴亡,朝中的二派却各执一词,分崩离析。她拿着圣密旨,笔迹劲瘦蛇舞,却似千斤重担。
渡口边,折柳送别。隔着雾蒙蒙的帘幕,梅边雪眉若远山,真是千金一笑腰肢袅。
撑篙船夫拉长了调子——船歌在碧波中渐行渐远,庐陵王眉间萧瑟,接你回来这四个字,被起早市的叫卖声冲淡,一切又热闹起来。
◆浅吟唱◆
梅边雪设想了一万种和花慢初见的场景。红烛昏沉,初夏的雨时缓时急,一会嘈嘈切切,一会润物无声。芭蕉叶在窗棂外随疾风飞舞,想来明日不知会有多少残红满地。
烛心剪了又剪,等了他整整三天,却还是不见他踪迹。
她对他了解甚少,只知年少成名,一直镇守边疆。近日被皇城急召回宫,却只是要为她赐婚。不待见她也是情有可原。
而她,只是带着细作的身份来到他身边,偷取虎符,军权合一,这是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这样一等,便等了一月有余。虽然在花慢府中终日惴惴,但吃穿用度,却是最好的。
其间,丫寰还送来了望江楼的酥饼,这是她最爱的零嘴,儿时,父亲只知攀附权贵,而母亲每日里也是对她冷淡之极。唯一的一次,她负气出走。她来到江边,小小的年纪,在黑暗中听着江浪拍打着礁石,胸中竟生出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气。当母亲找到她时,贴着她细嫩的脸蛋,她感觉到了濡湿,那是她的眼泪。回城的时候,给了她一包望江楼茶楼的酥饼,油渍渗透了包纸,甜香扑鼻。从那以后,只要她舞艺或棋艺,有所精进的时候,母亲会赏她一些她喜欢的东西。而她,很乖巧听从她的安排,入十二宫,学习作为细作要掌握的所有技能。每一次得到赏赐,她就觉得母亲是爱她的。
端午前一天,她像往常一样百无聊赖在院中自己与自己对弈,这样挺好,赢半局,输半局,方寸间,一个人经历了成王败寇。
直到一个纤长的身影,遮住了棋盘上的光影,她才惊觉对上一双深邃的眸子,剑眉星目,薄唇轻抿,盔甲着身,大气磅礴。梅边雪的心似烛焰漏了半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笑了笑,坐了下来,执棋与她对弈起来。直到晌午时分,两人在棋盘上金戈铁马,杀得难分难解,梅边雪终究还是输了半子。抬起头,花慢眉间都是笑意。
◆死别离◆
草木还是在生长,转眼间,凌霄爬上了藤架。而每隔三天的清晨,折下的凌霄花会挂在对面酒楼的窗棂上,这是组织催促的信号。
而花慢,脱下战袍,着了青衫,竟与她不紧不慢地过起日子来。晨起,他会陪着用早膳,上午,他看书,偶尔抬起头,看她娇俏的身影荡着秋千,嘴角含笑。黄昏时分,听着城外寺庙钟声响起,他还会亲自去厨房做了酥饼出来,她吃第一口时,很是讶然,味道和望江楼的差不了几分。他笑道:经常行军,也习了一手厨艺,如今有了用武之地。她躺在竹椅上,恍然间,这样的画面,庐陵王带她第一次去畅院的时候描述过。如今望着眼前这飘逸的身影,是梦是幻,她一时竟然分辨不出。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翻过无数次可以翻寻的地方,却找不到虎符。
而他,照常如此,陪她临摹,陪她下棋,也跟她讲一些军中的事。甚至在秋天的时候,为她糊了一个风筝,带着她去了城外。秋风如丝,她奔跑着,笑着,风筝飞在蓝天上,她的心却一下子湿润了,仿佛十八年来,她第一次认识自己。那是一种叫自由的东西,可以没有着落,但心和天融在一起的时候,心底里的晦涩都被划开,随着那丝丝的风,一丝丝被抽走,只余下明亮和快乐。
她在光阴里偷生,享受着片刻的欢乐。那一晚,梅花早早地开了,沁人心脾的暗香满溢在每一个角落里,似乎无处不在,当你要寻找它来的方向时,却又找遍寻不到。
她还折了几枝梅,置于瓶中。黄昏时分,飘起了零星的小雪。消失了半月的花慢回来了,而且在房中备了酒。桌子上,是她遍寻无果的虎符。她饮了一杯酒,热酒下肚,心中却是悲凉。原来终究是一场梦,时辰一到,就会醒。
他握着她的手,指骨分明,却暖暖的。他笑着说,其实他早就认识她。十三岁那年,十二宫的梅园,梅边雪因为被罚,在雪中跳胡旋舞。天地茫茫,万物寂寥,他经过那里,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跳舞,梅花初开,那红色的身影分不清是衣还是花,不停旋转,跌落,却一次次地爬起来。他看着她,最后脱掉了鞋子,一双粉足如点点樱花,在雪中盛开,他忘记了前行,只记得一颗心被永远羁绊在那片雪中。
他知道他来的目的,这几月的光景,容他安排好他的兄弟。因为他知道,庐陵王不会善待他的同僚,那是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大势所趋,现在是他交兵权的时候。而与她相处几月里,圆了他一生的梦。他一直爱着他,从十三岁开始。
而且他告诉他,安排梅边雪嫁他,是庐陵王一手策划。因为他的眼睛,只要遇到她,就不自觉地忘记了来路,爱一人秘密,怎么可能只深藏在心里,所以庐陵王懂,安排她过来,是最合适的。
◆关山月◆
关外的陵江渡口,庐陵王策马奔来。隔着飞扬的尘土,梅边雪竟然拼凑不出他的音容笑貌。他纵身下马,跌跌撞撞奔过来。驿道边,风幡招摇,冷洌的北风刮在脸上,竟丝毫不觉疼痛。
梅边雪眼望着蜿蜒的河道,从此,这陵江的水底,便永远沉着她的一颗心。
庐陵王站定脚步,却终究停在三步之外。几步之遥,却隔了千山万水。
怎么?当初在皇城渡口说接我回来,如今还是这四个字吗?
庐陵王仿佛被什么击中,他伸了伸手,却还是颓然放下。他看着她瘦弱的背影远去,四肢百骸似被针扎一般,密密麻麻的疼痛汇聚到心脏。这风还是这么凉,凉到整个人都在发抖。
残阳如血,关外的黄沙也敌不过经年的风霜。梅边雪游荡在这荒芜的关外。她心里终究明白,当她拿走虎符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生的离落,她以为,她还可以看到他,亲口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可是她亲眼看到了虐杀的残酷,他那些不服从的部下,头颅被砍下来,扔进了黄沙里,雪落下的时候,掩盖掉了一切。
她以为,她一个人来到这关外,自我放逐就可以救赎自己,当她听到花慢离世的消息时,她的身子如同置身于井底,外面呼啸的风声,都是如此的模糊。
她忘记告诉他,春天的时候,她愿意去陪他再放一次风筝。


论坛也知道我爱你。这一次当一回我的花将军,我的屠龙英雄。

这也太赤果果了
前排,边雪,写的一首好字
 开心玩,周一会有点忙,空了再来灌水。
开心玩,周一会有点忙,空了再来灌水。
这也太赤果果了
 对着别人我不敢,对着花慢儿,我可以很 豪气地说,我很耐她。
对着别人我不敢,对着花慢儿,我可以很 豪气地说,我很耐她。
 对着别人我不敢,对着花慢儿,我可以很 豪气地说,我很耐她。
对着别人我不敢,对着花慢儿,我可以很 豪气地说,我很耐她。
有人耐有人稀罕的感觉真好,去忙吧,忙完再回来开心开心
可惜没有我

等你挂了给你写 ,但还是不要挂,活成小强。
,但还是不要挂,活成小强。
等你挂了给你写 ,但还是不要挂,活成小强。
,但还是不要挂,活成小强。
那我怎么都是赢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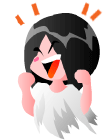

我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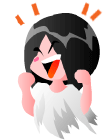
找她要蛋糕!要很大很大的那种!

找她要蛋糕!要很大很大的那种!

败家的,不留点土给我埋埋么
你挂了给你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