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收到新买的五本书,全是迟子建的。拿到后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一本散文集:《光阴于低头的一瞬》,边拆边笑:我这真是没读过什么书,盯上迟子建不放了。
其实书架上还有一些没拆封的书,很多作家也是一直喜欢的。只是最近重读迟子建,又唤醒了心里沉睡已久的对读书的渴望。大概,那些对她文字的热爱,源于对一个干净的、纯真的,而又充满温暖和爱的灵魂的渴望。渴望是一面镜子,照亮自己,感动自己。既然喜欢,就去热爱吧。
翻看目录,看到一篇《萨尔图的落日》。
萨尔图(区),是大庆市的前身,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往前可以追溯为清朝蒙旗杜尔伯特的游牧地,它的蒙语意为:月亮升起的地方。这个沾满了日月灵气的名字,从小就根深蒂固地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念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就像自苍茫黑土地上缓缓升起了一轮明月,心底荡漾起温情。
文章提到大庆市名字的由来,从这块黑土地奇迹般地开采出第一口油井,为国家甩掉“贫油国”的帽子,再到六十年辉煌后的油城面临着艰难的转型,这些,就像萨尔图的落日,它从不会萎靡不振,而是带着一股豪情,蓬勃、热烈,在天地间挥洒最后的光华,欣然与黑暗赴约!
今年冬天,我回故乡过年。
大庆地广人稀,道路宽阔,很少出现其他城市常有的堵车现象,在这里,会觉得天地开阔,胸怀敞亮。
每每往返于父母家与长姐家时,都要经过一段又一段人流稀少、车辆迅疾,有点荒凉的道路。沿路两边的行道树多是杨树,还有一些低矮的灌木,它们身体瘦弱,枝干稀疏得像纤细的四肢,颜色灰突突的。那是一种妥帖的,温暖的,甚至是亲切的陈旧感,即便是雪花飞扬的时候,都不会让人觉得凄清和孤寂,会让人想到散发着干草气息的落日。这个时候,落日、雪花、树木,是一幅黑白画里最和谐的景致,它们如同泛黄的老照片一样,勾起无数童年的回忆。
冬日里最安静的是树木,最灵动的是雪花和月光。
立春过后,我在故乡迎来了两场小雪。
那夜天光明亮,直透过薄薄的窗帘。我拉开窗帘,推开窗户,一汪月色如泉水一般涌入,带着丝丝缕缕的凉意,那是在潮湿的南方难得一见的清澈和甘爽。不知道在窗前站了多久,雪花纷纷扬扬漫了过来,落在手心柔软而温暖。一会儿功夫,地面就起了薄薄的一层霜白,月亮虽然被蒙上了轻纱,却不遗余力地把光华洒下来,映得地面越发地洁净。
记忆里的雪比这厚重,一脚下去可以没脚踝的那种。下雪的时候不冷,雪花像棉絮一样让人有想拥在怀里的感觉,但是它多调皮啊,还没等你捉住它,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多的雪又在你身畔飞舞起来。
融雪的时候最冷,风停了雪也住了,天地间白茫茫冷得剔透,我和两个姐姐在有月亮的夜晚跑出来玩。二姐用单车载着长姐在后座,而我则在车速并不太快的时候,窜上车前梁。那时我七八岁,瘦瘦高高,灵巧得很,总能像一只燕子一样,又快又稳地落在电线杆上。大概是有雪的缘故,有一次我刚窜上车,车子猛地振动一下,然后毫无抵抗力地“嘭”地一声摔在地上,我们三个滚在雪地上,哈哈哈地笑个不停,后来干脆躺在雪地上。雪后的月光无比洁净,照在人身上有一种梦幻的温柔的感觉。天地间一片静默清澈,让人忘记了寒冷,我们哈出的气像一条条银龙在空气中盘旋,倏忽间就飞上了天。
那时最高兴的事是去不远处的食杂店买零食:一包五香瓜子、一小包无花果,瓜子吃一颗满口生香,无花果酸酸甜甜舌底生津。
直到今冬回乡,和姐姐们一起喝茶吃茶点的时候,还说起儿时的美味,那时几毛钱一包的零嘴犒劳了我们的味蕾,满足了我们对天下美食的所有憧憬。后来吃到再多的美食,也不如儿时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
离开家乡多年,友人笑称我是古诗词里的游子,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即便在“车马”都不慢且随时可视频联系的今天,这话听起来还是会唤起一些怅惘。但月亮始终会升起,在北方的那个小城,在我的梦里。
2024年3月16日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16:51:0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16:51:07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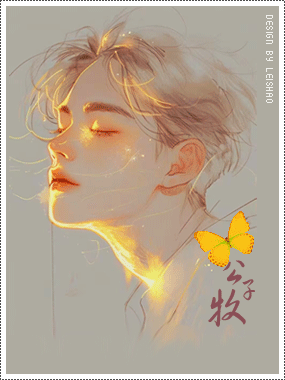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重拾旧笔
:重拾旧笔
 :牧牧
:牧牧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16:53:5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16:53:50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重拾旧笔
:重拾旧笔
 :牧牧
:牧牧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17:05:53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17:05:53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重拾旧笔
:重拾旧笔
 :牧牧
:牧牧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16 17:11:2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16 17:11:21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灯,等灯等登!
:灯,等灯等登!
 :今日1 帖
:今日1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0 10:43:3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0 10:43:39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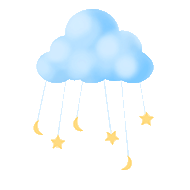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一世浮生一刹那
:一世浮生一刹那
 :远峤
:远峤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5 届
:风云0-5 届













 Post By:2024/3/20 18:16:4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0 18:16:42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2 9:52:2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2 9:52:27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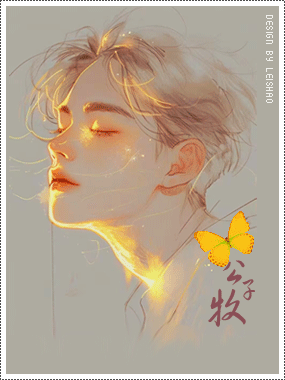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2 9:53:0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2 9:53:06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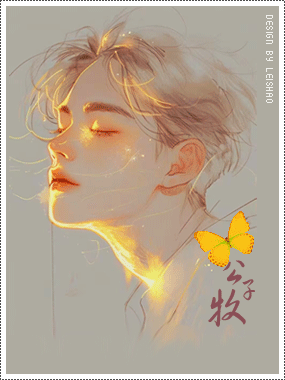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
 :苓苓
:苓苓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2 9:53:37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2 9:53:37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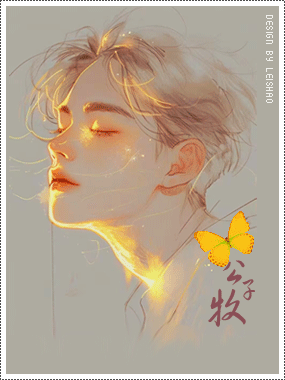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6 13:16: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6 13:16:16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