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疯婆子出嫁的那天,整个枫岭村都松了一口气,不需要陆有根打招呼,手上没有活的村人都赶到他家帮忙。
陆有根和王财进商量好,特意将过门的日子选在立冬,这时家家户户田里的稻谷早已入仓,被太阳晒干了的稻田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有根的两层小屋就盖在自家田地的旁边,来参加宴席的村人太多,门口摆不下,他索性将两张桌子放在了田里,安排村里的一大群娃娃坐着那。今天陆有根太忙了,一身红色夹克的他穿梭在人群中,脚不沾地跟各种相熟的面孔打着招呼,手里的红双喜散了一包又一包,家里的老人早就不在了,作为英花唯一的哥哥,他有责任地要为英花的出嫁张罗起一切。
“新郎来接人嘞!”一群娃娃早就冲上去讨喜,霹雳扒拉的鞭炮声后,胸前挂着朵红花的王财进从还未散去的硝烟里笑容满面地钻出来。他今天梳了一个大背头,脸上扑的淡粉像山沟里的晨雾,让人一时恍惚看不清岁月留在脸上的沟壑,王进财拖着一根瘸腿,不住地朝宾客们点头微笑,大喜之日,他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金黄的火光,屋外的阳光像灶台里哔剥燃烧的枯木,将他烤得浑身发暖。
有根下意识地要上去迎接,却被的邻座的二伯一把给按到座位上,“有根你别动哩,今朝你是家长,他就算五十了,也要给你敬酒磕头。”
“新娘子出来哩!”不知谁喊了一声,身穿红袄的陆英花被笑容满面的两个妇人一左一右搀着从屋子里出来。陆英花今日美得像一朵花,头上簪着一朵塑料玫瑰,周围点缀着白色满天星,这是时下最流行的头饰,弯弯的秀眉被修剪得如两丝新月,她有些胆怯,下意识地看向有根,却见有根被簇拥地坐在人群里,只好又低着头,眼睛没有焦距般在地上的瓜皮糖纸上乱扫。
“新郎官,快来接新娘子啊!”搀着陆英花的妇人朝着王进财嚷道。王财进赶忙上前代替了其中一名妇人的位置,陆英花对突然靠近自己的王财进下意识地躲了躲,但周围人太多了,她低着头,目光只能触得到一双双沾满泥土和灰尘的鞋子。新郎身上有淡淡的烟味,与有根身上的味道很像,陆英花扭过头,疑惑地打量起王财进,但这注视比门外的鞭炮声还短,她很快就被王财进胸口别着的那朵红花吸引,想要去够两只手却一左一右地被王财进和妇人紧紧拽住。
“敬茶哩!”有根周围的人早就散开,留出了一块空地。王财进替陆英花将茶水奉给陆有根,这时陆英花终于逮着空子,一把将王财进胸前的红花给摘了下来,前后翻转着放手里把玩,王财进咧开嘴嘿嘿笑起来,周围欢乐的气氛更加浓郁。
“磕头拜别——”五十岁的王财进向三十三岁的陆有根跪了下去,两个妇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另外两朵红花,连哄带骗地让二十五岁陆英花也跪了下去,起身后,陆英花手里的红花变成了三朵,她笑嘻嘻地想上前给哥哥展示,衣角却被身后的两个妇人不着痕迹地扯住。
整个接亲的过程,有根都恍恍惚惚地坐着,饮下那一口不知道滋味的茶水后他就醉了,周围的桌椅板凳都被奇异地拉长,每一个人都像田里弯曲盘旋的水草,它们身体柔软无骨,在吵吵闹闹的噪音里怪异地扭动着,只有王财进的头颅变得硕大无比,那一口被香烟浸渍出来的大黄牙占据了有根整个视线,他想再看一眼妹妹,茫然地在空气里搜寻,终于在一株老槐树下看到了一个扎着红色头绳的女孩,那女孩正蹲在地上观察石块下的蚂蚁,独自一人发出咯咯的笑声。
直到那笑声走远了,陆有根才回过神来,王财进已经带着英花骑上了摩托车,他要将新娘带去石墩村,那里还有一场热闹的宴席等待开始。陆有根端起面前的酒饮了一口,让顺着食道而下的灼热感暂时填补那突如其来的空虚。
“有根啊,你妹妹终于出嫁哩,接下来就该你咯,”二伯拍了拍陆有根的肩膀,他七十六了,孙子孙女都已经一大堆,与人丁单薄又已经过世的陆老三比起来,是受到葛仙保佑福气深厚的。
有根脸上涌上了一片潮红,陆英花离开的那条小路除了还有些未落地的尘埃外,只剩下两旁枯黄的丝茅草在随风轻荡。二伯的话让陆有根生出了新的力量,他从英花的出嫁中找到了更光明的未来,这未来驱使着他站起身,目光瞟向参加酒席的女人们,那些尖锐又轻柔的嗓音,苍老或青春的脸庞,都蕴含着繁衍生息的可能。陆有根端着酒杯,踉踉跄跄地走向别桌,他彻底地融入了酒席之中,门外稻田里的孩子们正兴奋地争抢着食物,不远处失去了稻穗的枯黄稻杆横七竖八地散落在稻田里,它们完成了秋天的使命,似乎正等待下一次春耕的轮回。
二、
家里没有了陆英花,五里八乡的媒婆终于肯上门了。
陆有根,陆老三的独子,拥有两层小楼和良田二亩,除了年龄大点外,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好女婿的人选。上门的媒婆带来了周围村庄姑娘们的信息,她们每一个都是保媒拉纤人口中的仙女,陆有根挑花了眼,让媒人安排见了几个。但村庄里的姑娘们眼光奇高,见面的时候都说陆有根憨厚质朴,回去后就跟媒人嫌弃陆有根老土。
陆有根只有初中文化,与土地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硬生生地靠着双手将家里的土房子换成了两层小楼,晚上,他在灯下看着自己长满老茧的双手,又对着镜子端详长满胡茬的脸庞,这样的自己,能不老土吗?他来到陆英花的房间,衣柜里还挂着陆英花的衣物,陆英花的桌子抽屉里,摆放着各种漂亮的小玩具。有根把每一件小玩意都认真地看了一遍,晚上就睡在陆英花的床上,第二天一早,他去镇上买了些漂亮明星的海报贴在家里,又理了头发,从那天开始,陆有根下地干活时戴起了尼龙手套。
但这些改变在媒人将一名姑娘带到陆有根家门前时破碎了一地。那名烫着波浪卷的姑娘看到了田地边的两层小楼,她说,现在谁还住乡下啊。
她又看到了客厅里贴的海报,笑道,王菲早就不流行了。陆有根局促地想留对方吃顿午饭,她说,下午还要去见三个相亲对象呢。波浪卷没有明确拒绝陆有根,但有根下午去挖地除草时,再没有戴新买的手套。
过完年,陆有根三十四了,还是会有媒婆来家里,但已经开始给他推荐寡妇,陆有根没有拒绝。陈桂莲今年三十六,有两个孩子,有根一眼就看上了陈桂莲的胸脯,米色的毛衣也无法掩盖住它的伟岸,这样的胸脯可以奶出更健康的孩子,见完陈桂莲的那天晚上,陆有根破天荒地睡不着,墙上的海报不止有王菲,还有好几个说不出名字的女人,她们在四四方方的画里看着陆有根在房间和客厅之间不停地踱步。有根深切地感受到女人的气息在朝着他靠近,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胸腹下方聚集,陈桂莲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她在狭窄的农村里没有更多选择,有根知道自己手上已经拽着一根线了,只需要轻轻一拉就能从地里拽出冒着乳汁的种子。
清明时分,有根去山上给去世的父母烧纸,往年英花还能帮着一起清理山道。今年雨下得很急,湿哒哒的杂草很难用柴刀砍断,泥泞的山路还让他摔了四次跤,好不容易爬到坟前,天上的雨倒又停了。有根细心地清理了这两座挨在一起的坟头,他带来的黄纸大部分都湿透了,只剩两三张可以点着,算算时间,陆老三和春芝被山石压死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情,那时候英花才七岁,这十八年里,有根带着天生痴傻的妹妹长大。对猝然长辞的两人,有根心中早就没有了思念,不过是循照旧历每年祭扫,但今年终究有些不一样,英花嫁人了,他也有了相中的对象。
陆有根微昂着头看向面前的两方矮坟,雨后山间的薄雾都在向此间聚拢,它们无声无息地萦绕在陆有根的四周,似乎要进入他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成为他此时沉默无言的底气。陆有根,很快就会扎入大地之中,留下属于他的根须,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根甚至心情极好地打了一个呼哨,他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便将来躺进地下,也能让黄纸的灰烬每一年在深山里飘荡不息,下山时,有根特意回头看了一眼,那两座掩映在青山之间的矮峰,像极了陈桂莲若隐若现的饱满乳房。
清明过后就该cha秧了,这时田里的水不冷不热,水面映照着蓝天,也映照着岸边的两层小楼,有根将自己对折进画一般的水田里劳作着,他享受伺候土地的过程,此时的每一个动作,都能在收获时得到回应,上午陈桂莲来看他,站在田边给他递了一次水。下午,二伯在田边扯着嗓子喊他,二伯说,陆英花被打了。
三、
陆英花被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石墩村与枫岭村隔着十里地,那些风一般的消息传到陆有根耳朵里不知道要拐几道山路。忙完了地里的活后,有根借着黄昏的光亮走到了石墩村,王进财的家在一处半山坡上,黄土垒成的墙壁外整整齐齐地码放着齐窗高的柴垛,柴垛延伸出去的一侧搭着一个潦草的猪圈,整个屋子前是一小片空地,空地上满是已经干燥的鸡粪,一角停着当初载走陆英花的那辆摩托车。
陆有根还没来得及喊人,迎面便遇到了八十岁的王大成,王大成眯着眼打量了陆有根半天,枯瘦的手抓着拐杖颤巍巍地问,找谁呀。这时王财进从厅后走出来,看到有根后明显愣了愣,他不咸不淡地招呼有根在八仙桌旁坐下,年老色花的王大成这才恍然大悟,孩他舅啊。
陆有根没有心思闲坐,他四处打量寻找陆英花存在的蛛丝马迹,大厅后的厨房里传来熟悉的咳嗽,他一个箭步迈过厅后的门槛,在柴火的浓烟里看到了一脸漆黑的陆英花。
哎呀,烧个灶都不会,王大成一边咳嗽一边用力跺着拐杖,财进,你的傻媳妇是想把我呛死啊!
陆有根喊陆英花的名字,英花怯生生地看向有根,手里的木柴再也递不进灶口。有根上前将英花拉到后厅的天井下,借着所剩不多的日光上上下下地打量她。陆英花跟出嫁的那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头发乱糟糟地粘在两鬓,身上穿着一件黑得看不出本色的破围裙,她耷拉着肩膀,手指不知所措地绞在一起。有根没有在她身上看到受伤的痕迹,目光瞥向她平坦的小腹时,来时的怒意顿时消散了许多。
怎么的,饭不做了啊,王大成含着浓痰的苍老嗓音在一旁响起,一根拐杖又把土地敲得笃笃作响。王财进自觉地走进厨房,继续往灶里添加柴火,陆英花有些害怕王大成,躲在有根身后,围裙上的碳灰蹭得有根身上到处都是,王大成开始骂骂咧咧地数落陆英花的不是,剥个毛豆能把豆子洒一地,洗五件衣服能被溪水冲走四件,喂个猪能把猪饿瘦两斤,更别提生火做饭了,不是想把厨房点了就是要呛死这一屋子人。
陆英花抽泣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加上正在烧火的王财进传来的咳嗽声,各种声音听得陆有根头昏脑涨,王大成那张皱巴巴的脸像锅里翻涌的泡沫,一张一合翕动的嘴巴像泡沫中间咕噜乱窜的漩涡,陆有根有拿起锅铲在这一锅汤里搅拌的冲动。半晌,铁锅安静了下来,王财进炖好了白菜汤,陆有根不想在这里吃饭,却又被王财进拉到一边。
王财进从皱巴巴的裤子里翻出一包烟,递给陆有根一支。两个男人蹲在屋檐下,白色的烟雾在发黄的牙齿间缭绕,又慢悠悠地在空气里纠缠,在最后一抹阳光消失之前,王财进说,你妹子好像不能生育,肚子快半年哩,都没有动静。
陆有根心头一颤,将手里的烟一口气吸完。他说,有空去做个检查吧。有根看着王财进那张五十年的丑脸,心里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出口,他想起自己来石墩村的目的,又像是找到了道德上的支撑,他问,你们有没有打过英花。
王财进似乎早料到了陆有根的问题,他说,打是打过的,不打不吃记性哩,我爹有时候拿拐杖敲一敲他,八十多的老头,没有什么力气,说是打,就是吓唬一下她哩。
这种果然如此的答案,倒让陆有根有些不知所措,他脑子里闪过英花干瘪的肚子,那平坦的小腹像雾蒙蒙的水气,让陆有根心头的恼火变得潮湿而无法发作,他说,你们不能打她。
这种话有什么意义呢?有根想,他是哥哥,说上这一句便已经尽到责任了。但接下来王财进的话却让陆有根变得惶恐,王财进说,要不,你把英花接回去吧。
陆有根猛地站起身,大声地质问王财进是什么意思,二十多的女人嫁给五十岁的瘸腿老汉,那是王财进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王财进这张破落户似的脸,还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英花能有什么问题,生不出娃那是死瘸子年老体衰,要去镇医院开单子,王财进这父子俩的德行,就是吊死鬼打粉cha花——死不要脸……
陆有根逃也似地从石墩村离开,离开前他又看了一眼英花,英花正坐在厅堂的八仙桌上,嘴里叼着一大块白菜叶子好奇地看着他。彼时天已经黑透了,王财进垂头丧气地窝在一张小板凳上吞云吐雾,王大成气得说不出话来,用拐杖捣地的笃笃声,驱赶着不速之客赶紧离开。
四、
田里的水稻长得飞快,秧苗反青的时候,陆有根下地运了一次禾,运禾就是除草,弓着腰双手在秧苗的间隙之中不停地探索,将手指触碰到的将长未长的杂草全部拔除,同时也松松泥土,让秧苗的根系扎得更深更稳,这是个不亚于cha秧的苦力活。陈桂莲带着小女儿站在路边看,母女两不时发出笑声,陆有根低头劳作,屋檐下传来的笑声让他干得更加卖力。
给稻田打完除草剂后,前期的农事便忙得差不多了,陆有根每天在家都盼着陈桂莲从家门口路过,但是除了运禾那日外,陈桂莲已经一连十几天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王财进来了一次,重申想把英花送回来的要求,被陆有根给狠狠地骂了回去。两层的小楼挡不住无孔不入的春风,王财进想要退婚的事情早就传遍了整个枫岭村,有根知道了陈桂莲不再上门的原因。
夜晚,他又来到陆英花的房间,在陆英花的床前坐了许久,自从英花出嫁后,他再也没有动过这件屋子里的东西,是否冥冥中便已知道这间屋子的主人还有回来的可能?她不过是天生痴傻,又不是山野猛兽,便是照顾一辈子又能如何?陆有根眼前晃过了陆英花和陈桂莲的脸,他生出了去找陈桂莲的冲动,又恍惚之中看到,陈桂莲的脸变成了“波浪卷”,他颓然地看着墙上的明星海报,身体被海报中的暧昧眼神一点一点地吞噬。
陆有根没有等来陈桂莲,却在一天吃过晚饭时,看到田边站着一个白色的身影,陆有根警惕地上前查看,浑身赤裸的陆英花正从田里捋下一把青壳的稻穗,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她披头散发,一双腿上沾满了泥土,胸前和背后到处都是伤痕,看到有根后,她嘿嘿地傻笑起来,被王财进父子赶出来的陆英花用了不知道几天时间,从石墩村走回了家里。
陆有根牵着陆英花走入两层的小楼,他给陆英花重新烧水洗澡,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陆英花一问三不知道,只知道走了很多的路,摔了很多跤,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才终于找到了这栋熟悉的小楼。陆有根没有想象中的愤怒,他仔细端详着陆英花身上的伤口,部分伤痕有旧日的痕迹,部分伤口已经结痂化脓,还有许多触目惊心的淤肿和擦伤。他拿出药酒给英花擦拭,将药酒在掌间搓热,双手粗暴地揉按着英花雪白的背部,英花发出痛苦的呻吟,兄妹俩肌肤的触碰,像是细致入微的运禾,陆有根满手的老茧在红肿的伤痕上游走,想要将英花这一路所受的伤害连根拔起。陆英花痛得受不了,挣脱开陆有根的触碰,怀抱着胸部蜷缩在床角里,陆有根目光微微顿了顿,他不是没有看过陆英花的身体,只是那两粒樱红又不可避免地令他想起了陈桂莲,陆有根收拾好药酒,给陆英花拿了旧日的衣物,这才回到自己房间,抚平剧烈的心跳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天晚上,陆有根辗转反侧没有睡着,屋里多了一个人,空气中都仿佛多了灼热的气息。他早早地起床,像以前一样为陆英花准备早餐,陆英花对墙壁上新出现的明星海报很感兴趣,她撕下来好几张,放进灶台里一边烧,一边咯咯傻笑。陆有根没有阻止她,一连几天,他都给陆英花上药,那些伤口随着水稻籽粒的变黄而慢慢消失。
陆有根逐渐不再去想陈桂莲,他认真伺候着水田和菜地,像过去二十年一样,一头扎进土地里,看着庄稼和蔬菜从种子开始,一点点慢慢长大。他不再需要媒婆,陆英花也不再需要出嫁,直到陆英花的肚子,也随着时间开始变大。
五、
立秋前,陆有根种下了第二茬水稻,这时,路过两层小楼的村民,都会将目光在陆英花的肚子上停留片刻,又带着暗晦难明的神色匆匆离开,仿佛朝着陆英花张望的那一眼,便能勾扯出无数动人心魄的秘密,二伯时不时地便站在小楼不远的地方,一边咳嗽一边用最恶毒的话语谩骂,在山谷里荡起绵绵的回声。
陆有根除了下地外,开始整日整日地待在家里,他不出门,也不许陆英花出门,那个莫名其妙隆起来的肚子,成为了他最大的敌人。陆英花吃不下东西,天天在屋里呕吐,陆有根脾气变得暴躁,在陆英花呕吐的时候摔了好几次瓷碗,满地的碎片让陆英花一边反胃一边大哭,陆有根恶狠狠地盯着她的肚子,仿佛在看一个尚未出生的恶魔。
每天晚上吃完饭,陆有根便端着凳子坐在英花跟前,表情凶狠地不断询问英花从石墩村到枫岭村的经历,不断捕捉那条路上的可疑身影,英花只是一个劲地哭,一个劲地摇头。有根却不依不饶,他非要找到一个草垛、一片茂盛的竹林、一块干净的草地,非要有一个看不清面目的男人,在将夜未夜的时候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在一遍遍的询问中,陆英花的眼神由迷茫逐渐变得清澈,浑浊的回忆里像一块荒地被陆有根强行开垦出一条清晰的轨迹,陆英花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笼罩着迷雾的男人,她可以用手比划出男人的身高,形容那个男人的身上的气味和力量,煞有其事地向过往的村民一遍遍讲述那个场景。每当这个时候,陆有根便木讷地坐在田垄边,他抬头看着盛夏转秋的天空,用余光品味人们脸上的表情,不论是惊讶还是怜悯,都让陆有根焦躁的心情微微平静下来。
陈桂莲在十月的晨光里来过,她带着两个孩子,在金黄的稻田那头远远地看了陆有根一眼,陆英花就靠在门槛旁,鼓着肚子慵懒地打着哈欠。陆有根第一时间便看到了陈桂莲,她穿着一件淡黄的格子外套,像一朵饱满的麦穗在风里婀娜地摇曳,陆有根还没来得及跟陈桂莲招手,陈桂莲便如雾一般消散,又像是纵身跃入了稻田中,化为了谷物的一部分,陆有根感受到了无言的羞愤,他疯狂地收割着水稻,挥舞着镰刀在清晨与秸秆搏杀,他恨不得自己成为被收割的水稻,被打谷机震成颗颗分明的谷粒,融入千千万万同样的谷粒之中。他累得像牛一般呼呼地喘着粗气,这样便不需要回忆某些漆黑的夜晚,可偶尔从劳作中回过神来时,又总第一时间想到陆英华肚子里的孩子,谷粒落在稻田里,来年可以重新长成秧苗,落在陆英花的肚子里,便长成了一个他也难以解开的死结。
秋收之后,王财进骑着摩托车来到了陆有根家,摩托车的后座上,大包小包地载着各种小吃和礼物,看到英花的肚子后,王财进脸上的喜色怎么都掩盖不住,他诚恳地对陆有根道歉,央求陆有根将陆英花交给自己带回家。陆英花把王财进当成了普通的村人,又一遍一遍地给他讲述那个迷雾里的男人,这个荒谬的故事显然没有让王财进相信,他信誓旦旦地向陆有根保证,陆英花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王进财的,他今后一定好好待她。
几乎没有多作挣扎,陆有根这一次亲手将陆英花扶上了摩托车,他朝着陆英花的背影挥手,像是在向一粒饱满的种子作别。快立冬了,空气里萦绕着泥土的清香,陆有根跳到已经干涸的稻田里,他仰着头躺在一簇稻草堆上,又抓过一束稻杆盖在脸上,将自己完整地埋葬。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9 20:30:0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9 20:30:04 [只看该作者]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9 20:38:5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9 20:38:52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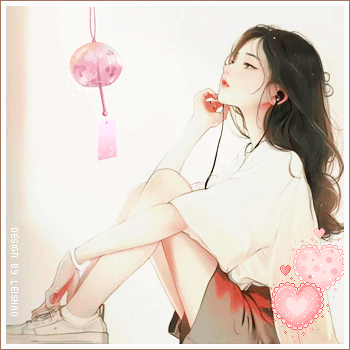


 |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



 :今日0 帖
:今日0 帖
 :风云0-0 届
:风云0-0 届





























 Post By:2024/3/29 20:46:4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24/3/29 20:46:41 [只看该作者]


